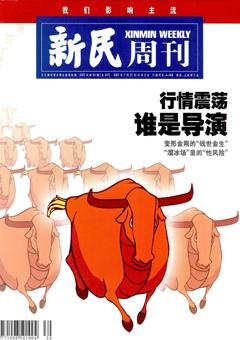葛劍雄:我一生受惠于圖書館
賀莉丹

高校圖書館的意義已遠超出借書、還書業務,高校的書應是全面的、系統的,這體現了一種知識結晶、一種文化。
今年3月,葛劍雄出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葛此前的身份是該校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葛劍雄的足跡遍及七大洲,作為一名關注社會動向的人文學者,他屢屢亮相媒體,評論時事。
7月13日,在復旦大學文科圖書館二樓的館長辦公室里,剛從青島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歸來的葛劍雄接受了《新民周刊》記者專訪,暢談任職以來種種感受。
建立圖書資料咨詢委員會
記者:這次任職轉換出自你個人要求,還是復旦校方的考慮?
葛劍雄:是校方的考慮。我做歷史地理所所長3任、11年了,要求不再做,學校希望我來圖書館,大概希望換換思路吧,原來的館長是理科的,做了15年,現在換個文科的,輪流做。
記者:一個說法稱,你做圖書館館長是因為要退休了。
葛劍雄:我今年62歲,還沒到退休時候。(笑)
不完全是年齡問題。前幾年我就跟學校提出應該培養新人,我們研究所是國家重點學科、教育部研究基地,不該老由一個人管著,現在換了比我年輕的,我希望今后有更年輕的人。
記者:是否很多人文學科教授都面臨兩難選擇?退休時也是學術成熟時,為讓賢不得不另找職位。
葛劍雄:現在各校不同,像我們學校,一般教授60歲退休,博導大多65歲退休,特殊情況可能70歲退……理科、醫科有院士制度,但文科到現在還沒有,我們學校有的文科老師很有名,但到70歲也要退了。
個人對這事要正確對待,個人研究受退休影響較小,當然退休后,不能再申請科研經費,除工資外的津貼大概也沒有了。考慮很多原因,"一刀切"很難,比如身體不跟歲數絕對平衡。從長遠看,退休應該有更大靈活性;但現在沒辦法,你不退人家上不來。不過我們學校一般會根據實際情況。
美國的大學教授是自愿退休的。我碰到的有些美國教授80多歲照樣做;還有的40歲就退休,接下來他做歡喜做的事,比如他本來研究電腦,退休了去畫畫、研究歷史……社會如果發展到這樣,就比較成熟。
我希望以人為本,考慮周到一點。比如,一些非退不可的教授,有時可返聘,我們在研究所搞的項目返聘了好多教授,他們做得很好,年輕人里找不到這樣的。
記者:作為一名研究型教授,擔任大學圖書館館長后,你有何新舉措?
葛劍雄:以前大家很多意見集中在圖書館,我發現有些是圖書館要改進,有些是雙方溝通不夠。
我們現在建立了一個圖書資料咨詢委員會,由31名教師組成,分別來自人文、社會、醫科、理科等,每個大學科或系、所,我們請一位教師擔任委員,請他們幫我們把關。(擔任委員)完全是盡義務,沒有任何報酬,他要了解圖書情況,并愿幫我們跟老師溝通,比如我專門請了一位中文系副教授,我知道他對數字化技術很內行。
我現在要求,在圖書館的重大事項做決定前,一定要征求咨詢委員會意見。比如,我們每年差不多花1000多萬元在外文雜志上,咨詢委員會提了很好的意見,建議哪本不再訂或再訂,我們還請他們回去征求老師們的意見。這樣就把有限的錢花在最重要的地方,我們也可及時聽到老師對我們圖書工作的意見,而且能把我們的困難告訴大家。學生中我們也成立一個,通過他們幫我們提高服務。最近很多同學畢業離校,我們請他們捐出不少可做公益的"愛心圖書"。
我長期做研究,對老師和圖書館兩方面情況都了解,易溝通,也愿為老師們的工作方便著想。比如老師提出,古籍部應自由去看,我贊成,但我們地方太小,所以我們向學校爭取房子,讓老師自由用書。
圖書館體現大學文化

記者:你與圖書館是如何結緣的?
葛劍雄:我小學五年級前在一個小地方,當時叫吳興縣南潯鎮,鎮上有劉承干的嘉業堂藏書樓等好幾家大藏書樓。但等我念小學,嘉業堂藏書樓不對外開了,有些藏書樓也燒掉了。因為學校圖書館的書很少,我很難借到書。
1957年,我進了上海的初中,按規定初中生可以到上海圖書館看書。我進初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上海圖書館,當時的上海圖書館在現在的美術館那,我走進去就想:地方這么大,書這么多,來不及看啊!當時初中生只能在里面看、不能外借,我一有空就去那看書,有些文章都在那抄,回來背。
過了幾年,我想辦法用人家的名義搞到一張外借卡,每次得人家寫委托書、蓋了章我才能借書,我記得當時圖書館外借部在南京西路、石門路的一幢花園洋房里,我愿意走走,我有不少書是從那借來看的。初中時有一次我想看歷史書《三國志》,圖書管理員以為我要看《三國演義》,我說沒錯,他覺得很奇怪,給我拿了。
1978年我考上復旦研究生,那時家里不像現在,沒什么書,除了上課我幾乎都在圖書館。當時文科圖書館這個樓還沒造,給研究生看書的地方是現在學校檔案館的樓上,我總覺得書真多啊,一直看。
學校第一天宣布這個決定時要我講話,我說,我一生受惠于圖書館。
記者:在海外知名大學,圖書館承擔怎樣的職責?
葛劍雄:一般講,學校對圖書館館長的工作較看重。作為一所大學,即使經費困難,它也會優先保證圖書館,很多書籍是長期積累,并非有錢就能買到,時間越長、書的價值越高。進一步發展,圖書館應主動提供信息。如果一個學校的圖書館起的作用好,對它的研究、教學肯定是很有利的促進。
發達國家到處有公共圖書館,我曾提過,上海圖書館應該在各社區都有分館;還書應該像寄封信一樣方便;除圖書,還可以聽CD、看電影,這都是information(信息)。我看這本書是找某方面知識,如果你的數據庫讓我直接找到所需資料,我不用借這本書了。圖書館是積累知識的地方,應該有一整套現代化手段,并不斷更新。
記者:目前我們高校圖書館的作用發揮并不充分,是否折射著當下急功近利心態?
葛劍雄:原因較多,第一,到現在為止,我們的圖書經費還不夠,很多館長都碰到這個問題,很多書買不起;第二,為老師和同學們服務還不夠,館際交流還不夠;大家對圖書館真正功能的認識還不夠,圖書館應該傳播知識、推動知識更新。
記者:過去傳統社會的圖書館館長,必由當地有聲望學者擔任,此傳統已漸消失。你如何看待這種消失?有人甚至認為高校圖書館館長是閑職一個。
葛劍雄:首先,高校圖書館的意義已遠超出借書、還書業務,高校的書應是全面的、系統的,這體現了一種知識結晶、一種文化。
其次,現在有數字化文件傳遞,圖書館對研究人員的作用應更大。你需要的文獻,無論在北京、臺灣、香港,還是美國哪座城市,我們都可去調。我們文科教師常抱怨花大多數時間搜集資料,這種情況逐步在改變,很大程度就靠圖書館用什么方式為他們服務。
再次,圖書館應進行學術活動,是學習、研究之地。世界上一些好的圖書館有供討論、個人研究、舉行公共活動的地方,我們現有的圖書館,包括大學圖書館遠達不到這個要求。正因如此,大學圖書館備受重視,哈佛大學真正的圖書館館長規定只能在哈佛最top的幾位教授中挑選一位擔任。除有形書籍外,圖書館還應作為無形知識象征,陶冶學生性情。
以前我們國家、地方圖書館館長都由德高望重的學者擔任,這些年不大注意了。教育部規定,每個本科生需要2個多平米的圖書館面積,一萬多個學生至少要有2萬多平方米的圖書館。這是有道理的,除看書外,圖書館還應鼓勵使用者做研究。這幾年有所改變,不少學校對圖書館越來越重視。
記者:當年蔡元培聘李大釗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辦圖書館的方針是,"圖書館已不是藏書的地方,而是教育的機構"。
葛劍雄:當初跟現在條件不同,現在的信息爆炸,圖書館要幫大家掌握資訊,比如,我們有文件傳遞業務,你需要什么文章,我們可以通過網絡全世界找,馬上給你提供PTF文件,你只要付小小成本。有很多書量太大,個人購買是浪費,如果圖書館服務好,今后可通過網絡在線服務傳輸文件,一些大部頭的書整個社會有幾部就可以了。
新技術是個好東西,可惜很多人不會用。圖書館的未來將經歷很大轉折,從紙本圖書發展到數字化圖書,我也主張并存,但今后的咨詢、查閱工作盡可能要用數字化取代。
記者:你既然贊成現代工具是個好事,為何不用手機?
葛劍雄:我用電腦大概是復旦文科研究人員里最早的,數碼相機、GPS我都有,但手機對我沒什么用,為什么一個人隨時隨地要跟人家聯系?我到現在基本不用手機,過多的信息不好,(不用手機)讓我自由點。
我承認,有時的確不太方便,但大多可以克服,比較起來,利多于弊,沒必要濫用一種新技術。在野外,誰救你?有手機也來不及!沒手機,倒會把很多事想得周到。我的電腦無線上網,我們通過郵件聯系。
研究仍在持續
記者:此次的任職轉換是否影響你的研究工作?
葛劍雄:一方面,學校知道我的研究、社會工作較多,在圖書館增加了一位常務副館長協助我處理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學校也希望我持續原來的研究計劃,我原來承擔的幾個項目照做。
我甚至希望有點幫助,譬如,這些圖書怎樣使教授們用起來更方便,我們有些項目就要參考古籍,如果大家方便,我也方便了。(笑)
目前我帶了七八個博士生,今年畢業4個,我一般不帶碩士,下學期我會給研究生開《中國移民史》課程。暑假還有3個跟圖書館有關的會,7月底在延邊開圖書館專家咨詢會,8月8日在青海西寧開教育部圖書指導委員會的會,8月18日去南非參加世界圖書館聯盟年會。有的會第一次參加,只能去,以后看情況。現在有很多學校的圖書館館長我還不認識,聯系當然要花點時間。
記者:與以前相比你的工作有何不同?
葛劍雄:我原來的研究所20多人,現在(圖書館)200人。原來我們雖有集體項目,但主要以個人來進行;而圖書館幾乎沒有個人的事,都以一個部門或系統進行,維持它的正常運轉是人跟事的管理;上司不同,以前我打交道的是教育部社科司,現在主要是高教司;現在教授們對圖書館有意見也會跟我提。
記者:在教育、環境保護、人口等領域上都可以聽見你的聲音。
葛劍雄:一個人除學術活動外,也是社會一員,如果自己的看法能對社會起一定作用,當然應該發表意見。所以我發表的內容不僅限于我的專業,也包括一些社會現象。
記者:目前你的壓力主要是什么?
葛劍雄:我比較忙,顧不過來。我總覺得我們整個國家、學術界的節奏太快、任務太重,很多工作做得慢一點,可能效果更好。特別一些大科研項目,我主張精一點、時間放寬一點,對整個國家有好處。
記者:你的足跡遍及七大洲,你很喜歡野外探索嗎?
葛劍雄:很喜歡,沒到過的地方我都想去。有人說危險,你坐在家里有時也有危險。一個人有機會,該出去體驗。但現在事太多,有很多機會我只好放棄。
我跟館里常郵件聯系,博士生有問題可用郵件聯系我,解決不了的我們見面,他們寫博士論文時我叫他們把寫好的隨時發給我,我隨時提意見,有兩個學生的畢業論文是我在非洲看完發給他們的。
有好的學生我還會招,但我不想招太多,多了顧不過來,我最多的紀錄是有一年招了5個博士生,一般招一兩個。我們的博士總體質量較高,全國優秀博士論文每年評100篇,迄今為止復旦大學文科得了8篇,其中4篇出在我們研究所,有兩篇是我指導的。
我原來做所長時,我們所不創收、不辦班、不招任何計劃外(研究生),我們的質量比較把得住。有人打電話給我說分數差一點、給錢,我說明年再考,要你錢干什么?!我們從來沒有這種事。
我們也主張同學中的公開競爭,我們面試是所有考生一起來,同學、老師之間可以看到,大家聽你回答,其他同學幫助糾正錯誤、搶答等,他們心里明白誰最好。我們培養研究生不是辦私塾,雖然我不做所長,我想(研究所)會繼續這樣。
記者:在未來,你最想做哪些事?
葛劍雄:等我時間多一點,把我想寫的書寫下來;世界上沒到過的地方還很多,有機會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