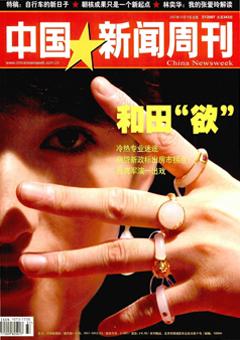就業不應是惟一溫度計
孫 冉
專業的好壞單純以就業率來判斷未免過于簡單,更不應因為就業率差就將某一專業砍掉,換言之,就業壓力應由社會、政府、高校三方分減,僅僅壓給大學會使整個高等教育變形。
如今,專業的冷熱很難有一個普遍的標準。
1999年高等教育擴招時,按招生人數排名前十的專業分別是:計算機、漢語言文學、機械制造、英語、臨床醫學、工商管理、會計、數學及應用數學、法學、電子信息。
現在這些專業在高校普及率極高,僅管理和外語兩個專業在上海高校的覆蓋率就達到了80%。正因為如此,這些專業不僅在報考時火爆異常,面臨就業時也競爭激烈。原來的熱門專業,到了就業卻變成了冷需求。而如機械加工、數控機床、速記這些市場反應頗好的專業,卻始終無人問津——按教育界的話說,大多數人出于偏見,不愿選擇走進工廠。
因此,熟悉高等教育的人們普遍認為,專業的好壞單純以就業率來判斷未免過于簡單,更不應因為就業率差就將某一專業砍掉。
《大學有問題》的作者熊丙奇認為,就業率差的專業要找到是什么原因導致的:是辦學方向不對,沒體現特色,或者是辦學質量不到位,沒結合到教育上。說到底,對待這個問題不能搞“一刀切”。
“有些問題是學校可以解決的,有些是學校怎么都解決不了的,這時就需要政策的扶持來做,如果說真的無法解決,才會到停辦這一步。而即使停辦也不應由政府說了算,而是由學校和教育市場來決定”熊丙奇說。
在他看來,教育市場包括兩部分,學校的生源市場和用人單位的人才市場。這兩個市場之間恰當的制約,即能使專業和就業產生動態的平衡。
通識教育的出口
有教育界人士指出,簡單跟著市場需求走的,是職業教育應實現的目標。在過去還是秉承著蘇聯教育模式的時候,就是簡單的為行業培養人才,一個蘿卜一個坑,效率優先。然而這樣培養出的人,雖然技術性很強,但適應性較差,一換了崗位,就無所適從。

而與職業教育相對立的是通識教育,強調對人類貫通的綜合素質的培養。它在美國最為普遍,從20世紀下半葉就獲得了教育界普遍的承認,并由一所大學迅速波及全國主要的大學。改變職業教育無法變通的最佳方式就是要打破專業界限,拓寬專業面,讓學生接受通識教育,在此基礎上再接受專業教育。
兩種教育方式的分歧從歐洲中世紀就開始了,即主張“解放人的思想和精神”的非功利性目的與“準備生存”的工具性目的之爭。
而兩者的矛盾在實行所謂消費者導向型的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表現得最為激烈。
在美國,市場運行和國家調控均以消費者,即買方利益為轉移。所以用人單位和大學生的意向關系到學校的生存,任何學校也不敢漠視,而是將其作為專業和設置課程的重要依據。
這種狀況在美國上世紀70年代表現得最為突出,不少高校在激烈的競爭中,不得不將專業設置屈服于市場壓力,導致高教職業化加深。
高等教育的過分市場化遭受到了美國教育和經濟界的一致反對,他們認為高等教育存在著與市場機制并不相協調的自身運作規律,理由是高校并不追求自身活動的最大利潤和最小成本,也并不完全依成本向學生收費等。
然而此時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當大學紛紛向綜合性研究型進發,通識教育越來越多時,職業教育又開始無法貫徹。
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胡瑞文認為,培養通識教育是給研究生準備的,為了朝上走才這么全面培養;但現在高等教育大眾化,本科生不是所有人都要成為管理型人才,也有一些要向技術型培養。
熊丙奇則認為,這個問題的癥結其實是社會不愿承擔任何培養人才的責任,非要依靠高校來承擔職業培訓所的角色。而如一些歐萊雅、寶潔、聯合利華這樣的外企,都有自己成熟的管理培訓生計劃。
以西門子公司為例,應聘時并不考察學生的工作經驗,只考核其基本能力和素質,因為這些就足以把你培養成西門子需要的人才。在專門的西門子學院,有入職經理和職業規劃經理來告訴你如何適應西門子的價值理念和工作環境,等于把學生真正變成社會人。
而如今用人單位對工作經驗的強調,讓學生過早社會化,大學教育和社會教育比例失衡。
教育界人士指出,高等教育不應無限承擔就業壓力,也應分減,僅僅壓給大學會使整個大學教育變形。在這個問題上高校、政府、社會各有各的責任。
將自主權還給高校
熊丙奇認為對大學來說,既然要辦,就要給它自主權。可以對它進行制度評估,辦亂了可以勒令停辦,但學校發展不能靠市場說了算,更不能以行政的力量要它回到以前狀態。
1852年,英國紅衣主教紐曼所著《大學的理念》首次探討了大學的精神,自此“學術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學生自治”等大學的基本價值和制度,淵源流傳。
其中大學自主權是精神的核心,它應包括:招生、學科設置、專業設置、人才培養方面包括課程和教材設置等方面的自主權。政府應擔任的角色是按照法律來監督辦學,現有規模是否符合條件,教學質量是否保證,對職責進行控制而不是過程。
專業設置往往是政府介入高校事務的切入點,目前,以專業目錄實施管理的模式,近似前蘇聯。而1992年后,俄羅斯聯邦科學部高等學校委員會就宣布自己與各高校不再是隸屬關系,專業目錄失去了強制性,只作為參考。
有人擔憂,政府放任不管,高校會失去理智盲目擴增專業。其實市場完全可以對此調節,當學校招不到學生,自然也辦不下去。政府在其中可以充當信息提供者的角色,給學校提供更全面的設置專業的背景信息,給考生和家長提供更準確的學校專業信息。
教育界人士認為,不僅專業設置上,在一些高校發展政策上也應放權,或者至少做到分類指導。
諸如擴招問題,很多大學并不趨之若鶩,對于建立綜合性大學的問題上,有些高校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這些年學科的增設呈現一窩蜂的態勢,很多學校一哄而上,但是過兩年,立馬反映到市場上就是此類人才過剩。這時候,人才之間一競爭,你們學校的學科基礎水平立馬凸現出來了。這樣反而辦不好。新升本科的一些院校尤其明顯,新專業多到反而使得學校以往優勢專業倒退。就像家里一下子多出來好多吃飯的嘴,最終大家都吃不飽。”上海大學教務處長周鋒說。
高校專業設置問題除了要淡化政府與市場的直接干預外,高校與用人單位聯合培養則是解決此問題的另一個突破點。
上海交大的核工專業,由國務院直接下指令讓學校一年提供200個畢業生,交大苦于無配套的師資和科研能力,遂與中廣核集團做了協定,學生讀到大三直接到過去接受培訓。這等于縮短了職業培訓的時間,但對學生來說也意味著被用人單位定位了。
但并不是每個學校和專業都有這么便捷的途徑。上海大學的通訊學院也與一些IT行業及醫療器械行業保持著密切聯系,對方人力資源部經理以及高級研發負責人參與教學委員會,但如何實現教學共建目前還是個問題,因為所設專業無法與教育部公布的專業目錄吻合。教務處長周鋒估計,變成選修課程或許是最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