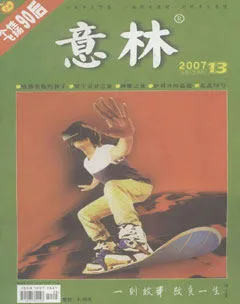口哨
張海迪
我會吹口哨。
是媽媽教我吹口哨的。那時我大約六七歲。
那時我整天躺在病床上,我的脊背上重疊著很長的刀口,我的腿不能動,我的胳膊不能動,我的脖子更動不得,假如我不小心活動一下,就會引起脊背傷口的劇痛。我長時間地躺著,我無可奈何地躺著,我終日孤獨地躺著。我不知道還有什么能比躺在這種疼痛里更難過的事了。我不知道我要躺多久,我不知道我的快樂是什么。我的眼睛一次次轉向窗外,我也沒有更多的玩具,我只有幾本翻爛了的小人書,一盒舊積木,還有一個傻乎乎的布娃娃。我惟一的快樂就是聽小鳥唱歌,它們嘰嘰啾啾很是熱鬧。
有一天我對媽媽說,我多想和小鳥一樣唱歌啊!
媽媽說我來教你吹口哨,這樣你就能和小鳥一起唱歌了。媽媽說,你把嘴唇嘟起來,輕輕,輕輕地吹。有一絲風吹過的樣子。
我于是輕輕,輕輕地吹,一絲細細的風從嘴唇中牽出,一個好聽的聲音散開來,很悠長很柔和,神奇而縹緲。我反復吹著,開始是單音,后來我學會了由低音吹到高音。再后來我就學小鳥叫,學它們啾啾地唱歌。我也吹自己會唱的歌,于是孤獨中的我找到了快樂。在我的口哨聲中,窗外小樹的葉子綠了,又黃了。在我的口哨聲中,樹葉飄落了,窗外的白雪蓋滿了大地。
春天來臨,少女時代的我熱情而活潑,在魯西北那片綠色的田野上,我又吹起口哨,我的口哨帶著弧線從這邊飄向那邊。村里的男孩們聽見我吹口哨很驚奇地瞪大了眼睛。我又用歡快的口哨呼喚大白狗,它一聽見我的口哨就會像一匹小白馬,從村里熱情萬丈地飛跑到我身邊。看著大白狗在我身邊親熱地搖頭擺尾,孩子們臉上露出油然欽佩的神情。我說我們一起吹口哨吧,于是田野上空仿佛飛來了一群百靈鳥……
夕陽就要落山了,我們還流連在金色晚霞的迷蒙中。孩子們推我來到河邊,我用口哨吹起蘇聯歌曲:
田野小河邊,
紅莓花兒開。
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愛,可是我不能向他表白,
滿懷的知心話兒沒法講出來。
啊……
晚風里,我的淚水涌出來。我覺得口哨與歌聲有區別,它給人更多的想像。口哨與唱歌不同,無論什么歌,用口哨一吹便牽出一縷淡淡的憂傷和悵惘。我唱歌沒有哭過,但我聽見自己用口哨吹出的歌卻不止一次地流下眼淚,也許是我喜歡那些染著憂傷色彩的歌。
木輪椅碾過鄉村土路的坎坷和泥濘,我告別了少女時代。
一天,我又一次躺在病床上,窗外的小鳥早已不在,這里病房的窗外看不見綠色的枝條,天空卻依舊是藍天白云。忽然我很想吹口哨。吹一支隨著輕風飄遠的歌,那個曾經孤獨的我,總盼望吹著口哨病就好了。不知不覺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這是多么漫長的一支歌啊。
我很想吹口哨,吹那支悠長縹緲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