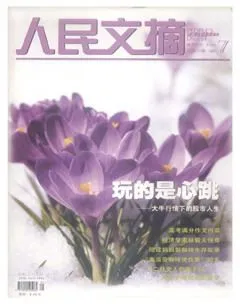俞平伯的“紅樓”情結
外祖母在1982年2月病故,此后外祖父俞平伯的獨居生活相當沉悶。除看書、寫字、偶爾讓外曾孫租個小三輪車出去吃頓飯之外,極少社交活動,過著近乎與世隔絕的生活。他把苦痛壓在心底,在言談話語中,卻從不流露。
我們家人都力圖使他沉悶的生活有所改變,但所做的一切,徒勞無效。他不愿做的事,絕勉強不得,所以也只有盡力照顧好他的生活,一切由他去。
1990年1月4日,是外祖父的九十誕辰。當日,老人強打精神,整整一個上午,在客廳接待絡繹不絕的客人。無論輩分大小,在給他拜壽時,他都堅持要站起來還禮。更為有趣的是,從寓所去飯莊,他乘坐的是租賃來的、專供老年人使用的小型三輪車,由他的外曾孫韋寧蹬著,緩緩行去。路人恐不會想到,坐在那輛“嘎吱嘎吱”亂響的破舊小三輪車上,穿著一件舊中式大棉襖的老頭兒,會是一位世界聞名、跨越了近一個世紀的作家、文學家和紅學家!
九十壽辰的紀念活動,在家人和親友們通力協作下,隆重而又圓滿地度過了。然而,看得出,他的心氣兒并不高。早在生日之前,他便常說,“過了九十歲就死了。”那時我們自然以為那只是囈語,誰料想此話成真!
九十壽辰后3個月,1990年4月16日,他因腦血栓再度中風,左側癱瘓,距第一次發病整整15年。病發突然,來勢很兇,也沒有任何預兆。他一動也不能動地躺在床上,面色青灰,人同槁木。經診斷,大夫要他入院治療,雖神志不清,仍連連搖頭,像過去一樣,堅決不肯住進醫院,只拿了些藥回來給他吃。
病中的老人真是可憐,他想動,動不得,想說,說不出。一向要強的他,堅持要用勉強能動彈的右手自己吃飯、吸煙,小便也不肯讓人幫忙。看他那股子倔犟的勁頭,艱難的舉動,令人心酸。為不使他因久臥病榻而引發褥瘡,我們每天堅持把他抱起來幾次,坐到書桌前去吃飯,飯后他歪著半癱的身子,叼著一支香煙,呆呆地坐著,兩眼直勾勾地望著窗外,不時抬起右手,習慣地撫摸著光禿的頭頂,在想些什么呢?也許什么也沒有想,他真該沒有什么牽掛了。卻不然!
他牽掛著“寫文章的人”。一天下午,他突然把我叫到床頭,抬起右手指了指他存放零用錢的壁柜,用含糊不清、斷斷續續的碎語對我說:“拿出……拿二百元錢出來。”我不解其意,迅速把錢拿出來,送到他眼前。“送……送給寫文……文章的人……”“寫文章的人很多,你要送給誰?”我附在他耳邊大聲喊著,他卻反應不過來,只不斷地重復著同樣的話。于是我把能想到的,和他相熟的寫文章的人一一數念給他聽,當提到潘耀明的名字時,他點了點頭:“就……就……給……潘……”我終于弄明白了,緊捏著手中的二百元錢,激動得熱淚盈眶。二百元,這數目太小了,然而那份情,那份在半昏迷狀態中仍流露出的感情,該有怎樣的價值啊!
待潘耀明回信向他致謝時,他已不記得,只是呆望著對他講話的我。就由他忘記了吧!我們卻永遠不會忘懷,不會忘記那二百元錢中所寄予的希望、關懷和深切的愛。
了卻了一樁心事,另一件心事又涌上他的心頭。這樁心事,在病后第三個月,不可遏制地迸發出來。
在服藥兩個月之后,他的病情略見好轉:那不健全的大腦,又有了些斷斷續續、不連貫的思維。他經常在清晨醒來,然后要陪夜的男傭抱他到書桌前坐下,邊吸煙,邊與男傭“閑談”。有一次甚至拿筆為男傭寫了幾個人名,他們是:葉圣陶、顧頡剛、冰心。為什么要寫,不得而知,或許是說與他們相識?還是想起了與他們交往幾十年的友誼?
自6月中旬開始,他每見到我,便總是重復地說一句話:“你要寫很長很長的文章,寫好后拿給我看。”這話使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寫什么文章?他為什么如此關心呢?
不久,他的話題,逐漸接近實質:“要重寫后40回。”語句含糊,很難弄明白他的真實意圖,然而有一點可以肯定了:他還是放不下那讓他人吃苦頭的《紅樓夢》!此后,話越講越清楚:“文章由四個人寫”,他對我說,“你是第一,俞成第二,我第三,韋梅、先平第四,寫好后送香港發表。”看這意思,是要來個“集體創作”了。但到底要寫什么,還是弄不清,無論如何不會是要我們重新寫作后40回吧?不管怎樣大聲地問他,也聽不明白,說不清楚。他那時的大腦思維,只能“輸出”,不能“輸入”,反應極其遲鈍。那些天,他一會兒要我把“脂批本”拿給他,一會兒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常常坐在書桌旁翻看《紅樓夢》,一看便是半個多小時。多少次,把我叫到身旁,似想說什么,又說不出。幾經反復,終于在斷續的話語中弄清了他的想法:要重新評價后40回!他不滿意他和胡適對后40回所作的考證,不贊成全盤否定后40回的作法。
外祖父在晚年,很少談《紅樓夢》。不想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地牽掛著它。這是壓抑了多年的一次總發泄——一次反彈,一首絕唱。“我不能寫了,由你們完成,不寫完它,我不能死!”他還對我母親這樣說。
我相信他定是帶著對《紅樓夢》的惦念和不甘心離開人世的。我不知道在天國的他,是否還像過去一樣地認真、執著。當我望著窗外綿綿秋雨的時候,時常虔誠地祈禱,那不是他灑向人間的“一把辛酸淚”。
(柴夢村摘自《文化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