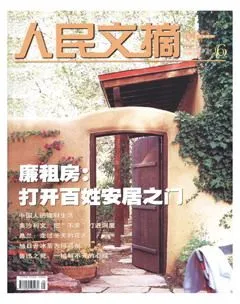領帶大王曾憲梓的苦難童年

他是“金利來”王國的創始人。在他三十多年的奮斗生涯中,苦難的童年、勤勞堅強的母親,共同鍛造了他的頑強意志和不屈不撓的精神。他,曾憲梓,一個在全世界都響亮的名字。
一
1934年2月2日的晚上,領帶大王曾憲梓出生在梅州一個貧苦僑眷的家里。
地少人多的梅州,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說。謀生的艱難,使得客家大多數男人外出營生,且多到南洋各地發展。曾憲梓的曾祖父、祖父,就是由于不堪過于潦倒而冒著生命危險,一路漂泊到南洋去的。他們曾經營一些小買賣為生,也賺了一點錢,然后返回家鄉蓋了房子,也就是現在的祖屋。
但是好景不長。祖父在闖蕩南洋的過程中,沾染上了鴉片,并且一發不可收拾。在毒癮與日彌深的情況下,祖父不惜變賣了家中微薄的家產。直到山窮水盡之后,毒癮難耐,祖父含疚離開了病榻之上的曾憲梓的祖母,甚至也來不及顧及當時仍是年幼的曾憲梓的父親、叔父和姑姑,獨自一人去了緬甸,從此一去不返,最后由于貧病交加而客死異鄉。
祖父棄家出走之后,窮困得苦不堪言的曾家,使得曾憲梓的父親,不得不中斷了小學學業,獨立挑起家庭沉重的擔子。到了十幾歲的時候,由于環境所迫,父親就像當年祖輩父輩的客家人一樣,懷著年輕人所特有的堅定信念,懷著創建美好生活的強烈欲望,和村里的男人一起,到了泰國開始闖蕩南洋。
破釜沉舟般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幾年之后,父親的事業開始有了不錯的起色。不到十年,父親和叔父已經能夠定居在泰國,一邊做些小買賣,一邊經營兩間小百貨公司。
極度貧困的曾家,總算有了一絲令人振奮的希望。于是,1927年的初夏,年僅23歲的母親藍優妹只身趕赴泰國與父親結婚。同年,母親懷上了曾憲梓的哥哥曾憲概。這之后,曾家的生活安定中逐見安詳,父親即使是小本經營的生意,也始終是薄有盈利,母親也可以帶著曾憲梓的哥哥曾憲概,往返于梅州與泰國之間。1933年的春天,年輕的母親在熱帶雨林氣候的泰國,懷上了曾憲梓。
父親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他從不善于用語言表達自己,他只是希望自己賺更多的錢,使他的妻子從此能夠不愁溫飽,使他的孩子們從此能夠無憂無慮地上學念書。然而,天有不測風云。由于過度的勞累,使父親患上了糖尿病,忙于生計的他常常顧不上看病吃藥,以至于到了無藥可醫的地步。在1938年4月那個陰雨綿綿的日子里,死神終于奪去了父親年僅35歲的生命。
臨終的時候,父親將那張兩千塊銀元的欠單塞到母親的手里,這是他留給他們母子生存下去的最后希望,他緊緊地握著妻子的手,叮嚀她保存好,叮嚀她再苦,也要讓孩子們念書。
二
父親去世之后,年僅32歲的母親,帶著9歲的憲概、4歲的憲梓,半饑半飽地過著他們含辛茹苦的歲月。
每天夜里,母親翻來覆去地盤算著明天的口糧、后天的口糧。當時,家里只租有幾分薄田和兩間老屋。青黃不接的日子,母親去替人家挑石灰。母親像男人一樣一擔一擔地挑,然后人家也像對待男人一樣,按擔子計數,給母親工錢。
然而,鄉下人挑石灰建房子的活路畢竟有限。于是母親在安頓好兩個兒子后,決定跟著鹽商雇傭的挑鹽隊伍,從梅縣挑鹽l7UhA3+dLIymS94zgkXE9Q==到江西去賣。這是一件連男人都不輕易做的苦差事,因為只有等到挑一擔鹽到達江西后,鹽擔必須無虧無損,刻薄的鹽商才會記工算錢。而母親一去就是十來天。在泥地里已玩累了的小憲梓,常常坐在自家的門檻上,眼巴巴地盼著他的媽媽回來。
母親駕牛替人家耙田,主人家往往會用很大很大的碗,盛滿滿一碗雞蛋煮米粉來犒勞母親。其實主人家也知道,母親怎么吃也是吃不完的,但他們都知道,母親還有憲概、憲梓兩個兒子。所以,好心的主人家故意做得很多,使得母親可以帶回家去給憲概、憲梓吃,或者讓他們兩兄弟到田壟上和母親一塊兒吃。
三
經過幾十年的奮斗,擁有億萬資產的曾憲梓,當社會需要的時候,常常拿出令人驚嘆的大筆捐贈。不過,在他個人的生活上,卻異常節儉,并有一個不為常人所知的習慣: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要計算一下,每一分錢花得值不值?
他說,自己永遠都不會忘記自己童年時無法遏止的種種渴望。
那時候,叔父一家人為逃避戰亂,從泰國返回家鄉梅縣,與曾憲梓的一家人共同住在曾家的祖屋里。叔父他們很有錢,他們的房間正好在曾憲梓他們住的房間隔壁,于是常常有一種很香很香的紅燜豬肉的香味,從叔父他們的房間傳出。
這種情況,對于經常是饑腸轆轆的曾憲梓來說,簡直就是一種難以忍受卻又不得不忍受的折磨。饞得直咽口水的曾憲梓,就經常偷偷地趴在房間的窗戶邊,悄悄地吸入這種美妙的香味。
實際上,如果伸出頭,是可以看得見叔父餐桌的。但是,對曾憲梓管教十分嚴厲的媽媽說了:“孩子,聽話,要有志氣。不要看了,看了你會更想、更難受。”
小小年紀的曾憲梓,覺得媽媽的話只對了一半。“是的,媽媽,我可以有志氣,可以忍著不去看,但是我的好媽媽啊,這么香的香味是擋不住的呀,我就是求它不要飄,它也會飄過來的呀?!”
這種情景,直到今天,對于曾憲梓來說,都記得非常的清楚,并且是歷歷在目、無法忘懷的。因為,當時那種很深很深的渴望,已經萬般無奈、萬般無助地銘刻在他童年的心靈里。
直到今天,曾憲梓還深有感觸地說:“從母親帶著我們度過的艱苦生活中,在我幼小的心靈里,我深深感受到窮苦人家不可言狀的那種疾苦,我心里面便有一股強烈的志氣,那就是我長大后一定要好好做人,一定要改變這種貧窮的生活。”
(王 帆摘自《現代家庭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