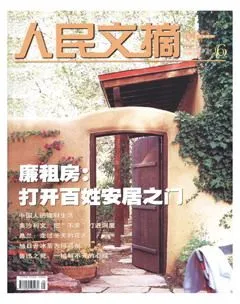李燕:“安樂死”之夢

跟大部分人一樣,李燕在年近30歲時開始認真籌劃未來。她的希望是:能夠合法地安樂死。
肌無力的病情越來越嚴重,她目前只有脖子和手指微微能動。不過李燕一直被照顧得很好,衣著整齊潔凈,衣食無憂,性格甚至能說得上樂觀;而網絡讓她“走”出了自己的小家,生活增添了許多滋味。
可是她的博客說的卻是個沉重的話題:不能體面地活著,就要有尊嚴地死去。
為“安樂死”而忙
“知道霍金嗎,我和他的病同種不同類,他是神經元的問題,我是進行性肌無力……”每個記者問她的病情時,李燕都會熟練地回答。
雖然李燕一直在通過博客尋找幫助,希望有人幫她提交安樂死立法的申請,但找上門來的卻大多是記者。
在此之前,李燕一天會在網上泡上7個小時,晚上12點左右休息,第二天9點、10點才起床。而最近,她都會在早晨7點起床,開始接受記者的采訪。
由于太過繁忙,李燕將QQ留言設定為:我現在在接受采訪,之后再跟你聯系。那么多記者上門,話免不了要重復,不過李燕總會面帶笑容,一一回復。雖然很多話,在她的博客里也早已經說過。她對記者說:“我只有靠你們了。”她認為記者是她與“立法”之間惟一的橋梁。
痛苦但有尊嚴
李燕的家在銀川市賀蘭縣的一個老式小區內。屋子一共40多平方米,分割成局促的兩室一廳。房間很干凈,墻上掛著李燕用電腦繪制的作品,門上懸著母親手工編織的小掛件。
“一點異味也沒有,真不像是個癱瘓病人的家。”當地電視臺一名女記者說,這與她到過的類似家庭見到的情形迥然不同。
李燕從1歲時開始發病,走路最好的時候也需要人托著,到了3歲,她只能騎在小三輪車上,用還有些力氣的左腿蹬著地前進。肌肉無力的癥狀此后一點點侵蝕她的全身——11歲時,她坐上了輪椅;15歲時,她再也端不起為她特意準備的塑料碗,重新像幼兒一樣靠母親喂飯;25歲左右,她的四肢幾乎完全失去了運動功能,全身只有脖子能略微挪動。
李燕至今還記得自己左臂失去功能時的情景。那是一年冬天,她突然發現自己原本尚可活動的左臂不能動了,當時她穿著厚厚的鴨絨衣。“我試著鍛煉,但衣服太厚了,我就想天暖和后再鍛煉吧。天暖和后,就再也動不了了。”
除了無法活動,內臟的痛楚也時常侵襲李燕。“心臟像巨型大鼓在敲,胃里像有火在燒,吃什么吐什么。”
在李燕母親的記憶里,李燕曾有三次因過于痛苦而拒絕飲食,李燕自己則說這樣的情形至少有五六次之多。
在她精神還好、肉體的痛苦暫止侵襲時,李燕用“懶散”形容自己的生活。
每天媽媽會將她從床上抱到輪椅上,為她梳洗,喂她吃早餐。在家里的時候,媽媽會頻繁幫她挪動坐姿;天氣好的時候,會推她出去曬太陽;為她定期清潔,讓李燕從不為衛生難堪。父親在食物上準備得非常精心,“我的病不能缺營養,我吃得很好,營養很充分”。
2003年,李燕開始接觸電腦和網絡。開始,她坐著輪椅到網吧上網,后來家里買了電腦,裝了寬帶。靠著左右手可以勉強動的各三根指頭,李燕迷上了電腦繪畫,和很多年輕人一樣喜歡在網上沖浪,而開始撰寫安樂死博客后,李燕更是獲得更多的動力。

如果把要求定得低些,李燕的生活毫不缺乏物質、精神乃至理想。“我覺得自己活得很有尊嚴。”她說。
母親守護底線
如果沒有母親,李燕一直享受的有尊嚴的生活會大打折扣。
2005年6月1日,李燕的母親在院里一腳踩空致右腳骨折。在母親養傷的20多天里,李燕的生活大亂。
雖然父親也悉心照料李燕,但畢竟清理衛生上不能像母親盡其所能。晚上為李燕翻身,白天給她調整坐姿,為她打開電腦,幫她打字這些活,也只有母親才能做到無微不至。
“我媽媽是我的廚師、護理工、婦科病大夫。”李燕說。在李燕的博客里,記載著母女倆去看養老院的一次經歷。母親希望有一天自己不能照顧她時,可以把她送到那里繼續生活。雖然不大情愿,但李燕最后還是答應去看一下。一場大雨最終使母女倆未能成行。
李燕的博客并沒有記載后來的事。后來,她們最終到了養老院。結果是,母女倆都覺得,不可以讓李燕在那里生活。
如果沒有了母親,李燕無法接受活著。“我很反感那句話:好死不如賴活著。”李燕說,曾有人用這話勸她不要安樂死。“我只能說,他沒有體會過我的生活,這樣說,是不負責任的。”
李燕的媽媽宋鳳英已經63歲了,對于女兒,宋鳳英一直心懷歉疚:“我沒有給她一個健康的身體,她從小也沒有好的經濟條件,我對不起她,也救不了她……”
她說自己至少可以繼續照顧女兒10年。“到了七八十歲,我愿意跟她一起安樂死,我不會把她丟在這個社會上,丟給親戚朋友。”
對于女兒在呼吁的安樂死立法,宋鳳英已經從最初的不理解到完全接受,“如果她能把這事辦成,就能幫助很多和她一樣受苦的人了。”
安樂死與“重生”
在萌生安樂死的想法后,李燕曾給自己的父母寫過一封未發出的信:
“爸媽別怪我。我活得實在太痛苦了,無論我多么努力地說,多么努力地笑,我還是無法像正常的人那樣從心底里快樂。”
“我馬上就30歲了,一晃眼40歲也會來到,我現在越來越害怕這些年年增長的數字了。它們越接近我,我就越來越痛苦,越來越恐懼,越來越焦慮。未來會帶給我什么樣的場景,我想不到,但我可以感應得到,會很可怕,生不如死。”
“與其等到你們都老了抱不動我的那一天再死,不如現在就開始,起碼我看到的你們是能動的,這樣我也就有了一點安慰了。傷心、難過是難免的……要比天天受折磨好得多……”
雖然直到現在,還沒有人幫助李燕提交“安樂死立法”的申請,但她也知道,即使有人幫助,安樂死立法也不會那么容易通過。
在網上她已經知道,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忠誠在2006年兩會時,就提出安樂死立法,但也沒有通過。
對于不可知的未來,李燕說,只要還有人需要安樂死,自己就會不斷努力。“我要讓國家知道,有我這樣一個人,我有這方面的需要……”
對于爭議重重的安樂死,李燕說,在她的心目中,安樂死不是毀滅。
“我覺得并不殘酷,安樂死是自愿的。不是像南京大屠殺一樣,見人就殺的……就像鳥籠子里的鳥,籠子還被罩上了,我想做的是從籠子里飛出去。我認為,這是一種重生的境界。不要把安樂死想得太灰暗了,站在我們的角度看待安樂死,你會發現這是截然不同的。”
(吳 思摘自《錢江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