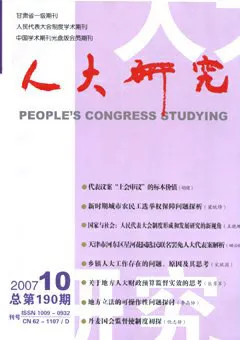新時(shí)期城市農(nóng)民工選舉權(quán)保障問題探析
農(nóng)民工是我國(guó)社會(huì)轉(zhuǎn)型時(shí)期出現(xiàn)的一個(gè)非常龐大群體,在和諧社會(huì)建設(shè)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據(jù)國(guó)務(wù)院近日發(fā)布的《中國(guó)農(nóng)民工調(diào)研報(bào)告》顯示,我國(guó)有1.2億左右的農(nóng)民外出務(wù)工,而且每年呈600萬(wàn)的趨勢(shì)增長(zhǎng)。這樣一個(gè)越來(lái)越龐大的社會(huì)群體如果游離于政治生活之外,他們的利益訴求得不到回應(yīng)和保障,必然會(huì)給城市的管理和社會(huì)的穩(wěn)定帶來(lái)不可忽視的影響。因此,我們不能不關(guān)心城市農(nóng)民工的政治生活,其中他們參加選舉的權(quán)利能否得以實(shí)現(xiàn)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城市農(nóng)民工選舉權(quán)利之現(xiàn)狀
普遍享有、平等地行使選舉權(quán)是衡量一國(guó)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標(biāo)志之一,是人民主權(quán)實(shí)現(xiàn)的重要條件,也是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基礎(chǔ)。我國(guó)憲法、選舉法以及地方組織法對(duì)每一個(gè)具有選舉權(quán)利的公民都給予規(guī)定和保護(hù),但是隨著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人口流動(dòng)愈加頻繁,尤其是在城市流動(dòng)的農(nóng)民工,他們的選舉權(quán)利正日益被邊緣化,這一群體的選舉權(quán)現(xiàn)狀不容樂觀。
(一)城市農(nóng)民工參與戶籍地的選舉比例低
據(jù)徐增陽(yáng)和黃輝祥兩位學(xué)者對(duì)湖北省武漢市農(nóng)民工政治參與狀況的調(diào)查顯示,沒有參加最近一次村委會(huì)選舉的農(nóng)民工高達(dá)79.5%,參加的只占19.3%。即使參加選舉的農(nóng)民工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通過(guò)委投或函投的方式參加,親自參加的也只是其中的52.4%[1]。另?yè)?jù)鄭傳貴先生對(duì)江西省南昌市的調(diào)查顯示,只有15%的農(nóng)民工自外出打工后參加過(guò)村委會(huì)選舉,沒有參加的就占81.5%[2]。村委會(huì)選舉是村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礎(chǔ),是農(nóng)民政治參與的重要形式。但是農(nóng)民工外出打工大多為了養(yǎng)家糊口,并且在外生活多年,他們出于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利益關(guān)聯(lián)性的考慮以及對(duì)選舉程序設(shè)計(jì)的質(zhì)疑,往往不得不放棄在戶籍地的選舉權(quán)利。
(二)農(nóng)民工被拒于城市選舉之門外
城市是農(nóng)民工的生活和工作地,與農(nóng)民工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guān)。武漢市的農(nóng)民工調(diào)查表明,69.3%的農(nóng)民工認(rèn)為應(yīng)該參加城市管理,然而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他們的這一訴求往往受到諸種制約。據(jù)各省關(guān)于《縣鄉(xiāng)兩級(jí)人大代表選舉實(shí)施細(xì)則》來(lái)看,一般都明文規(guī)定:外來(lái)人口在戶口所在地參加選舉。雖然也有對(duì)實(shí)際上已經(jīng)遷居外地的選民在取得選民資格證明后可以在現(xiàn)居住地的選區(qū)參加選舉,但是我國(guó)選舉技術(shù)的困難和代表名額分配上沒有考慮流動(dòng)人口,所以農(nóng)民工很難獲得在現(xiàn)居住地的選舉權(quán)利。另外,城市居民也排斥甚至拒絕農(nóng)民工參加當(dāng)?shù)氐倪x舉,因?yàn)樵诓辉黾用~的前提下允許外來(lái)人口在當(dāng)?shù)貐⑴c選舉,對(duì)本地戶籍人口的民主權(quán)利就是一種侵犯。
由此可見,農(nóng)民工既無(wú)法在戶口所在地實(shí)現(xiàn)選舉權(quán),也不能在現(xiàn)居住地參加選舉,他們無(wú)疑成為政治參與的“體制性邊緣人”。
二、城市農(nóng)民工選舉權(quán)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戶籍制度的限制,選舉法規(guī)的空缺
按照現(xiàn)行的選舉法及相關(guān)法規(guī)規(guī)定,縣鄉(xiāng)兩級(jí)人大代表在選區(qū)劃分、選民登記方式、代表名額分配上主要是以戶籍為基本依據(jù)的。原則上農(nóng)民工是不能參與所居住社區(qū)的選舉,而只能回原戶口所在地參加選舉。但是農(nóng)民工要回鄉(xiāng)參加選舉的成本過(guò)高,而且鄉(xiāng)村的選舉與自身利益關(guān)聯(lián)性也不大。要他們花上千元甚至幾千元回去參加一次與自己利益關(guān)系不大的鄉(xiāng)村選舉,農(nóng)民工往往會(huì)望而卻步。農(nóng)民工中大多數(shù)人在城市生活多年,也是其中一分子,更希望能融入城市群體中并參與城市管理,進(jìn)而選出能充分表達(dá)自身利益訴求、維護(hù)自身利益的代表。但是在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下形成的對(duì)農(nóng)民的歧視、對(duì)外來(lái)人口的抵觸心理以及在城市選舉操作上種種實(shí)踐困難等原因,農(nóng)民工在城市也無(wú)法實(shí)現(xiàn)他們理應(yīng)擁有的選舉權(quán)。戶籍體制的束縛、選舉法規(guī)的空缺,無(wú)形中給農(nóng)民工設(shè)置了一道難以逾越的屏障。廢除戶籍差別、改革和完善現(xiàn)行的選舉制度,使農(nóng)民工享有在其居住地的選舉權(quán)利,就成了當(dāng)前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二)農(nóng)民工利益代表組織的缺乏
公民參與政治往往借助于一定的組織載體,通過(guò)組織載體可以把各個(gè)利益主體在公共問題上模糊不清的意志和行為轉(zhuǎn)化為明確的共同組織意志和集體行動(dòng),從而影響政府決策或其他公共管理活動(dòng)[3]。然而,由于我國(guó)長(zhǎng)期實(shí)行限制性民間組織管理政策,導(dǎo)致社會(huì)利益結(jié)構(gòu)的組織化程度不高,并且發(fā)展極不平衡。政府出于維護(hù)社會(huì)穩(wěn)定的考慮,在民間組織管理上一直實(shí)行嚴(yán)格的控制,如要成立新社團(tuán),一般要求有活動(dòng)資金、固定場(chǎng)所和工作人員等條件方能獲得業(yè)務(wù)主管部門的批準(zhǔn)。對(duì)于缺少社會(huì)資源、收入甚微的農(nóng)民工而言,要符合以上條件成立代表自身利益的團(tuán)體組織幾乎是不可能的。沒有一個(gè)正式組織,農(nóng)民工人數(shù)雖多但不構(gòu)成勢(shì)眾,無(wú)法依靠正式的組織來(lái)維護(hù)自身的利益。當(dāng)農(nóng)民工遇到自己無(wú)法解決的問題時(shí),往往尋求于“同(老)鄉(xiāng)會(huì)”如此一般的非正式組織。雖然這些組織對(duì)農(nóng)民工的利益也起到一定的保護(hù)作用,但無(wú)法替代正式組織的政治功能、法律功能以及社會(huì)地位功能所發(fā)揮的作用。
(三)農(nóng)民工政治效能感比較弱,影響其參與選舉活動(dòng)的積極性
政治效能感指的是公民對(duì)自己政治參與行為影響力的主觀評(píng)價(jià)。農(nóng)民工大多認(rèn)為自己的投票行為作用不大,其效能感很低。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只從短期的選舉成本考慮,卻沒有意識(shí)到自己選舉出來(lái)的代表對(duì)于維護(hù)自己的合法權(quán)益和解決自己的社會(huì)保障問題、工資問題以及其子女的教育問題的重要性;二是農(nóng)民工認(rèn)為代表們并不替自己說(shuō)話,發(fā)揮不了作用,覺得選了也白選,選誰(shuí)都一樣;三是對(duì)選舉程序的公正性、民主性產(chǎn)生質(zhì)疑,認(rèn)為既然上面早已內(nèi)定好了人選,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票根本起不了作用。在政治領(lǐng)域,人們的選舉行為的的確確是一種利益行為。整個(gè)選舉制度和代議制度都是建立在一種利益基礎(chǔ)之上的,公民參與選舉,從根本上說(shuō)都是為了某種利益的[4]。當(dāng)農(nóng)民工認(rèn)為自己的行為起不到預(yù)期的作用或不能給自己帶來(lái)大于所付成本的更大利益時(shí),他們的選舉態(tài)度往往是消極的。
三、保障城市農(nóng)民工選舉權(quán)利的對(duì)策思考
農(nóng)民工政治參與主要是通過(guò)參加選舉活動(dòng)這一途徑來(lái)實(shí)現(xiàn)的,因此,保障城市農(nóng)民工的選舉權(quán)利是當(dāng)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問題。筆者認(rèn)為,應(yīng)從這幾個(gè)方面著手:
(一)改革和完善戶籍制度,為實(shí)現(xiàn)農(nóng)民工選舉權(quán)利掃清體制性障礙
我國(guó)的戶籍制度在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期對(duì)于維護(hù)社會(huì)穩(wěn)定和促進(jìn)早期工業(yè)化建設(shè)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人口流動(dòng)頻繁的今天,戶籍制度給流動(dòng)著的農(nóng)民工帶來(lái)了許多困難。當(dāng)前,農(nóng)民工的選舉權(quán)被邊緣化,使他們處于國(guó)家政治生活的“真空地帶”。“某種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5]沒有農(nóng)民工這一龐大群體的政治參與,社會(huì)主義民主也只是一種假民主,那么公平正義也就無(wú)法得到根本體現(xiàn),和諧社會(huì)的目標(biāo)更不可能實(shí)現(xiàn)。要將這一群體納入政治生活和參與社會(huì)管理,推動(dòng)社會(huì)主義民主政治,就必須給予他們的選舉權(quán)利以制度上的保障,改革現(xiàn)行戶籍制度,弱化戶籍制度的政治功能,促進(jìn)農(nóng)民工市民化,讓他們享有與城市居民平等參與城市社區(qū)選舉和人大代表選舉的權(quán)利。我們可以借鑒戶籍制度比較成熟的國(guó)家在這方面的經(jīng)驗(yàn)。例如,英國(guó)法律規(guī)定,在某一地區(qū)或選區(qū)內(nèi)居住三個(gè)月以上時(shí)間(法國(guó)、比利時(shí)是六個(gè)月,美國(guó)是一年),你就是當(dāng)?shù)氐倪x民而不管你的原籍在哪里。
(二)設(shè)立選舉登記機(jī)構(gòu),采取自動(dòng)登記與自愿登記、網(wǎng)絡(luò)登記與手工登記相結(jié)合的登記模式
選民登記是選舉活動(dòng)的基礎(chǔ),它關(guān)系到公民選舉權(quán)和被選舉權(quán)的確認(rèn)或剝奪。改革開放后,農(nóng)民的大規(guī)模流動(dòng)給選舉工作增加了許多困難,要耗費(fèi)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確認(rèn)選民身份。這些大量的登記工作必須由常設(shè)的機(jī)構(gòu)來(lái)做。選民登記機(jī)構(gòu)根據(jù)戶籍管理資料自動(dòng)登記選民,同時(shí)強(qiáng)調(diào)選民應(yīng)主動(dòng)到選舉機(jī)構(gòu)去辦理登記手續(xù)、領(lǐng)取選民證。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通過(guò)互聯(lián)網(wǎng)進(jìn)行登記、查詢和公布選民名單。對(duì)于長(zhǎng)期在外并表示不參加戶籍所在地選舉的農(nóng)民工,戶籍地應(yīng)不予登記,但是可以為其出具選民資格證明并告知其應(yīng)參加現(xiàn)居住地的選舉。只有把選民資格審查、選民登記工作做好了,選區(qū)劃分和代表名額才能更加科學(xué)與合理。
(三)增加選舉的競(jìng)爭(zhēng)性規(guī)定,提高城市農(nóng)民工參與選舉的積極性
雖然我國(guó)選舉法規(guī)定實(shí)行差額選舉,但往往實(shí)際差額不大。一些地方選舉為了保證政黨和組織提名的候選人當(dāng)選,有意識(shí)地把可能性很低的人選確定為正式候選人作陪襯。這樣選舉就缺少了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沒有候選人的平等競(jìng)爭(zhēng),選民無(wú)法選出能代表并維護(hù)自己利益的代表,他們的積極性就會(huì)受挫。這也是農(nóng)民工選舉態(tài)度冷漠的原因之一。因此,要提高農(nóng)民工參加選舉的積極性,必須允許農(nóng)民工自己的代表或代表農(nóng)民工利益的候選人參加選舉,讓農(nóng)民工也選出表達(dá)和維護(hù)自己利益訴求的代表。
注釋:
[1]徐增陽(yáng)、黃輝祥:《武漢市農(nóng)民工政治參與狀況調(diào)查》,載《戰(zhàn)略與管理》2002年第6期。
[2]鄭傳貴:《流動(dòng)人口政治參與邊緣性的社會(huì)學(xué)研究》,載《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4年第7期。
[3]邵德興:《當(dāng)前城市外來(lái)人口政治參與的若干難點(diǎn)分析》,載《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xué)報(bào)》2004年第4期。
[4]蔡定劍:《中國(guó)選舉狀況報(bào)告》,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頁(yè)。
[5]羅爾斯著:《正義論》,何懷宏等譯,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yè)。
參考文獻(xiàn):
[1]艾麗穎、孟擁國(guó):《淺析農(nóng)民工在城市中政治參與的現(xiàn)狀》,載《湖南科技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6年第1期。
[2]李東、 劉偉:《流動(dòng)人口的選舉權(quán)分析》,載《西北人口》2004年第3期。
[3]任中平、劉剛:《論構(gòu)建和諧社會(huì)進(jìn)程中的農(nóng)民工政治參與——不可忽視的“四家問題”》,載《云南社會(huì)科學(xué)》2006年第2期。
(作者單位:廣西師范大學(xué)政治與行政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