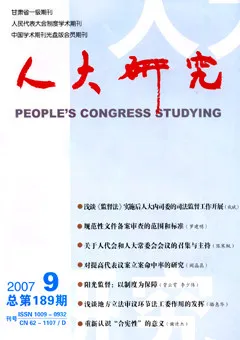《新民主主義論》并未初步形成理論形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研究毛澤東關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論具有重要的文本與實踐價值。毛澤東何時首次提出“人民代表大會”概念,這似乎不成問題。理論界、學術界一般認為:毛澤東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首次提出“人民代表大會”概念。由此推論:毛澤東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已初步形成理論形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然而,我們通過追本溯源的考證與分析,發現上述觀點是一種基于版本原因得出的錯誤結論。
一、《新民主主義論》沒有提出“人民代表大會”概念
眾多著述指出:毛澤東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最早提出“人民代表大會”概念。如稱“需要特別指出的是,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這一光輝論著中,首次明確提出了‘人民代表大會’這樣一個嶄新的概念”[1]等等。其實,我們通過對各版本的《毛澤東選集》及《新民主主義論》單行本的內容比對,可以得知:《新民主主義論》并沒有提出“人民代表大會”概念。
問題主要產生于《新民主主義論》中的一段話:“中國現在可以采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縣人民代表大會、區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人民代表大會(字體下著重號為筆者所加,下同)的系統,并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但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才能適用于各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于表現民意與指揮革命斗爭,適合于新民主主義的精神。”[2]確實,這是新中國建立后出版的各版本毛澤東著作中出現“人民代表大會”概念之處。問題是,新中國建立后,在出版毛澤東的著述時,原文經過了若干改動。據考證,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做了三次修改,分別是1940年2月、1942年春、1952年4月[3]。新中國建立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及單行本《新民主主義論》都采用1952年經毛澤東修訂的內容。那么,我們必須弄清,《新民主主義論》中的這段話是否經過了改動?回答是肯定的。正是毛澤東在第三次修改時改動了這段話。
1940年1月,毛澤東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為題發表了演講。2月,該文以相同標題發表于延安的《中國文化》雜志。同月,延安《解放》雜志以《新民主主義論》為標題發表。自此該文正式以《新民主主義論》行世。事實上,1952年前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各根據地、各解放區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或單行本《新民主主義論》這段話都沒有出現“人民代表大會”概念,原話均為:“中國現在可以采取國民大會、省民大會、縣民大會、區民大會直到鄉民大會的系統,并由各級大會選舉政府。但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才能適用于各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于表現民意與指揮革命斗爭,適合于新民主主義的精神。”[4]與此相印證,謝覺哉在1945年1月27日的日記中引用了毛澤東這段話,除個別技術性的錯漏外,也完全與此一致[5]。可見,《新民主主義論》中并未提出“人民代表大會”概念,它是毛澤東1952年改動而來的。
順便說明,既然《新民主主義論》不享有“人民代表大會”概念的“首創權”,那么據筆者現所掌握的資料看,“首創權”當由《論聯合政府》享有。《論聯合政府》說:“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制度,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只有這個制度,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最高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務,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6]我們進行了認真核對,這段話中“人民代表大會”概念在建國前后各版本的《毛澤東選集》及單行本《論聯合政府》中都是一致的。
二、《新民主主義論》并未初步形成理論形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1952年,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內容做了改動。那么,原有“國民大會”等概念與改動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等概念之間,僅僅是文字表述上的不同呢,還是涉及實際含義的差別?如果是前者,那僅僅涉及“人民代表大會”概念的形成時間等;如果是后者,那就涉及理論形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基本形成時間等重大問題。茲事體大,不容不辨。
有人認為,毛澤東對其已發表的著述進行改動,往往只是一種不涉及原文思想內容變化的技術性改動。這種認識值得懷疑。舉例說,建國前夕,毛澤東對蘇維埃代表大會有了新認識:“‘蘇維埃’代表大會。我們過去又叫‘蘇維埃’,又叫‘大會’,就成了‘大會大會’,這是死搬外國名詞,現在我們就用‘人民代表會議’這一名詞。”[7]根據毛澤東上述精神,建國后在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過程中,凡出現“蘇維埃”字樣,均作了改動。如將“蘇維埃”改為“我們”,“蘇維埃政權”、“工農兵蘇維埃政權”改為“政權”、“紅色政權”、“民眾政權”,“蘇維埃代表大會”、“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改為“工農兵代表大會”,“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工農共和國”,“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等等,這些都反映了毛澤東乃至整個中共對革命政權有了新的重要認識,而不只是“技術性改動”。應當看到,毛澤東1952年對《新民主主義論》的多處改動中,既有涉及文字語氣、標點符號、語法結構等技術性改動,又有關涉概念置換、內容修正等實質性改動。而將“國民大會”等概念改動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等概念,明顯屬于后一類改動。
第一,從制度名稱和基本內容看,抗戰初期與中期的毛澤東繼承了孫中山《五權憲法》與《建國方略》政體制度構想。孫中山將西方代議政體與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相結合,為未來中國政治發展設計了藍本。孫中山認為,中國政治發展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以縣為自治單位,國民得選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選舉議員以議一縣之法律;凡一省全數之縣都實行自治,則省為憲政開始時期;全國有過半數省份達到憲政開始時期,則召開國民大會頒行憲法。可見,在孫中山設計的基層地方自治與中央五權分立的政體制度架構中,國民大會具有顯著意義。1929年,國民黨政權公布《鄉鎮自治施行法》與《區自治施行法》,對鄉民大會、區民大會的地位、職權作了法律規定;1936年,國民黨政權頒布《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該法規定國民選舉代表組成國民大會,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副總統等,國民大會擁有創制、復決、修改憲法及憲法賦予的其他職權;省設省參議會,名額每縣市一人,由各縣市議會選舉之;縣設縣議會、縣政府,由縣民大會選舉之;市設市議會、市政府,由市民大會選舉之[8]。由于缺乏制度運行的生態空間,也由于國民黨政權“以黨訓政”的政治取向,國民大會等政體制度僅停留于文本層面,并未在中國現實運行。可以看出,無論從制度名稱,還是制度的文本設計看,毛澤東與孫中山、國民黨政權所提出的“國民大會”等制度是基本相同的。但有兩點區別:毛澤東強調在民族危亡的抗戰時期,相關制度“現在”就“可以”落實;在制度適用層次上,毛澤東則作了靈活與周密的調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倡導“中國現在可以采取的”政體制度是對《五權憲法》《建國方略》設計藍本的理性回歸,是對國民黨政權現實政體制度的超越。但并未表述理論形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第二,從毛澤東政體制度思想發展脈絡看,抗戰初期與中期的毛澤東客觀理性地認同現實國民黨政權政體制度。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民族矛盾超越了階級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在民族主義的情境下,中國社會政治格局發生變化,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政權再次走向合作,兩黨主導的政體、政治制度也由對峙走向趨同。由于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政黨體系中相對較弱一方,毛澤東主張在中國共產黨主導的區域放棄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推動中國共產黨主導的政體制度向國民黨政權政體制度靠攏,在中國實現民主共和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等政權目標。抗戰前后毛澤東政體制度思想的變化,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一種價值不斷向現實的妥協過程。1937年,毛澤東說:“國民大會要是真正代表人民的,要是最高權力機關,要掌管國家的大政方針。”[9]1938年,毛澤東認為,三民主義共和國“是一個民權主義的國家。國內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級官吏是民選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設立人民代表會議的國會與地方議會;凡十八歲以上的公民,除犯罪外,不分階級、男女、民族、信仰與文化程度,都有選舉與被選舉權。國家給予人民以言論、出版、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質上保護之……我們所謂民主共和國,就是這樣一種國家,就是真正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10]1939年,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致力于“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這種人民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就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共和國。”[11]1940年,“三三制”在陜甘寧邊區與其他抗日根據地普遍開展。1937年至1940年期間,毛澤東還倡導“三民主義共和國”。可見,在1940年《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強調“國民大會”等完全符合他在當時的政體制度思想。
第三,從1940年至1945年中國共產黨的政體制度實踐看,中國共產黨主導的政權建設沒有出現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踐。我們可以這樣設想,如果《新民主主義論》中的“國民大會”等概念相當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等概念,那么,我們很難解釋一個文本與現實的悖論:為何早在1940年毛澤東就主張“中國現在可以采取”,但遲至1948年才在華北解放區出現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前奏與雛形[12]?合理的解釋只能是:《新民主主義論》中的“國民大會”等并不相當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等。在1940年至1945年中國共產黨的政體制度實踐中,各抗日根據地始終實行的是參議會及“三三制”政體制度。毛澤東自己對此態度非常明確。1942年,毛澤東說:“不要把這里(指陜甘寧邊區——筆者注)的參議會看成只是本區的參議會,而要把它看成所有華北華中各根據地的參議會的領袖。”[13]1944年12月,謝覺哉建議陜甘寧邊區參議會更名,毛澤東回信說:“參議會改名,關涉各解放區,中央尚未討論,請暫不提。”[14]事實上,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在1940年至1945年仍處于對未來政體制度形式的探索中,正如謝覺哉日記中所說:“新民主主義政體毛主席已給了原則的指示——民主集中制,但具體形式,究與其他民主國會相反或還有些近似,則有待于研究。”[15]
第四,從“人民代表大會”版與非“人民代表大會”版《新民主主義論》對比看,“人民代表大會”概念體現了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理論新認識,反映了毛澤東建國前后、尤其是建國初期的制度設計構想。1952年,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一文進行了較大的改動。這次改動吸收了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很多新看法、新思維,擯棄了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抗戰特定時期的某些特定提法,契合了建國前后國內的政治形勢與意識形態。如刪去了“作為覺悟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政治代表的,就是各種革命的政黨,其中主要的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一句;將“建立中國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改動為“建立以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16]等。1952年的改動總趨勢是更突出了對中國社會階級本質的分析,強調了工人階級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淡化了資產階級與國民黨的政治作用,彰顯了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在如此背景下,毛澤東將其建國前后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構的設想帶入改動實踐中。建國初期,毛澤東認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政權的適當形式。1949年,《共同綱領》確立了法律形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1951年,斯大林建議中國共產黨盡快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1952年,毛澤東開始考慮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問題。明白這樣的國內政治背景,我們就很容易理解毛澤東對“國民大會”等概念的改動了。補充一點,在《新民主主義論》的那段話下,毛澤東接著說:“‘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須表現在政府與軍隊的組成中,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夠達到這個目的,就叫做政體與國體不相適應。”[17]“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一語,取自孫中山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這大概有助于我們理解“國民大會”等概念的真正含義。
可以說,毛澤東將“國民大會”等概念改動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等概念,這透露出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理論新思考、新解釋,這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新發展。但是,我們絕不能因此而以后來標準來詮釋往昔事實,得出非客觀與非科學的結論。歷史事實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并沒有初步形成理論形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三、《新民主主義論》在政體制度層面的價值考量
正如亞里士多德說:“政治(政體)研究……第一應該考慮,何者為最優良的政體,如果沒有外因的妨礙,則最切合于理想的政體要具備并發展哪些素質。第二,政治學術應考慮適合于不同公民團體的各種不同政體……優良的立法家和真實的政治家不應一心想望絕對至善的政體,他還須注意到本邦現實條件而尋求同它相適應的最好政體。第三,政治學術還該考慮,在某些假設的情況中,應以哪種政體為相宜;并研究這種政體怎樣才能創制,在構成以后又怎樣可使它垂于久遠。”[18]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所提出的“國民大會”等政體制度仍有重要意義,這主要體現于其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若干政體制度原則。
“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原則。西方啟蒙運動以來,“主權在民”取代了“主權在君”,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幟,西方代議民主制度即為其理論的制度化形態。毛澤東吸收西方政治文明的精華,逐步提出國家一切權力歸屬于廣大勞動人民群眾,并將其改造為政權建設的根本原則。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無論如何,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這些階級,或者已經覺悟,或者正在覺悟起來,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19]在制度具體設計中毛澤東提出,中國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度,人民選舉國民大會、省民大會、縣民大會、區民大會、村民大會等,由國民大會及地方大會選舉各級政府。應該說,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充分體現了“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思想。但是,《新民主主義論》中并未明確指出“人民”的內涵與外延,也沒有過多論述人民的民主權利與民主制度設計。部分緣于此,我們說,《新民主主義論》并沒有初步形成理論形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會的重要原則。《新民主主義論》承繼了毛澤東一貫的民主集中制思想。民主集中制范疇,最先是指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原則,而后逐漸推演到政權建設,成為社會主義性質國家政權機關的一種重要組織與活動原則。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在論述蘇維埃政權問題時,將“民主集中主義制度”稱為“新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等;在江西瑞金,中國共產黨人按民主集中制原則組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及其蘇維埃代表大會;1937年7月,毛澤東說“政府如果是真正的國防政府,它就一定要依靠民眾,要實行民主集中制。”[20]《新民主主義論》中說:“這種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這種民主集中制政府,才能充分發揮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對革命的敵人。”并明確說:“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21]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地將民主集中制與政體聯系起來,是毛澤東政治實踐中積極探索民主集中制的新認識。但是,正如有學者指出,相對于根本原則,民主集中制是一種淺層次的原則,是國家機關的組織與活動原則[22]。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并未設想出未來的國家的政體,但毛澤東已充分認識到未來國家政體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所以特別強調民主集中制,甚至將其與未來政體等同。順便說明,我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不是民主集中制。學界關于我國政體是民主集中制觀點既違背邏輯推理事實,也不符合政體運行實踐。事實上,在毛澤東的語境中,民主集中制有多種含義,既可指國家政治制度、政黨組織原則,又可指政府工作作風、國家結構形式等。
總之,《新民主主義論》為后來毛澤東理論形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初步形成提供了理論儲備,它對新民主主義政權的政體理論探索具有重要意義,是毛澤東國家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需特別指出,1945年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受到了其極大的影響,明顯汲取了其思想養料。《論聯合政府》首次提出“人民代表大會”概念,標志著毛澤東理論形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初步形成。
四、簡短結論
正確結論基于精準的材料,原始版本對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至關重要。由于原版難覓,有學者早已指出:毛澤東著作可出兩種版本,一為最后改定本,供學習宣傳;一為原版本,或錄有歷次修訂的版本,供理論與學術研究。這是非常必要的。正是透過版本的迷霧,我們才認定:建國后毛澤東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等概念代替了原來的“國民大會”等概念。《新民主主義論》沒有提出“人民代表大會”概念,并未初步形成理論形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注釋:
[1]參見萬其剛:《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形成與發展》,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年1期。
[2]、[9]、[11]、[16]、[17]、[19]、[20]、[21]《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347、563、672、677、677、347、677頁。
[3]參見方敏:《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的修改》,載《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6期。
[4]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編印1940年版,第19頁。
[5][15]謝覺哉:《謝覺哉日記》(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47頁。
[6]《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頁。
[7]《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8~1309頁。
[8]繆全吉:《中國制憲史資料匯編》,臺灣國史館1991年版,第547~563頁。
[10]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的報告。
[12]參見楊建黨:《華北人民政府時期的人民代表會議制度之考察》,載《人大研究》2007年1期。
[13][14]《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7、249頁。
[18]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76頁。
[22]參見蔡定劍:《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頁。
(作者系廣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中外政治制度專業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