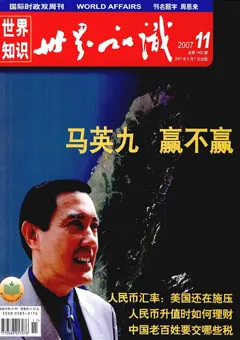匯率低估、外貿失衡與經濟安全
國家經濟安全是指主權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利益不受內外部威脅而保持穩定、均衡和持續發展的一種客觀狀態與主觀感受。由于一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發展階段以及風險防范能力、國民文化心理等方面不同,因此對經濟安全的理解與感受有較大差異。受近代國際關系與當今國際秩序的影響,發展中國家對經濟安全的敏感度普遍要高于發達國家。當今,如火如荼的全球化,正在沖擊與重塑世界各國的經濟安全觀。對于諸多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提高微觀經濟活力(集中在企業國際競爭力)以及維護宏觀經濟穩定性(集中在政府國內經濟調控能力),正成為經濟安全的核心。
透過近現代世界經濟史,可清晰看到,通過調整本國貨幣對外比價來增強本國商品國際競爭力的做法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國際金融無序或失序時期。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之前,如今的發達國家都普遍運用貨幣貶值的辦法來提升本國商品的競爭力。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經濟秩序因為經濟大國的貨幣戰而一度陷入極度混亂,世界經濟由此彳亍不前。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新興經濟體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紛紛效仿發達國家,通過調整貨幣匯率以躋身國際市場。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也沿襲了這一通用做法,使“中國制造”譽滿全球,對外貿易蒸蒸日上,國際收支黑字不斷飆升,外匯儲備連年新高。但就在國人為其沾沾自喜之時,經濟安全風險也悄然而至。
“廉價貨幣”拉動經濟增長不可持續。就國際經驗來看,以“廉價貨幣”促進外貿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是以他國不以牙還牙為前提的,道理很簡單,貨幣都競相貶值,就是沒有“廉價”勝出的零和博弈。戰后,美國之所以容忍西歐、日本以及后來的“四小龍”長期采取“廉價貨幣”政策,是因為有“冷戰”的特殊國際政治格局,而且美國經濟一度具有絕對領先優勢。如今已是斗轉星移,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中國做得有些過頭了,以至于將塵封多年的“重商主義”標簽毫不客氣地拋送給了中國,多方施壓中國必須調整匯率政策,扭轉貿易嚴重失衡,使國際經濟秩序回歸到西方世界可以操控的水平上。綜觀我們的一些部門的表現,似乎國人的呼聲可以不聽,但洋人的臉色不可不看。而且,越來越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正使中國的經濟安全問題越來越容易受制于人。因此,以外貿來拉動經濟增長的策略,遇到了嚴峻的“可持續”問題。
bqO/HfTsiIu3sKiynxB1JA== “廉價貨幣”導致國內經濟失調的狀況正日益嚴重,不斷削弱宏觀調控能力。由于人民幣被低估,價格信號失真,市場機制扭曲,正常配置資源的效率受損。“廉價貨幣”相當于對非貿易部門征稅而用于對外貿易部門的補貼,相當于落后的中西部內陸地區對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的補貼,是損不足以補有余,是劫貧濟富,因此在激勵貿易部門超常發展的同時,抑制了非貿易部門的正常發展,集中體現在服務業發展滯后,內需嚴重不足,就業問題凸顯,地區差距拉大。貿易順差激增,國際收支黑字飆升,流動性嚴重過剩,資產泡沫問題日趨嚴峻,老百姓實際感受到的通貨膨脹也不斷加劇,在市場機制不健全的情形下,宏觀調控越發艱難。例如,去年7月至今年5月18日,央行七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三次提高利率,然而這些緊縮措施并未產生明顯效果。
“廉價貨幣”所贏得的國際競爭力難以持久。透視成功經濟體的國際競爭力,大多建立在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之上,貨幣政策只是輔助手段。長期執迷于由“廉價貨幣”而獲得的競爭力,會使相關企業與行業不思進取,過多過長停留在勞動與資源密集產業,產業結構升級緩慢,整個國家的競爭力難以提高,進而影響在國際分工中的主導性與市場話語權。“廉價貨幣”惡化了貿易條件,“把利潤奉送他人,把GDP留給自己”,而且資源、環境、勞動者健康等方面的代價難以估量。因此,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建立與增強,應著眼于長遠的競爭力而不是眼前的競爭力,是國家整體的競爭力而不是少數行業的競爭力,是綜合品質的競爭力而不是單一廉價的競爭力。
有鑒于此,調整人民幣匯率使之趨于均衡水平,平衡外貿與國際收支失衡,有助于糾正資源配置扭曲,恢復市場機制功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擴大內需,增強宏觀調控的有效性。調整人民幣匯率,使中國的國際競爭力逐漸建立到依靠技術進步、管理創新與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之上。必須注意到,人民幣匯率調整仍然存在相當大的風險,尤其是在日益強大的內外壓力下而被迫拋棄“主動、漸進、可控”原則。但是,人民幣幣值調整比開放金融市場讓美國金融機構長驅直入更加可取,正可謂兩害相權取其輕。更何況,匯率調整進而貿易糾偏已是當前中國經濟安全的內在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