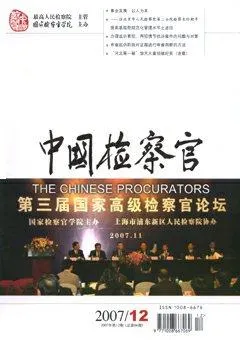開車接應實行過限同案犯之定性
一、基本案情
張某與杜某經預謀來到一平價商店盜竊,杜某負責盜竊,張某在外面車上等待接應。杜某竊得一批手機充值卡(價值人民幣1216元),離開時被店主王某發現,雙方撕扯在一起,杜某拿出隨身攜帶的匕首威脅王某抗拒抓捕。張某看到雙方撕扯在一起,就開車順著杜某跑的方向將車停在距商店不遠的地方,后杜某上車逃離現場。張某堅稱,因為杜某當時背對著自己,并未看到杜某拿刀威脅王某,是上車后聽杜某說的。
二、分歧意見
對張某行為的認定存在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張某構成轉化型搶劫的共犯。理由是:張某在看到了杜某盜竊行為被發現,并與對方相撕扯的情形下,并未直接逃離、亦未加以阻止,而是積極實施了開車接應杜某的行為,己經具有了相機行事的性質,超出了盜竊的共同故意。
第二種意見認為張某構成盜竊罪。理由是:張某在發現杜某被王某抓住,且雙方撕扯在一起時,并未上前協助杜某抗拒抓捕,而是將車開出一段距離后等候杜某上車一起逃離現場,張某不具有轉化型搶劫罪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即張某構成盜竊罪。理由如下:
本案是一起較為典型的共同犯罪中實行過限案件。實行過限是共同犯罪中獨有的內容,其中的“實行”是指實行犯的實行行為,“過限”是指超過共同犯罪故意的界限。綜合起來,實行過限,就是指實行犯實施了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犯罪行為,也即實行犯在共同犯罪故意之外實施的犯罪行為。對實行犯而言,實行過限所涉及的犯罪與其參與實施的共同犯罪絕非同一種犯罪。然而,實行過限作為一種故意犯罪行為,它和實行犯參與實施的共同犯罪往往在時空上聯系比較緊密,多數情況下都難以分割開來,故在司法實踐中容易產生混淆。本案中杜某在盜竊過程中,實施了抗拒抓捕的暴力威脅行為,構成轉換型搶劫是沒有疑義的,但對張某而言則是共同犯罪中的實行過限,張某不具有轉化型搶劫的共同犯罪故意和犯罪行為,不應對過限的暴力威脅行為負責,不構成轉化型搶劫罪。
首先,事先張某及其同案犯不具備盜竊被發現就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脅的共同概括故意。張某與杜某因“想偷點東西”而來到王某的平價商店,在杜某實施盜竊價值1216元充值卡的行為時,張某在外面車上等待接應。應該說,本案的共同盜竊故意很明顯,手段也很確定,就是“偷”,雖然杜某攜帶有匕首,但現在沒有證據證明張某與杜某之間存在盜竊被發現就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脅的共同概括故意。
其次,事中張某不存在犯意的轉化。杜某在盜竊被發現后,為抗拒被害人的抓捕而使用暴力威脅,這表明杜某已經從盜竊的故意轉變成了轉化型搶劫的故意,而張某在偵查、審查起訴以及審判階段都供述了他只看到了杜某盜竊行為被發現,與對方相撕扯的情形,并將車開到杜某逃跑方向的不遠處,接應同案犯的事實。但因背對著杜某并沒有看到其使用匕首威脅抗拒抓捕的情況,這一事實是在張某接應杜某上車后聽說的。這表明張某作為一名盜竊的共犯并未認識到他所參與的共同犯罪的性質已經改變為搶劫,而且,接應杜某是在事先預謀盜竊時就商量好了的,并不因為杜某使用暴力威脅抗拒抓捕,張某接應他,就使得張某的行為具有了相機行事的性質,超出了盜竊的共同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