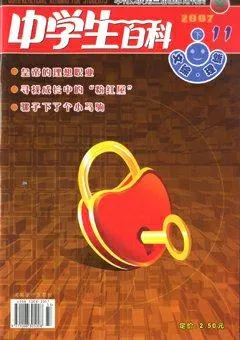龜的結構主義
關于烏龜殼的來歷,有這樣一個故事:
上帝喜慶的時候(我忘了為什么,也想象不出上帝有什么可喜慶的:生日?結婚?升官?)龜沒去,因為它不想離開家。于是上帝大怒,懲罰它永遠也不離開家——它的烏龜殼。
如果這故事當真,那么這次懲罰已經有兩億年之久——差不多在晚三疊世,最早的龜就已經背著它的家飄游四方了。經過兩億年的滄桑之變,龜有充分的時間和充分的理由把這個家弄得更像樣子。你不妨說,它成了個結構主義者,龜殼就是它最精致的結構。
順便說一句,龜殼與“王八蓋子”不是一回事,龜和王八(鱉)是兩類不同的動物,當然,它們是表親——鱉起源于早期龜類。兩種動物的最大區別就在甲殼上:鱉甲即“王八蓋子”是一層骨板,從里面看上去有點像人脊椎和肋條,背甲和胸甲可以分開;而龜甲分兩層,下面是骨板,上面是盾片,胸、背甲由骨橋連為一體。
龜殼就是這樣一個自足、圓滿而適度的結構,它的攻守兼備和進退有據是值得稱道的:它嚴密、堅固,可以有效保護自己,同時四肢和頭尾又能伸出接觸外界,便于運動和取食。這個精巧的結構無疑是十分成功的,它保證了龜最大限度地生存和發展,兩億年來發生了無數腥風血雨的天災人禍,包括讓恐龍全軍覆沒的“大滅絕”,龜卻依然馱著它那溫暖、親切、安全可靠的家優哉游哉地來來去去。不但家族繁盛(1835年,達爾文乘坐著貝格爾巡洋艦來到加拉帕戈斯群島時,漫山遍野的巨龜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它還成了世界上最長壽的動物,這一切不是有賴于龜殼的有效保護和節能功效嗎?如果說,其他動物“更高、更快、更強”,也是出于無奈:它們沒有如此圓滿的體系可以依靠。
當然,這個保護了龜兩億年的結構不可能沒有一點代價:龜殼限制了它,它不可能站起來,不可能兩手合抱,不可能長出尖牙利爪,奔走如飛,它只能爬,在這個星球的漫長歷史中很有耐心地爬。
龜殼帶給它的另一損失是名譽上的,由于某種結構上的相似性,龜替某些人背上了罵名。(人類也會把它和別的什么結構“結構”到一起去,這肯定是龜始料未及的。)雖然這對它并無多少真正意義上的傷害,但“修名之不立”總是個遺憾——盡管這很有點莫名其妙,有點突如其來。
一種結構,就是一種認知世界的方式,它是一條道路,也是一個囚籠。問題是,沒有人可以離開結構,只要他活著,就必須找幾條安身立命、為人處世的原則和方法,而他自己,也就被這些原則和方法規定起來。正如愛默生對海龜的不屑評論所言,海龜的思想離不開它自己,從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可說是一只海龜(當然,不是前面一段中的含義)。
由于緩慢,由于長壽,對于人類,龜的結構主義很有些哲學意味。一個小老太太曾經就烏龜的問題教誨了大哲學家羅素,她告訴羅素:這個世界是馱在一只大龜的背上的。哲學家問她:這只龜又站在哪兒呢?“一只更大的龜背上。”小老太太信心十足地答道。
編輯/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