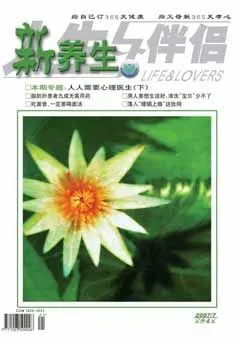難以穿越的廣場(chǎng)
K君是一個(gè)斯文的中年男子,他不管到哪里都需要太太做伴,甚至連上廁所也不例外,夫妻兩人真的到了“出雙入對(duì),形影不離”的地步。但與其說(shuō)這表示他們“恩愛(ài)異常”,不如說(shuō)是“痛苦異常”,要了解這種痛苦,必須從頭說(shuō)起:
據(jù)K君說(shuō),他在25歲時(shí),有一次單獨(dú)走過(guò)康科德廣場(chǎng),在空曠的廣場(chǎng)上,他突然產(chǎn)生一種莫名的驚惶,呼吸持續(xù)加快,覺(jué)得自己好像就要窒息了,心臟也隨著猛烈跳動(dòng),而腿則癱軟無(wú)力。眼前的廣場(chǎng)似乎無(wú)盡地延伸著,讓他既難以前進(jìn),又無(wú)法后退。在全身冷汗淋漓下,他費(fèi)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跋涉”到廣場(chǎng)的另一頭。
他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突然會(huì)有那種反應(yīng),但從那一天起,他即對(duì)康科德廣場(chǎng)敬而遠(yuǎn)之,下定決心以后決不再自己一個(gè)人穿越它。
不久之后,他在單獨(dú)走過(guò)英華利德橋時(shí),竟又產(chǎn)生同樣驚惶而難受的感覺(jué)。隨后,在經(jīng)過(guò)一條狹長(zhǎng)而陡峭的街道時(shí),也莫名其妙地心跳加快、全身冒汗、兩腿發(fā)軟。
因?yàn)樽杂X(jué)有異,他曾接受某位醫(yī)師的治療,但情況不僅未見(jiàn)改善,反而持續(xù)惡化。到最后,每當(dāng)他要經(jīng)過(guò)一個(gè)空曠的地方時(shí),就會(huì)無(wú)法控制地產(chǎn)生嚴(yán)重的焦慮癥狀,以至于他不敢再單獨(dú)接近任何廣場(chǎng)。
有一次,一個(gè)女孩子到他家拜訪,基于禮貌與道義,他必須護(hù)送那位女孩回家。途中原本一切正常,但在抵達(dá)女孩子的家門(mén)后,他自己卻回不了家了。
天色已晚,而且還下著雨,他太太在家里等了五個(gè)小時(shí)還不見(jiàn)他的蹤影,于是焦急地出去尋找他。最后在英華利德橋邊,看到他全身濕透地在那里哆嗦,因?yàn)樗麩o(wú)法穿越那座橋。
在這次不愉快的經(jīng)歷后,他太太不準(zhǔn)他單獨(dú)出門(mén),而這似乎正是他所期待的。但即使在太太的陪伴下,每當(dāng)他來(lái)到一個(gè)廣場(chǎng)邊時(shí),仍然會(huì)不由自主地呼吸加快、全身顫抖,嘴里喃喃自語(yǔ):“麻曼拉達(dá)、嗶嗶比塔科……我快要死了!”此時(shí),他太太必須趕快抓緊他,他才能安靜下來(lái),而不致發(fā)生意外。
到最后,不管他走到哪里,他太太都必須跟在旁邊,連上廁所也不例外。
>>解析:
這是一個(gè)典型的“懼曠癥”病例,它也是畏懼性神經(jīng)官能癥之一。
懼曠癥本來(lái)專指對(duì)空曠場(chǎng)所的畏懼,但精神醫(yī)學(xué)界目前已擴(kuò)大其適用范圍,而泛指當(dāng)事者對(duì)足以讓他產(chǎn)生無(wú)助與惶恐之任何情境的畏懼,除了空曠的場(chǎng)所外,其他如人群擁擠的商店、戲院、大眾運(yùn)輸工具、電梯、高塔等,也都可能是讓患者覺(jué)得“無(wú)處逃”而畏懼的情境。過(guò)去所謂的“懼高癥”與“懼閉癥”等,現(xiàn)在也都屬于“懼曠癥”。
懼曠癥的一大特征是,患者的驚惶反應(yīng)通常是在單獨(dú)面對(duì)該情境時(shí)才會(huì)產(chǎn)生,如果有人做伴就能獲得緩解,甚至變得正常,而且能讓他免除這種畏懼的“伴侶”通常是特定的某一兩個(gè)人。精神分析學(xué)家因此認(rèn)為,懼曠癥可能是來(lái)自潛意識(shí)的需求,患者極度依賴某人,對(duì)他人有嬰兒般的纏附需求,但在意識(shí)層面,他無(wú)法承認(rèn)此一幼稚的渴望,所以就借懼曠癥的驚惶反應(yīng),使對(duì)方有“義務(wù)”必須時(shí)時(shí)和他做伴。本案例中的這位K君,他的懼曠癥從精神分析的觀點(diǎn)來(lái)說(shuō),就是他在潛意識(shí)里對(duì)太太有嬰兒般的纏附需求。
但這種以“功能”來(lái)解釋“原因”的說(shuō)法,無(wú)法獲得普遍的贊同。
事實(shí)上,很多懼曠癥患者均難以從過(guò)去的經(jīng)驗(yàn)中找到令他們畏懼的原因。專門(mén)研究遺傳基因?qū)θ祟?lèi)社會(huì)行為產(chǎn)生影響的社會(huì)生物學(xué)家威爾森提出了一個(gè)出人意料的說(shuō)法,他說(shuō)畏懼癥患者所畏懼的對(duì)象常是早期人類(lèi)生活中所面對(duì)的危險(xiǎn),譬如懼曠、懼高、懼閉、懼暗、懼蛇、懼雷、懼蜘蛛等,如果說(shuō)畏懼癥是環(huán)境或文化制約的產(chǎn)物,那么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危險(xiǎn),譬如核電、汽車(chē)、瓦斯爆炸等,應(yīng)該是更常見(jiàn)的畏懼對(duì)象,但事實(shí)上不然,很少有走過(guò)核電廠或看到汽車(chē)就會(huì)出現(xiàn)呼吸急促、全身發(fā)抖、冒冷汗等自律神經(jīng)反應(yīng)的患者。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人類(lèi),其畏懼反應(yīng)仍然是相當(dāng)“傳統(tǒng)”的——懼曠癥遠(yuǎn)多于懼電癥、懼蛇癥遠(yuǎn)多于懼汽車(chē)癥。威爾森因此認(rèn)為,其實(shí)是進(jìn)化規(guī)劃人腦,使它留意某些危險(xiǎn)情況,但社會(huì)進(jìn)化的腳步遠(yuǎn)快于生物進(jìn)化,生物進(jìn)化還“來(lái)不及”處理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危險(xiǎn),因此,現(xiàn)代人腦中存有的畏懼對(duì)象,仍是幾百萬(wàn)年前遺傳基因所規(guī)劃、謄錄在腦紋里的那幾種“古典”的危險(xiǎn)。
如果我們認(rèn)為神經(jīng)官能癥有體質(zhì)——也就是腦神經(jīng)的生理及生化因素,那么社會(huì)生物學(xué)家的這種說(shuō)法恐怕也不是天方夜譚吧。
據(jù)《心理醫(yī)生》
編輯 / 張秀陽(yá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