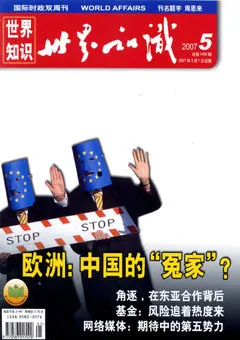美國:影響中日關系的重要因素

張家棟 博士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
中日關系“經熱政冷”的局面已經延續多年了。2006年9月26日,安倍晉三出任日本新首相,在10月8日的第一次出國訪問中就來到了中國,傳達了日本試圖改善中日關系的積極信息。但是,中國與日本之間在歷史問題和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問題上的分歧尚未解決,在歐盟對華武器禁售、日澳軍事關系等方面又出障礙。中日關系仍然步履艱難。
中日雙方雖然經常圍繞著歷史問題和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問題產生爭議,但這只是中日關系中的口水仗,并非新問題,其本身也不是非解決不可的國際關系癥結,更不是兩國的真正關注點。
中日關系的主要問題在于:兩國相互間的認識與政策已經與兩國目前的國家實力狀況很不吻合,而雙方政策的調整又受到美國因素的相當制約。
影響中日關系乃至整個東亞安全格局的一個全新因素,是中國和日本的同時崛起。上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基本上停滯不前,但是其海外投資發展迅速;在政治方面,日本追逐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并試圖在政治、法律和軍事方面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目前已經將防務廳升級為省,并計劃徹底修改和平憲法。日本的這些措施使得中國二戰結束以后60年來首次面臨著一個“政治、軍事上強大的日本”。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日益擴大,國防力量有所增強,中國的利益和影響正在遍及世界的各個角落。這同樣使日本面臨著鴉片戰爭以后150年前所未有的“強大中國”問題,與此相應,“中國威脅論”在日本不斷涌現,“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論”在中國也有上升,兩國陷入到一種安全困境之中。
這一現實需要中日雙方重新定義相互之間的戰略關系,重新制訂外交政策,提升對方在自己對外格局中的地位。但是,由于日本戰后一直執行“美國第一”的政策,日本的對華政策也基本置于日美關系框架之中。1998年江澤民主席訪日前,雙方在擬定《中日聯合宣言》的過程中,日方就曾拒絕采納“中日戰略伙伴關系”這一用語,認為,“戰略”一詞只能用于日美關系,不能使日中關系與其平起平坐。由于美國及其軍事存在是中國和日本都無法擺脫的戰略因素,兩國自然也就缺乏擺脫安全困境的動力,而易受美國牽制。一方面,日本試圖依托日美同盟繼續保持對華安全優勢;另一方面,中國則希望美國能約束日本的軍事企圖。
所以,中日關系中的不正常現象,固然有其歷史等方面原因,但是在根本上卻源于美國壓制下的關系扭曲。對于美國來說,若想維持其在東亞的主導地位,就離不開日本的支持,而要維持美日同盟關系,就必須使日本與中國處于難以解脫的安全困境之中,從而使日本更加依附于自己。事實上,在東亞地區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安全兩難:如果沒有美國的存在,中國與日本可能會陷入某種軍備競賽;由于美國的存在,中國與日本又難以建立正常的雙邊關系。
目前東亞局勢的變化,特別是中國和日本在美國外交格局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既給中日關系帶來了挑戰,也提供了機會。挑戰在于:美國日益將中國明確為潛在的戰略競爭者,將以更大的力度拉攏日本抗衡可能來自中國的戰略壓力,這將進一步牽制中日關系;機遇則在于:中國與日本在美國外交關注中的地位逐漸提高,兩國與美國的關系更加平衡、平等,有利于中日之間建立正常的戰略關系。從歷史上看,中日兩國作為兩個強大的鄰國,成為敵人的代價是非常高昂的。只有兩國都認識到中日關系的重要性,而不是將安全保障寄于第三方身上,才能促進雙邊關系的發展,并從根本上擺脫安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