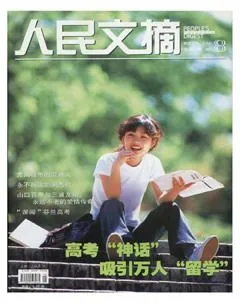傅聰:我是鋼琴的奴隸

音樂的苦行僧
對時間一向吝嗇的傅聰,每天近11個小時與鋼琴“促膝談心”,而且絕不允許任何人打擾。提起傅聰對音樂的癡迷,他的好友方潔說:“他對藝術的追求簡直到了偏激的程度。”她回憶,有一次傅聰去外地講學,馬上就要去機場了,他還坐在鋼琴旁彈得入神,大家都催他,“別彈了,還剩5分鐘了”,傅聰說:“再彈5分鐘,再彈5分鐘。”到了酒店,他就直奔鋼琴,跟旁邊的人說:“給我一杯茶、一塊毛巾。”然后就什么事兒也不理了,為了練琴,他常常把吃飯的時間給擠掉了,練完才吃。他有句話最能概括這種執著:“音樂是我的圣經,我的上帝。”
傅聰始終戴著一副黑手套,只有半截指頭露出。這是因為練琴把手練壞了,五個手指腱鞘隨時有可能裂開,要經常敷藥,打封閉,戴著手套暖和,也習慣了。他說:“我是鋼琴的奴隸,更確切地說是音樂的傳教士,人生的大半輩子消磨在琴上,太辛苦了!但我還沒有退休的計劃。恐怕只有等我的手壞到不能彈的時候,才會停,才會有時間到處看看,到那時恐怕我都走不動了!”
如今,70多歲的傅聰依然出現在世界各國的知名音樂廳里、大師班上,聽眾會完全被他的個人魅力和他彈奏的樂曲所震撼,仿佛鋼琴家不是用兩只手在彈奏,而是用靈魂演繹樂曲深層的內涵。
多彩的情感世界
傅聰一直珍藏著一幅初戀女友的素描畫像。那是早年前往波蘭學習時,女友親筆畫好后送給他的。沒想到,這幅素描畫像竟成了他一生美麗的記憶。1959年,國內政治運動已起,他的父親、著名翻譯家傅雷先生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經常遭到批斗。女友偷偷寫信將發生的一切告訴傅聰,并告誡他不要回來,否則他的藝術就完了!xLHcmrIwkMhFNlimSkQcgNF+Xp/yHtdgJNI9Vq9AYys=正是這封信,促使傅聰出走,并挽救了一個鋼琴大家。
浪漫、唯美的天性讓傅聰經歷了3次婚姻生活。住在倫敦期間,他認識了小提琴家梅紐因的長女彌拉,1960年兩人結婚,生有一子,但十多年后,他終因“東、西方人秉性差異太大”而離婚。1973年,他經歷了極為短暫的第二次婚姻,妻子是韓國駐摩洛哥大使的女兒玄禧晶。這次婚姻很不幸,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們結婚3個月便無法共同生活了……”后來,在鋼琴家魯普的介紹下,他結識了在香港長大的鋼琴家卓一龍,兩人結婚后,傅聰漂泊的“航船”才停靠進了平靜的港灣,現在,一家四口生活在倫敦,其樂融融。
他不敢看“家書”
幾乎所有與傅聰初次見面的中國人都要提到《傅雷家書》。他說:“我覺得許多人老是問我家書的事情,好像我還是小孩子似的。”
其實,他仍然“真”的像個孩子,身為國際級的音樂大師,并不講究派頭,他說“越是高級的酒店我越不愿意住,那么多開關我都搞不清楚怎樣用,我只要房間里有個床墊就足夠了”。傅聰在演出前有個“小秘密”,就是一定要把眉毛修得很整齊,如果眉毛不順了,在演奏時就會分心,他就總覺得自己不對勁兒,一定要在演奏間隙回后臺用小鑷子把眉毛弄好。
雖然“家書”是影響了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的讀物,但傅聰說:“‘家書’其實我從來都不看,我不敢看,每一次看都太激動,整天就沒辦法工作了,太動感情了,不敢看。我覺得‘家書’的意義最簡單來說,就是我父親追求的是一種精神價值,它包含了很多東西,東方的西方的,是一個很博大的精神價值,可絕對不是物欲橫流的世界。”
博學正直的鋼琴大師
傅聰很欣賞父親的一句話:“一個藝術家,永遠要保持赤子之心。真正偉大的藝術家都是孤獨的,只有孤獨才能創造一個新的世界,讓這個新的世界去溫暖、安慰更多孤獨的人。”
如今,傅聰已經自成一“家”——一個性格獨特、博學多才、憤世嫉俗的大鋼琴家。他的身上,有著鮮明的雙重疊影:音樂的傅聰和人文的傅聰。音樂的他,充滿著詩情畫意和幻想,被稱為“鋼琴詩人”,他的琴聲中,有一種純凈、質樸以及神幻般的古典美;而作為人文的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涉獵甚廣,學識淵博,且直言不諱。他的身上,有著矛盾的兩重性:叛逆和順從;細膩和粗獷;詩情與悲壯。
貝多芬曾說過一句名言,音樂是他的最后避難所。這話對于傅聰亦然。
(吳 婷摘自《黨員干部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