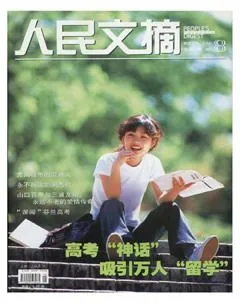李鴻章家族:遲到了半世紀的家族約會
他們曾被罵作“賣國賊”的后代,他們很難感受到出身豪門的優越,為了避免可能受到傷害,他們甚至故意隱瞞自己的出身。有一種豪門望族的后代身份,曾經叫人不敢承認。

膽戰心驚的逃亡歲月
掐指算來,從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算起,上海第一大官宦家族李家迄今已綿延了八代人,共計206年。
所有的豪門家族都會沿用傳統的“詩書傳家”,李氏家族自然不例外。“文章經國,家道永昌”,李家把家族子弟們按資分輩,但起名排序卻截至在“家”字輩。“道”字輩的名字大多由雙名改成了單名。老四房的李家政說:“戰亂時,很多‘家’字輩吃夠了苦,不能讓孩子再被這勞什名字牽連進去。”于是他把本屬“道”字輩的女兒直接取名為李琳,以此保護自己的孩子。
“這實在是沒辦法”,如今已經83歲高齡的李家政回想當年,仍然抑止不住內心的悲傷,他把嗓音壓得很低,情不自禁微微搖著頭。
老人的思緒飄到了半個世紀前,“時局不穩定,日本人到處殺砸搶掠,母親帶著我從安徽安慶老家逃出來,先逃到香港膽戰心驚地兜了一圈,然后再投奔上海的舅舅家。”當時的落腳地就在康定路某老式石庫門房子里,這一躲,就是幾十年。內亂外患,當時許多“國”字輩李氏后代集體大逃亡,抗戰時基本逃離安徽。解放后,有的像李家政一樣隱居大陸,也有很多流散到海外。
驚魂未定,緊跟著就是“文革”、“掃四舊”。家里典藏豐富的藏書樓沒逃過劫難,八十幾箱好書,被撕的撕、燒的燒,轉眼間統統付之一炬,其他值錢財物均無幸免。
就這樣,李氏家族“經”字輩打下的財富,輪到“國”字輩坐享其成和不思進取,加之后來的戰爭和動亂,短短幾年內就徹底敗落。家族史研究學者宋路霞說,很多李氏后代都怕了,從此過上了謹小慎微的生活。
李家政默認這種說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都不肯在單位的資料表格上寫自己是安慶人,以至于單位里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實出身,連兒子女兒也不告訴。禍從口出的事情他看得太多了。
“家”、“道”字輩,唯有低調
歷經磨難,大多數“家”字輩意識到,只有發奮圖強才有出路。雖說當時已有一份不錯的工作,但李家政還是報考了交通大學機械系,響應建設四個現代化的口號,讀機車專業。“我們沒有上一代那么命好,只有自己靠自己了”,完成學業后,李家政順利進入鐵路局當了工人。
盡管時代已經變遷,李家政還是小心翼翼守著自己的真實出身。兒子女兒長大后,他就托人把他們送出國外。如今女兒在加拿大,兒子也公派到德國。上海只有他和老伴,依舊住在石庫門里。
國內的“家”字輩、“道”字輩已經習慣了低調。四房李家錦之女李蕓說:“可能以前被嚇著了,生怕有什么不好。”這么多年下來,連多年的好友都不知道她是李鴻章家族后裔。有意思的是,流散在國外的李氏后代們卻要高調得多。
李蕓說,前兩天有個姓伊藤的日本人特地通過領事館找到他們。原來當年李鴻章曾遭到殺手襲擊,子彈擊中額頭,恰巧是伊藤家族的祖母為李鴻章取彈醫治,于是李鴻章出于感激,為對方題了一幅四字成語,夸贊醫術高明。伊藤家族后人現在東京開了醫院,還把李鴻章的題字掛在院內。他們循著在日本的李氏后人張揚出來的信息,才找到了上海的李蕓。
重編家譜,串起家族溫情聯系
經歷了半個世紀的跌宕,1998年,安徽合肥傳來消息,李鴻章故居終于修整成立了。當時每一房都派代
表去參觀,整個家族自抗戰之后第一次人數湊得那么齊。老四房的李家錦留下了各房聯系人的電話號碼,為重編李鴻章家譜做準備。
在李蕓記憶里,重編家譜的感覺就像做一幅巨大的拼圖,每找到一塊合適都很興奮。“父親就是這樣一點點詢問,結合合肥文物館里的資料,像螞蟻啃骨頭一樣,花了兩年時間編寫了新的家譜。”其中“道”字輩也一律在名字中間加上了“道”,以求輩分準確整齊。
在這個過程中,家譜就像根紅線,把原本疏遠的家族成員一點點拉近,國外不少李氏后人陸續回到中國,敘舊、暢談,彼此越來越融洽。
2004年的大年初四,李鴻章家族后人舉行了遲到了半個世紀的團拜會。當時共有近200位李氏兄弟姐妹出席,如今,年初四的家族團拜會已成為李家的傳統節目。今年春節,李家政的女兒李琳就千里迢迢從加拿大趕回來,陪父親參加聚會,好不熱鬧。
與“道”字輩的尋根熱情截然相反,李氏家族最年輕的“永”字輩們,對家族的感情則相當淡漠。
李家政老人的孫輩,基本上都在國外長大,幾年難得回國一次,和祖輩的感情已經疏遠,更別提讓他們去理解老祖宗李鴻章。
又如李蕓的女兒,20歲出頭,正在上海外貿學院念大學。李蕓說,有時讓女兒去參加團拜會,小姑娘還嫌沒勁不樂意去。因為團拜會上多數是年歲偏高的族人,他們說的家族故事,“永”字小輩從沒經歷過,沒有共鳴。對此,父輩們也很無奈。
(肖 婷摘自《上海壹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