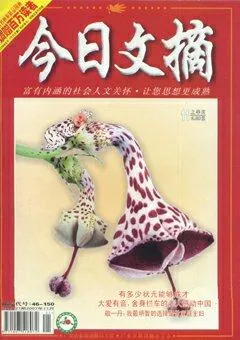一袋面包與一條生命的背后
這是一條讀后讓人痛心疾首的新聞:今年5月18日,沈陽一16歲少女因太餓,在便民店內偷面包被抓獲。店主稱欲要把此事告發至學校后,她覺得無臉面對他人,選擇了自殺來終了一切。(5月21日《時代商報》)
16歲的少女,花季般的女孩,在她的生命之花剛剛吐露芬芳之際,卻選擇了自殺這種決然的方式結束了如花的生命,留給摯愛她的親人無限悲傷。有一首詩曾這樣寫道:“16歲的花季只開一次。”當我們走過青春,回首歲月,常常會感嘆16歲的青蔥歲月是那樣地令人留戀。但這位叫黃娟的16歲少女,花蕾才剛剛綻開,卻被無情的歲月、冷漠的環境所摧殘凋謝。
“死了就死了唄,我們抓小偷還犯法了不成,她死了和我們有什么關系?”一自稱是店內負責人的女子說出了這樣的話。一位目擊者這樣告訴記者,當時黃娟在便民店內雖沒有遭到暴力,但她一直被要求站在便民店一角,店主則在一旁不停地數落著黃娟。隨著店主嗓門越來越大,屋內也聚集來了越來越多的人。黃娟幾次賠禮認錯,店主均熟視無睹,一副輕蔑的模樣。這種冷漠的現實叫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怎么承受得了?這個長期處在饑餓中的少女,沒能禁受住面包的誘惑,而伸出了偷竊的手。假如那位店主能發一點善心,讓她悄悄地拿走,或者輕輕地告誡她今后不能這樣做;假如我們的政府部門能顧及到這些衣食無著落,吃了上頓沒下頓的貧困群體;假如我們都能節儉一點,伸出溫暖之手救濟他們一點,悲劇還能發生嗎?
正值豆蔻年華的少女,應該有陽光般的笑容,但黃娟沒有,她連肚子都填不飽,整天為餓肚子發愁,她還能笑得起來嗎?“就是一袋面包,葬送了孩子的命。”黃娟家的一位鄰居說:“就連走路她都是貼著墻根,好像很害怕的模樣,無精打采,好像吃不飽飯似的。”其實,這是一種饑餓癥的表現,只有貼著墻根走,她才不會倒下。盡管她再餓,也還是堅持著,但她沒有想到自己最終還是禁不住那酥香可口的面包誘惑,倒在一包僅2元錢的面包下。所以黃娟在遺書中就說,她犯下了大錯。“其實她是特懂事理的孩子,如果不是萬般無奈,也不會做出讓自己都無法原諒的舉動。”她的親人向記者展示了一段她記下的遺書內容:“我當時真的很餓,我也知道不好,但是我真的很餓。”這樣的吶喊,難道不讓人心如刀絞,痛定思痛?
《讀者》中曾講了這樣一個異國他鄉的故事:一位母親因貧窮在超市偷了食物給她的孩子們吃,結果被超市保安抓到起訴到法院。經審理,法官是這樣宣判的:“這個女人因盜竊有罪,判罰10美金,而我們社會里還有這樣一個母親需要靠偷竊來養活兒女,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因為我們的冷漠而有罪,每人判罰1美金。”法官說完,第一個站了起來,掏出1美金放在桌上。在場的每一個人都震驚了,人們排起長隊,繳出了每人終生難忘的一筆罰金。
一位花季少女就這樣在現代文明教育的社會中永遠地走了,誰該為她的死負責?一邊是每年吃喝浪費數億元,一邊卻是饑餓的人們。我們的社會讓一個花季少女饑餓得要偷吃,不也是因為我們的冷漠?黃娟的死,拷問著我們的良心,應該說,我們都罪責難逃。只要有一個人餓著肚子,或者站在我們的面前乞討,或者無法忍受饑餓而偷,我們的道德感就要追問。
這是一種社會悲劇,沒有培養起自愛與愛人的基本感情,正是這個悲劇的根源!如果不鏟除這種病態的習氣,不深挖這場悲劇的劣根,這樣的悲劇就會重演。
(文摘感言:關注民生,促進和諧,是我們共同的責任,希望社會有識之士共同努力,擔負起這個神圣的職責,歡迎廣大讀者朋友就相關社會現象進行交流。來稿來函請按照雜志社地址寄本編輯部上半月收,信件請注明“話題討論”,我們將擇優刊出,并給予適當獎勵。) ■
(周舸薦自《觀察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