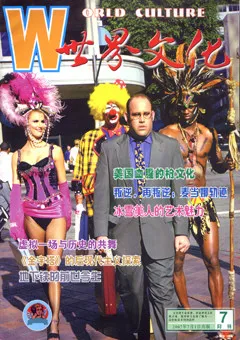真我與映象
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憑借簡約有力的藝術風格和豐富出色的現代派手法,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硬漢形象,也確立了自己獨特的文壇地位。研究海明威的性格,人們總是在他的成名著作中尋找答案,卻常常忽視小說家早期的作品。《印地安人營地》就是海明威24歲左右創作的一部短篇小說,它根植于海明威對生活與人生、生命與死亡的理解,含蓄而又清晰地折射了小說家富于傳奇色彩的人生歷程。
歷經風雨,初涉人生
《營地》著重展現了一個名叫尼克的男孩在承受中不斷思考不斷成長的過程。某個深夜,尼克跟隨醫生父親去營地為一位難產婦女接生。到達以后,尼克難以忍受婦女撕心裂肺的喊叫,懇請父親為她止痛。但由于時間緊迫,父親竟然忘了帶麻醉藥和手術器械。在父親的寬慰下,尼克為了證明自己的勇敢,目睹了一場殘酷的手術——婦女被3個男人死死按住,一把大折刀和一根長長的羊絨縫線……手術結束后,此前受重傷一直臥在婦女旁邊的丈夫卻因無法承受妻子的哀號,已經用刀片悄悄地割喉自殺!這血腥的一幕恰被尼克無意看到,在恐慌與不安中,他弱小孤獨的心靈第一次對生活產生了疑問,小心翼翼地向父親詢問著生死的問題。
故事里,尼克性格敏感而脆弱,有些膽小卻又極力想證明自己。從他身上人們似乎看到了年少時期的海明威。海明威出生在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母親是名鋼琴教師,精明能干,收入不菲。父親則如同尼克的爸爸一樣,是個普通的鄉村醫生。海明威的母親性格異常自負要強,在家庭生活中幾乎居于專斷地位,經常對父親吆三喝四,也常常違背幼年海明威的真實想法,強迫他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甚至多次強迫他和自己的姐姐裝扮成孿生姐妹……這一切使得少年海明威過早地體味到了生活的不幸與艱辛,也注定了母子一生的緊張關系。這個時期的海明威經常感到焦慮憂郁和驚恐不安,渴望被人理解被人尊重。如同他老年時期所說的那樣,“自己常感到莫名地驚慌……晚上睡不著覺……母親的影子總身隨其后……”這種狀況到1928年達到了頂峰,父親的開槍自殺使原本就緊張的母子關系瀕臨崩潰,海明威一度抱怨是母親逼死了父親……
基于這樣的生活背景,海明威在年歲稍長后就立志要擺脫家庭的束縛,決心向母親證明自己是個真正的男子漢。他從小就喜歡打獵、釣魚等挑戰性的運動,總喜歡在男人堆里“鬼混”,甚至聲稱時刻做好了殺人的準備……在走上創作道路后,他開始了極富個性的題材選擇——推崇極限忍耐、體力暴力甚至血腥蠻荒……
縱觀海明威的所有小說創作,有關尼克的就有二十多篇,從尼克是個少年寫起直到他成為健壯的青年。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海明威經歷著與尼克驚人相似的人生歷程,在生活的磨練摔打中漸漸變得叛逆強悍起來,一步步貼近世人熟知的生活硬漢……
錚錚硬漢,直面生活
在《營地》里,海明威還推出了一個人性矛盾復雜的醫生形象。一方面,他醫術高超,對病情判斷準確,治療果斷有效,另一方面,他對待病人卻性情麻木,缺乏人性——僅用一把折刀和羊絨線就堅持進行手術,病人痛苦欲死的呻吟在他看來極其正常,甚至自己“根本聽不到”。此外,手術成功后他的表現也凸現了這個人物的復雜性。一方面,他沉浸在母子平安自己高超醫術得到充分體現的歡快中,但又不愿讓尼克看到自殺男子的悲慘景象。這些又顯示了他人性中自然的平常與善良。可見,這的確是個矛盾的人物,也正因這種矛盾才奠定了他的真實。試想一下,作為一個外出接待急診的醫生,當他診斷出孕婦瀕臨絕境時,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堅持自己的判斷,極力同死神和時間賽跑,用生活的冒險精神努力博取母子平安的頭彩。在此,與其說海明威創造了一個搏擊真實生活的強者形象,不如說他是在自比,這種比較源于他對生活的理解,源于他的那一段段傳奇經歷。
一戰爆發以后,在“拯救人類,拯救國家”的激情澎湃中,海明威以紅十字會車隊司機的身份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著又自愿長期擔任駐歐記者,后來又以記者身份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西班牙內戰……生活與戰場,抗爭與戰斗,堅持與死亡,這些字眼如同深夜營地里的那個手術一樣,充斥著血腥與殘酷。幸運的是海明威用男人的強悍與睿智征服了死亡,頑強地生存了下來。
戰爭結束后,海明威并沒有得到片刻的寧靜與安逸,卻陷入了巨大的生活反差當中:失意,困惑,失落,彷徨,病痛……各種始料未及的局面接連出現,生活再次把他推到了手術臺前。此刻,已經飽受生活滄桑的海明威依然保持著高昂的戰斗姿態,他舉起了紙筆,在發奮的寫作中醫治著生活帶來的生理創傷、愛情創傷和榮譽創傷。我們可以想象,在他生活最困難的時期,他的心中一定回蕩著尼克父親的那句話——是個男人“總應該能承受點什么”……于是,他堅持戰斗著,歌頌著拳擊手的強韌、斗牛士的智勇、獵人的聰慧、軍人的剛烈與酒客的豪放……
命運關口,勇敢抉擇
在小說《營地》里,海明威還刻意對印第安人一家三口的命運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安排:貌似軟弱的母子存活了下來,性格堅強的丈夫卻選擇了死亡。在海明威看來,那對歷經生死的母子是幸運的,她們的結局帶給了我們美好的遐想與期待,但卻要以經受難產的苦痛作為前提。那個自殺男人的結局是悲哀的,但選擇的方式卻是剛強的,他的自殺不是出于對死亡的恐懼,而是出于對生命的敬畏。——這就是海明威的人生哲學:生活總是辨證統一的,戰爭與和平、勝利與失敗、渴望與失望、榮耀與困惑都相距咫尺,甚至連生存與死亡都可以比肩相鄰。顯然,這樣的鋪排與渲染也鮮明地揭示了海明威晚年對人生的思索。
步入老年之后,海明威贏得了巨大的榮耀,鮮花、掌聲、地位、名譽,一切接踵而至,但這些卻阻擋不住他內心的痛苦:生理上病魔纏身,體質日漸衰退,思想也逐漸貧乏,到最后甚至還患上了精神抑郁癥和老年癡呆癥……久治不愈的痛苦深深折磨著海明威,他生活中的所有概念幾乎都雜糅得不分彼此。正如他在一部小說里所說的,無論是在自己少年、青年還是老年時期,無論是在自己成功得意之時,還是在挫敗消沉之際,總感覺有個年輕貌美的古怪女子在身邊倏然顯現,又悄然離去……這個鬼魅般的身影直到這時他才忽然明白,原來就是死亡!于是,海明威站在了人生的另一個十字路口,一如《午后之死》中所說,“一切故事講到相當長度,都是以死結束的”,他知道當平常的戰斗無法戰勝生活的痛苦,留給自己的路只有一條——用死亡同命運做最后一戰!
1961年,一位偏執的老人走上了如印第安男人一樣抗爭命運的另類道路——在自己的書房內舉槍自殺!他用既駭人又撼人卻也感人的方式詮釋了“生存就要戰斗死亡也要戰斗”的哲理,用響徹心扉的兩聲槍響表達了“人可以被消滅卻不能被征服”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