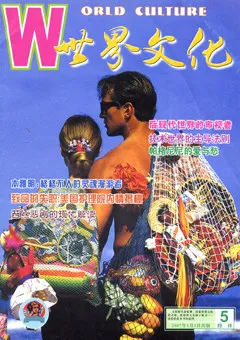后現代世界的審視者
電影《黑客帝國》中,導演沃卓斯基兄弟用以下場景向他們所崇拜的鮑德里亞致以敬意。在電影里,救世主尼奧翻開了一本由鮑德里亞所寫的名為《擬像與模擬》的書,而這本綠色封皮的“書”里面裝的則是一張與全世界人民性命攸關的光盤。
當地時間2007年3月6日,經過長久的病痛折磨,法國著名哲學家、社會學家讓·鮑德里亞靜靜地在他巴黎的寓所中去世。至此,親歷法國“五月風暴”、投身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的“68一代”知識精英集體謝幕,只剩下他們的宗師——99歲的列維·斯特勞斯仍然頑強地活著。
我們普通大眾之所以能夠與這位思想龐雜晦澀、言辭犀利、激勵人心但是也富有爭議的當代法國思想家在現代“消費社會”邂逅,那就得感謝鮑德里亞的書迷——導演沃卓斯基兄弟了。沃卓斯基兄弟正是通過《黑客帝國》中的以下場景向他們所崇拜的鮑德里亞致以敬意。在電影里,救世主尼奧翻開了一本由鮑德里亞所寫的名為《擬像與模擬》的書,而這本綠色封皮的“書”里面裝的則是一張與全世界人民性命攸關的光盤。電影中類似于施洗者約翰角色的孟菲斯對尼奧說:“歡迎來到真實的荒漠”,這句臺詞事實上也是原封不動地掠美鮑德里亞的原話。在拍攝《黑客帝國》的續集時,導演沃卓斯基兄弟(從去年開始變成了姐弟,因為哥哥拉里做了變性手術)還積極地與鮑德里亞聯系,請教他對于劇本的看法,要求劇組所有人都認真閱讀《擬像與模擬》。考慮到這本出版于1981年的書到1994年才翻譯成英語在美國出版,而電影拍攝于1999年,沃卓斯基兄弟已經算是善于追逐理論潮流的了。然而鮑德里亞卻認為這兄弟倆的讀解“主要是基于誤解”,并且拒絕了他們改編劇本的邀請。盡管如此,骨灰級的“黑客迷”們還是將鮑德里亞奉若圭臬,視他為“黑客帝國之父”。
讓·鮑德里亞(1929~2007)出生于法國東北部阿登省蘭斯一個農民家庭。對于自己的童年生活,他后來回憶說:“祖父一生務農。父親是一位公務員,未到年齡就退休了。”鮑德里亞說,在他的家鄉,農民是懶惰的,他們從不拼命工作,只是維持著勞作與自然之間的平衡,農民們付出的,正是由土地和神袛們帶來的東西,他們不需要多生產些什么。他自嘲地說,這是一種懶惰的策略,一種致命的策略,他自己就感染了這種懶惰的世界觀,對市民社會中那種惟利是圖的主動精神、競爭風格表現出明顯的反感,而把懶惰看作是一種“自然”的力量。
但是鮑德里亞并沒有選擇這種鄉村生活,而是成為家庭中惟一一位研究學術的人,一個在后來反對符號統治但又用符號進行寫作的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講,這就是“同父母決裂了”,也是與他的鄉村生活的決裂。當然,這僅是一種“虛擬”的決裂,在他的心靈深處,鮑德里亞還總是存留著對鄉村生活的眷戀,日后的鮑德里亞似乎總是處于這種虛擬決裂的狀態。
這種心態也影響了他后來的理論風格,那即是總是走向邊緣化,總是與現有的東西進行決裂。先是由馬克思,走向后馬克思思潮,然后是同弗洛伊德主義和福柯決裂,接著是同女性主義、生態主義,甚至是后現代主義決裂,在根本上是同“現實”本身進行了決裂。而這種決裂由于上世紀60年代之后那種烏托邦精神的消失,從而走向了一種悲觀的境地。
就世人而言,鮑德里亞更多地被視為是一位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后現代主義思想家。
一位美國學者指出——讓·鮑德里亞是迄今為止立場最為鮮明的后現代思想家之一。而鮑德里亞的追隨者則稱贊他為新的“后現代世界”的守護神。他給后現代場景注入了理論活力,他是新的后現代性的超級理論家。更重要的是,鮑德里亞發展出了迄今為止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極端的后現代性理論,這些理論極具滲透性,影響到了文化理論、現代媒體、藝術等各個層面的話語。
英國學者尼克·史蒂文森在《理解媒介文化》一書中,把鮑德里亞的理論比喻成暴風雪的來臨,是“當前所見到的最精密復雜的對大眾傳播的后現代性批判”。這一論斷給人一個提示,要深入、透徹理解鮑德里亞的“傳播媒介理論”,就必須融入他所描述的那個后現代性的社會文化景觀—— 一個由時尚符號、電子媒體主宰的世界。換句話說,也就是要在一個后現代語境中去把握鮑德里亞的思想。
鮑德里亞也是一個悲觀的媒介技術論者。對傳媒的討論是鮑德里亞理論架構中的主題之一,電視、網絡、廣告都是他關注的焦點。在研究方法上,他采用了符號學、心理分析和差異社會學等研究范式。在信息傳媒手段高度發達的情形下,他直接追問人的本質和人的意義,摒棄了意識形態等諸多社會因素,把傳媒技術和人的最終迷失和墮落作為一對因果關系。這一方面為人們開辟了思考的新疆域,為人們冷靜、理性地重新審視新型文化提供了一條路線。大家普遍認為,他是第一位反思“新型文化”的思想家。但另一方面,過分強調媒介的作用又使他極容易落入客體主義的陷阱中,落入“萬事無一物”的虛無。
雖然研究界傾向于將鮑德里亞定位為一個后現代主義者,但鮑德里亞自己卻不認同這種看法。他說:“對于這種‘后現代的’詮釋,我不能做什么,那只是一種事后的拼貼。在擬像、誘惑和致命策略這些概念里,談到了一些與‘形而上學’有關的東西(但也沒有想要變得太嚴肅),而‘后現代’則把它轉化為一種知識界的流行效應,或者是因為現代性的失敗而產生的征候群。由此來看,后現代自己就是后—現代:他自己只是一個膚淺模擬的模型,而且只能指涉它自己。”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更愿意把鮑德里亞看作是一位文化思想家,他認為,在所謂“后現代主義是當代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論證過程中,鮑德里亞的思想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伊哈·哈桑則“將他歸入政治哲學家一類,名列馬爾庫塞之后,但位居哈貝馬斯之前”。如此這樣排名,應該與鮑德里亞早期的“符號馬克思主義”分析消費社會有關。凱爾納在《后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中則把鮑德里亞作為一位形而上的詩意哲學家來進行定位,并且重點批判了他后期的虛無主義哲學。到底把鮑德里亞放入怎樣一個理論坐標里去考察?學者們的眾說紛紜沒有一個定論。
有人問鮑德里亞:“您是哲學家、社會學家、詩人,以上皆非或以上皆是?”鮑德里亞回答:“我既非哲學家亦非社會學家。我沒有遵循學院生涯軌跡,也沒有遵循體制步驟。我在大學里教社會學,但我并不認為我是社會學家或是做(專業)哲學的哲學家。理論家?形而上學家?就極端的角度而言才是。人性和風俗德行的思索者?我不知道。我的作品從來就不是大學學院式的,但它也不會因而更有文學性。它在演變,它在變得比較不那么理論化,也不再費心提供證據和引用參考。”
其實,這種理論歸屬的流變性和透明感,不僅反映了鮑德里亞整個理論發展的軌跡,也為把他最終定位為后現代思想家作了很好的注釋。他的理論中充滿了對同一體系、總體化的拒斥,崇尚差異性,強調瞬間感的話語。他的敘事體系缺少嚴密的理論論證、常常流于空洞的說教,而且行文時思想跳躍性強,文字怪誕,使我們在理解他的思想時會遇到不小的障礙。另外,對符號現象的分析是鮑德里亞的理論基點,符號結構體系支配著現實世界,擬像、仿真是符號結構支配的形式和手段,在后期,鮑德里亞甚至把這種符號結構用“全能符碼”這一抽象的概念來描述,有人認為,鮑德里亞的這種做法實際上以一種“總體性”去取代另一種“總體性”,理論上的悖論存在于他所信奉的那種反總體化的觀念中,這種悖論同樣也存在于其他許多后現代理論家的理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