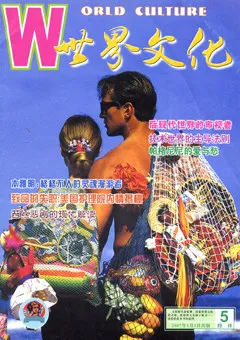“漩渦”中的龐德
伊茲拉·龐德是美國現代主義詩歌的先驅,對20世紀美國詩歌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20世紀初,他曾先后發起了“意象主義”和“漩渦主義”的文學運動。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他卻因自己在戰爭中的言行把自己置于了政治與文學的真正漩渦當中。
龐德第一次處于漩渦之中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他被美國司法機關指控有叛國罪。圍繞著這一指控,在美國產生了關于他命運的廣泛爭論。這一事件的根源是龐德在二戰期間在意大利的一系列不理智的行為。這幾乎是一種空前的叛國罪,因為用廣播為敵對國家做宣傳而被指控的人可以說以前還沒有過。
龐德1924年來到意大利,在此后的很長時間里,他贊同法西斯主義,認為只有在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的領導下,世界才會和平,才會變得更安全。他把羅馬-柏林軸心看作是“林肯時代以來第一次對富人政權的嚴厲打擊”。他仇視猶太人,反對美國參加歐洲戰爭。早在1936年,龐德就開始在意大利電臺發表講話,談他對經濟和政治的看法。1941年1月,他的一檔固定節目開播,名為“美國時間”,每周播放一次。他在廣播中不斷攻擊美國和英國,為意大利和德國辯解。他抨擊羅斯福政府和美國模式。他甚至說應該絞死羅斯福和幾百名猶太人。即便在意大利向盟軍投降、墨索里尼僅僅在意大利北部作為德國的傀儡苦苦支撐之后,他仍然非常堅定地忠于墨索里尼,繼續在米蘭進行他的宣傳廣播。但是龐德的表現似乎有些過頭,他的胡言亂語甚至引起意大利政府官員的懷疑,以為他是美國派來的特務。1941年年底美國參戰后,龐德的這些廣播成為叛國行為。1943年,他在美國被指控叛國罪。
1945年5月3日,二戰在歐洲的最后一周,他在拉巴洛的家中被意大利反法西斯游擊隊員抓獲。他匆忙拿了一部漢英對照的儒家經典《四書》和一本中文詞典,便跟著游擊隊員離開了家,他不知將被帶往何處,但卻想到了被處死的結局。他被送到美國在比薩設立的懲戒訓練中心,這實際上是一座勞改營,是專門讓那些犯重罪的美國士兵通過勞動訓練進行改造的地方。龐德被關在一個露天的鐵籠子里,這是用來關押最嚴重的犯人的。他后來在《比薩詩章》中稱其為“猩猩籠子”。龐德在這個籠子中生活了25天,白天要經受陽光的烘烤,夜里還要被燈照個通宵,因此身心都受到嚴重損害,被轉送到醫療營,正是在這里,他開始了《比薩詩章》的寫作。
當年11月,龐德被引渡回美國。他被指控犯有16條叛國罪行。他未來的命運在美國引起了人們的爭論。剛剛經過大戰的美國人仇視叛國的情緒還很高,許多人要求判處這位美國最有名的詩人死刑。而他的朋友們,包括著20世紀一些最偉大的作家,開始擔心他會被處死。其中,海明威非常擔心龐德這位曾經大力幫助提攜他的老朋友的戰后命運,因此提議用“精神錯亂”為理由來為龐德進行辯護。這個主意得到很多龐德和海明威文學界的以及在政界的朋友的支持,并且通過律師也得到了龐德本人的認可。幾天之后,4位知名精神病醫生簽署報告,做出如下描述:怪僻,易怒,以自我為中心,狂想,注意力不能集中。結論是:心智有缺陷,不能勝任聽從正當建議或者具備自我辯護方面的普通常識。據此,陪審團認為他精神失常無法出庭,因此他并沒有受到審判,而是被送到了華盛頓的圣伊麗莎白精神病院,那是專門為患精神病的罪犯開設的醫院。當然,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精神失常,是不是他的朋友們以及醫生為了使他免于受審而耍了什么花招,到現在也沒有定論。
雖然被監禁在精神病院,但龐德繼續著《詩章》的創作,同時還翻譯了三百多首中國詩歌,1954年,這些譯詩由哈佛大學出版。在此期間,很多拜訪者來醫院看望他,其中包括查爾斯·奧爾森、羅伯特·洛威爾、T·S·艾略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艾倫·金斯伯格等文壇名人。
龐德再一次置身漩渦是在1948年美國第一屆伯林根詩歌獎的評選中。這個獎項是由時任美國國會圖書館顧問的詩人艾倫·塔特提議設立的,具有政府性質。國會圖書館專門為此成立了一個美國文學委員會,成員都是名家,包括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艾略特、自白派詩歌創始人羅伯特·洛威爾、獲得普利策詩歌與小說兩項獎的羅伯特·佩恩·華倫、W·H·奧登、艾倫·塔特、康拉德·艾肯、凱瑟琳·安妮·波特、保羅·格林等14人。在這14人中,投票反對龐德獲獎的只有兩位,一位是猶太詩人0b1e1b85c71e0d59844f772e44fc7970卡爾·夏皮羅,他的理由有二:其一,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本人是猶太人,不可能把這一獎項授予一名反猶主義者;其二,他認為這位詩人的政治哲學與道德哲學最終玷污敗壞了他的詩歌,降低了它們作為文學作品的價值。另一位是凱瑟琳·加里森·查品,她投反對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是當時美國司法部長的妻子,她認為把這一政府性質的獎項頒給一名背叛自己國家的人是極為不妥的。而其他12位委員卻一致站到了另一面,他們都認為,無論龐德在政治上表現如何,他在詩歌方面的貢獻都超出他的政治錯誤。
1949年2月20日,《紐約時報》刊登了龐德獲得第一屆伯林根詩歌獎的消息,引起了各方的爭議。大部分人對此表示憤慨,另一些人則認為這種把對審美的追求與政治分開正是這個國家自由與理性的表現。爭論在6月開始進入白熱化,普利策詩歌獎獲得者、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赫利俄在《星期六文學論壇》上發表文章,不僅抨擊龐德獲獎一事,還同時暗示伯林根基金會與法西斯分子有關。此舉引起軒然大波,評審委員會嚴正聲明他們與法西斯分子毫無關系。國會圖書館館長也出面否認評審委員會有任何過錯,并強烈批評了赫利俄和《星期六文學論壇》。7月底,一位收到這篇文章的紐約議員在眾議院會議上要求對把獎頒給龐德一事進行調查。他認為文學問題應該由文學界來處理,但國會有權了解評審委員會是否正確代表了美國人民的意志。評審委員會發表了一份長達72頁的聲明,來反駁赫利俄的觀點。結果,國會既沒有進行調查,也沒有撤消給龐德的獎,只是決定頒發文學藝術方面的獎項不應該再帶有政府性質。從1950年的第二屆起,伯林根詩歌獎改由耶魯大學頒發。
也許問題的關鍵在于伯林根獎授予的對象是龐德這個人還是《比薩詩章》這部作品。選擇龐德作為伯林根詩歌獎的第一位獲獎者,當然是與《比薩詩章》的偉大藝術成就分不開的,但同時也很難說其中沒有政治目的。有人指出,獎項是給龐德這個人的,而且是通過秘密協商得出的結果。這似乎也并非沒有根據。曾經擔任過助理國務卿的著名詩人邁克利什曾經談起過1948年6月的一次會議,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這一點(但他沒有參加這次會議),那次會議的與會者包括艾略特、E·E·卡明斯、奧登、塔特等人,他們共同商討出一個設想,在國會圖書館設立一個新的詩歌方面的獎項,通過名人組成的評審委員會授獎,而委員們要選擇龐德作為第一位獲獎者,由此改變他的艱難處境,同時把政府尤其是司法部置于非常尷尬的地位。與這一方的觀點相對,國會圖書館人員聲辯,該獎項是授予《比薩詩章》的,而不是授予龐德的。他們認為,“如果允許除了詩歌成就之外的因素來影響我們的決定的話,那將破壞這一獎項的重要意義,并且從根本上否定文明社會賴以生存的、客觀看待問題的原則的正確性。”
對于這場爭論,著名文學批評家歐文·豪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我們不可能只把龐德作為一名詩人,而不首先把他看作是一個人來褒獎他。他認為這件事情是與道德心有關的:把這一文學獎項授予龐德首先應該是對他作為一個人的褒獎,因此也就應該是對他的道德行為的褒獎。對他進行褒獎,也就意味著把他看作是一個具有正常的、得體的、充滿敬意的人際關系的人,這意味著公眾友愛之手的延伸。豪也承認,嚴格把詩人的詩歌與詩人的人格區分開來是很難把握的,因為在一個人的美學思想和人生價值之間是很可能互相抵觸的,在這種情況下,生活現實必須優先于文學來加以考慮。
事情的結果表明,即使評委會委員們確實有政治目的,要向政府施壓以便早日釋放龐德,他們的目的也并未達到。直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許多有影響的名人和媒體又發起運動,呼吁釋放龐德。經過海明威、艾略特、弗羅斯特等人的多方努力,1958年4月18日,龐德在被關押十二年多之后,他叛國罪的指控被取消,他終于走出精神病院。
同年6月30日,他又來到了意大利。到達那不勒斯時他還朝著記者們行了一個納粹禮。但是,在這古老而靜寂的歐洲,龐德逐漸地擺脫了自己的憤怒。他一直在繼續著他的《詩章》的創作。在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后,他似乎開始對自己過去的行為表示后悔,對一些前來拜訪他的人承認自己做錯了。1967年,他在與金斯伯格見面時說:“我很慚愧,我犯的最嚴重的錯誤是反猶主義,那是一種愚蠢而狹隘的偏見。”
1972年11月1日,龐德在威尼斯病逝,就在前一天,他剛剛度過自己87歲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