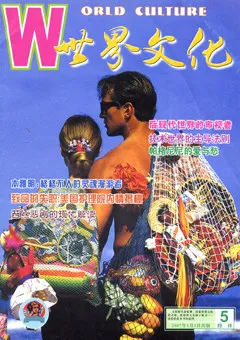命運多蹇的萊蒙托夫
米哈伊爾·尤里耶維奇·萊蒙托夫(1814-1841)是繼普希金之后俄國又一位偉大詩人。萊蒙托夫1814年生于莫斯科。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在塔爾哈內度過的。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天資聰穎,通曉多種外語,在藝術方面也很有天分。后來考入莫斯科大學。經過一段時間學習后轉入圣彼得堡近衛軍騎兵士官學校。1837年1月27日普希金因受匿名信的侮辱,而與法國大革命的逃亡者、禁衛軍官丹特士進行決斗。普希金在決斗中受了重傷,29日逝世,死時38歲。萊蒙托夫聽到這個消息后悲憤至極,當即寫下了著名的詩篇《詩人之死》。詩人對殺害普希金的兇手投出了匕首般的詩句,激怒了沙皇,震驚了整個社會。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親自安排下,他被流放到高加索。由于外祖母的奔走,詩人于1838年4月回到彼得堡。1840年2月有人煽動法國公使的兒子巴蘭特與萊蒙托夫決斗。決斗中對手沒有擊中,萊蒙托夫朝天放了一槍,但仍被第二次流放高加索。1941年7月15日,萊蒙托夫在皮亞季戈爾斯克市近郊旁的馬舒克山麓,由于不值一提的原因跟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沙皇軍隊的退伍軍官馬丁諾夫進行決斗。萊蒙托夫沒有開槍,而馬丁諾夫一槍擊中了萊蒙托夫的心臟,當場身亡,死時只有27歲。他的創作天才還沒有充分展示。但是萊蒙托夫在短暫的一生中創作了四百多首抒情詩、30部長詩,以及《假面舞會》、《當代英雄》等戲劇作品和小說。他的創作反映了19世紀30年代俄國先進人士的孤獨、憂郁和叛逆精神。痛苦、悲觀絕望與烈火般叛逆激情的融合是萊蒙托夫作品的獨特風格。
萊蒙托夫不僅是俄國文學史上,而且是世界文學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
即使不是全部,但是他的童年時代對萊蒙托夫許多命運之謎作了回答。童年不是簡單地感覺到存在于詩人的創作之中,而且賦予他的許多作品,可以這樣表達:略帶點苦咸味。
而問題不僅在于未來的詩人過早地失去了母親,雖然這也影響了他的處世態度,也不在于他一生中跟父親只見過幾次面。災難和倒霉的事,幾乎從他降生之日起就一直伴隨著他。
據說,給他母親接生的婦產科女醫生看著新生的嬰兒,不知為什么竟說這個孩子將死于非命。她是從哪兒悟得的,簡直是個謎……
萊蒙托夫自幼體弱多病,長期備受疾病的折磨,痛苦萬分。正如詩人的一位親戚說的:“他像患瘰疬病的孩子,身體十分虛弱。”當我們了解詩人童年多病體質的細節,似乎覺得跟畫像上出現的萊蒙托夫年輕漂亮的驃騎兵的形象不大相符。但是我們不應忘記,甚至最有才能的人都跟我們所有的人一樣,都是由同樣的肉體組成的。更不用說我們的主人公終于不僅活下來了,戰勝了自己的疾病,而且成為體格強壯、堅韌不拔的人。比如在馬術和技能方面,他敢于跟倔強的山民徒手格斗,這一點他遠遠勝過本團的許多軍官。然而,甚至這些表現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他多病童年的反彈……
有一次,詩人說他自己:“我是苦難的兒子……”他指的不是肉體上的痛苦,而是心靈和精神上的痛苦。實際上受生活環境支配的幼小的萊蒙托夫經常處在他的父親與外祖母伊麗莎白·阿列克謝耶夫娜·阿爾謝尼耶娃的矛盾沖突中間。外祖母從一開始就不喜歡這個女婿,在她的眼里,他是個無用而輕浮的男人。自女兒死后她簡直就是仇視他,要求他永遠離開塔爾哈內。他事實上失去了對兒子的一切權利。
對于外祖母應當特別說一說,因為她對未來的詩人體力和精神上的成長有很大影響。她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流傳到我們今天對她的評語說她是“一個具有特立獨行、百折不回性格的女人,習慣于支配別人。她的特點是人長得很美,出身于古老的貴族門第,具有典型的老派的地主婆的個性,同時喜歡對任何人當面直言不諱,哪怕是叫人痛苦難堪……”然而無論是美貌還是金錢(她作為世襲貴族的財富有:600個農奴,塔爾哈內的美麗莊園,領地上有好幾個村莊)并沒有給她帶來幸福。一開始就生活在類似慢性自殺的不正常的環境中。她的丈夫米哈伊爾·阿爾謝尼耶夫過早地辭世。她的惟一的女兒、詩人的母親遭遇不幸的婚姻也從生活中消失了。這個堅強剛毅的女人還能有什么作為呢?除了外孫米申卡,她再也沒有什么親人了。現在他是她生命中的惟一慰藉。
伊麗莎白·阿列克謝耶夫娜為了心愛的外孫幾乎做到無微不至。譬如米申卡表示希望有頭小鹿,外祖母立即叫仆人來并給他們些錢,還事先說好,要他們沒有買到鹿之前不要回塔爾哈內。下一回外孫又提出要騎著小馬到外面去兜風。
自然外祖母為了讓外孫能夠受到良好的教育,又請了家庭教師照管和培養他。請德國的女教師教他德語,請俄羅斯化的法國人教他法語。但是在外祖母心中占首要地位的還是外孫的健康。曾經兩次(有的資料上是5次)伊麗莎白·阿列克謝耶夫娜把外孫帶到高加索皮亞季戈爾斯克去洗礦泉。不難想象,她和外孫必定一起去玩過心愛的地方馬舒克山麓——當時誰會知道,地球上的這塊地方,日后成為她的外孫命喪之地。
經常讓外祖母擔心的另一件事是:雖然米申卡健康的活著,但是不知什么原因,無名的憂愁常常無緣無故地向他襲來。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她的吩咐,兒童室里來了幾個由仆人扮演的化了裝的童話中的角色,盡管他們唱呀,跳呀,千方百計地給小少爺尋開心,可是他根本無動于衷。
一句話,假如有一天小外孫要外祖母的命,她也會毫不猶豫地交出來。但是這種沒有分寸的愛,只能給孩子的心靈帶來同樣的傷害,甚至可能對此產生自發的仇恨。伊麗莎白·阿列克謝耶夫娜的這個帶有點神經質的、生來易沖動的外孫,開始一點點感覺到自己是這世界的中心。在游戲時,根據他一個同曾祖的兄弟回憶說:他無耐性,好發號施令,具有一種病態的自尊。他喜歡看青年的仆人進行拳斗,他竭力激勵他們,忽而用甜餅,忽而用一杯伏特加酒來款待勝利者。
也許這沒有什么,伊麗莎白·阿列克謝耶夫娜的外孫從嬌生慣養的小少爺逐漸會變成自負的、冷酷無情的貴族老爺,當時這在俄羅斯并不少見……但是,謝天謝地,這樣的事在萊蒙托夫身上并沒有發生!因為嬌養慣了的男孩的任性和許多古怪的念頭僅僅是偉大詩人童真的一面,另一方面更具有分量的是在他身上年復一年地表現出的多才多藝的天賦和精力充沛的激情滿懷。這個黑頭發的男孩(在他的額頭上有一綹白發),有一雙敏銳、聰明、淺藍色的大眼睛。他4歲了才剛剛學會說話,令人驚奇的是他喜歡說韻語,稍后又著迷似地沉湎于寫生畫、建筑和音樂。讓外祖母特別高興的是外孫非常喜歡看書。在掌握了德語和法語之后,他讀西歐的古典文學作品讀得入迷。有一個時期,年輕的萊蒙托夫在考慮自己的志向時,突然不知為什么又迷上了數字。
外孫一天天長大了,他的愿望常常與外祖母的想法格格不入。舉例來說,有一天他發現塔爾哈內許多農舍沒有煙筒,冬天室內燒不暖。他要求伊麗莎白·阿列克謝耶夫娜給這些房子的主人買磚頭,以便讓他們自己砌煙筒。是否可以說,外祖母滿足了心愛的外孫的“任性要求”?
年輕的萊蒙托夫剛剛顯露出的詩歌天才令人矚目,本來頑皮的少年突然不與人交往,不顧外祖母對他焦慮不安的忠告,他常常獨自到村外田野、森林中去喃喃自語地寫詩(不是偶然地,他在第一首詩《切爾克斯人》中作了這樣注腳:“寫于琴巴爾的橡樹旁”)。誠然,他初期的詩作是稚嫩的,且帶有模彷的痕跡。他似乎是寫給自己看的,不肯輕易出示別人。然而所有的詩人都是這樣開始的:偉大的詩人是這樣,平庸的詩人也是這樣……而過了幾年之后,似乎由數量到質量過渡的規律完全取得了一致。在他的創作中產生了令人目眩的爆炸性的成果。在俄羅斯文學的天際出現了一顆耀眼的詩歌新星——米哈伊爾·萊蒙托夫。
但是俄羅斯還沒有來得及從普希金突然辭世之后清醒過來,高加索又向首都傳來了來自馬舒克山麓的噩耗。眾所周知,為《詩人之死》而極端仇恨萊蒙托夫的沙皇尼古拉一世聽到這個消息后惡狠狠地喊出:“狗該有狗的死法”但是當他醒悟過來以后,也不得不向自己的親信們承認:“諸位,剛剛得到消息,那個能夠代替普希金的人死了!”
對阿爾謝尼耶娃來說,命運給她的打擊,沒有比外孫之死更可怕的了。她是那樣的愛他,可以說世上沒有人像她那樣愛他。飽含著極度的悲傷,外祖母哭壞了眼睛,由于過度流淚,哭得松弛的眼瞼不再聽使喚,為了看一眼使她厭煩的世界,她不得不用手指稍微提起眼皮,撐著衰老的病體,用盡最后的力氣(因為她已近80高齡了)把偉大外孫的遺骸運回到塔爾哈內。4年后,外祖母在凄涼孤寂中辭世,讓自己的遺骸永遠地守護在外孫的墳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