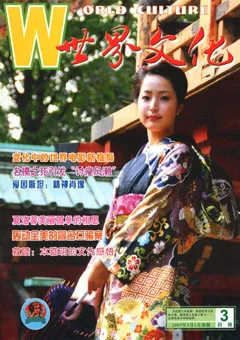變化中的世界電影新格局
電影作為一種藝術(shù)形式,經(jīng)歷了一百多年的發(fā)展,形成如今獨(dú)特的景觀,它綜合多種藝術(shù)形式從而在時(shí)間和空間上展現(xiàn)其魅力所在。然而隨著上世紀(jì)60年代末法國新浪潮的發(fā)展,由《電影手冊(cè)》諸多編輯提出的“作者論”強(qiáng)調(diào)了電影創(chuàng)作中導(dǎo)演對(duì)藝術(shù)形成起到的重要作用,電影的風(fēng)格形式和主題內(nèi)涵便和導(dǎo)演的作者身份聯(lián)系起來,由此導(dǎo)演這個(gè)職業(yè)屬性具備了藝術(shù)家的特質(zhì),而不僅僅是電影產(chǎn)業(yè)中的簡單的從業(yè)人員。當(dāng)導(dǎo)演對(duì)其作品具有很高的把握能力,或者能夠在個(gè)人創(chuàng)作和制片商要求的矛盾中形成某種平衡,那么他便可以向作品浸注個(gè)人風(fēng)格并表達(dá)內(nèi)在思想和人文關(guān)懷。此外,根據(jù)導(dǎo)演的個(gè)人經(jīng)歷和其所在的社會(huì)背景,其電影作品勢必呈現(xiàn)出與其周遭環(huán)境、地緣政治、社會(huì)歷史相關(guān)的種種內(nèi)在。
然而,從上世紀(jì)80年代開始,世界電影走向越來越工業(yè)化,新好萊塢的崛起使得美國迅速確立了其世界電影中心的位置,其作品不僅在商業(y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美國導(dǎo)演西科塞斯、科波拉、阿爾特曼等人的作品的藝術(shù)價(jià)值也得到了國際的認(rèn)同,為獨(dú)立電影在好萊塢工業(yè)環(huán)境下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盡管在商業(yè)電影方面,文化殖民主義和國際化使得電影發(fā)展呈現(xiàn)出單調(diào)枯滯的局面。但是對(duì)于那些有能力呈現(xiàn)個(gè)人風(fēng)格的電影導(dǎo)演而言,不僅國際融資方式可以突破本國電影制度的限制,而且國際交流的頻繁使得文化呈現(xiàn)多元化發(fā)展。因此,從上世紀(jì)90年代中后期開始,世界電影呈現(xiàn)出一種嶄新的格局:在信息和傳媒為主導(dǎo)的現(xiàn)代社會(huì)中,先鋒與傳統(tǒng)、藝術(shù)與商業(yè)已經(jīng)悄然融合起來,導(dǎo)致電影的形態(tài)和內(nèi)置發(fā)生了更加傾向于人本主義的文化特征,而這種傾向于消除商業(yè)和藝術(shù)二元對(duì)立的趨勢,正在潛移默化的深深改變觀影人和創(chuàng)作人對(duì)于電影的種種觀念。
昂首闊步的美國電影
美國電影的全球市場覆蓋率占到70%。在有的國家和地區(qū)占到90%,通過全球化的目標(biāo)、多元文化的傳統(tǒng)、樸素的價(jià)值和娛樂性的表現(xiàn)方式,實(shí)現(xiàn)了其在全球電影產(chǎn)業(yè)份額當(dāng)中的巨大比重。然而,在好萊塢的疆土上總是存在著堅(jiān)持自己個(gè)人風(fēng)格的獨(dú)立導(dǎo)演,在影片制作中維持比較大的空間上進(jìn)行自由的個(gè)人創(chuàng)作。西科塞斯、科波拉等人在七八十年代為美國電影贏得了巨大的藝術(shù)成就,在諸如《憤怒的公牛》、《現(xiàn)代啟示錄》、《陸軍野戰(zhàn)醫(yī)院》等優(yōu)秀影片中,導(dǎo)演呈現(xiàn)了獨(dú)特的美國黑色電影的特征,并在其中對(duì)于美國傳統(tǒng)價(jià)值進(jìn)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隨后出現(xiàn)的大衛(wèi)·林奇、科恩兄弟、吉姆·賈木許等導(dǎo)演在具有強(qiáng)烈個(gè)人風(fēng)格的影片中注入了奇特的美國景觀,從而在國際電影節(jié)上贏得了無數(shù)榮譽(yù)。在這些具有強(qiáng)烈獨(dú)立精神的作者的作品中,人物、性格、故事,這些好萊塢至關(guān)重要的元素失去了原本的含義,通過解構(gòu)和反諷而成為描述環(huán)境和歷史的砝碼。這種帶著魔幻色彩的黑色風(fēng)格,與好萊塢娛樂片截然不同的敘事手法、夸張變形的人物形象,營造了一個(gè)又一個(gè)獨(dú)具魅力的個(gè)人影像世界。
在新世紀(jì)諸多新銳導(dǎo)演中,蓋斯·范·桑特應(yīng)該是出道最早的一位,在上世紀(jì)80年代末,他就協(xié)同托德·海恩斯、提姆·伯頓等人在紐約掀起一片“新酷兒電影”熱潮,然而到90年代沉寂了將近10年左右之后,在新世紀(jì)推出的三部電影(《杰瑞》、《大象》、《最后的日子》)在歐洲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以極簡主義風(fēng)格,深厚的哲學(xué)觀念和充滿遲滯感的長鏡頭美學(xué)贏得了歐洲影人的好評(píng)。導(dǎo)演亞歷山大·佩恩的影片則具有深厚的歐洲人文傳統(tǒng),畢業(yè)于斯坦福大學(xué)的他身上具有強(qiáng)烈的知識(shí)分子氣息,其作品也具有很強(qiáng)的文學(xué)傾向。在最新的兩部影片《關(guān)于施密特》和《杯酒人生》中,佩恩流露出強(qiáng)大的文學(xué)技巧,其作品具有法國導(dǎo)演侯麥的風(fēng)格,通過把事件小型化,用最簡單、最平實(shí)也最普通的方式對(duì)社會(huì)進(jìn)行反思。而對(duì)于同樣具有強(qiáng)烈歐洲傾向的導(dǎo)演韋斯·安德森而言,他在短短的四部影片中,就顯露了驚人的電影技巧和獨(dú)特的姜學(xué)觀念。在去年人選柏林電影節(jié)的《海海人生》中,以其怪誕而炫美的視覺效果將安德森的冷面幽默發(fā)揮到一個(gè)高度。電影散漫的結(jié)構(gòu),慵懶的節(jié)奏和卓然的幽默感是安德森一貫的作風(fēng)。
不同于前面幾位具有歐洲風(fēng)格的導(dǎo)演,美國新生代的導(dǎo)演更多的沉迷于電影技巧。如布萊恩·辛格和斯派克·瓊斯。而拍攝了《記憶碎片》的克里斯托弗·諾蘭對(duì)于影片結(jié)構(gòu)和懸念設(shè)置十分熱衷,他對(duì)閃回和剪輯的運(yùn)用簡直是化腐朽為神奇,對(duì)心理不確定的暗示比之大衛(wèi)·林奇的電影同樣是看重實(shí)驗(yàn)性。在投身好萊塢主流電影之后拍攝的《失眠》和《致命魔術(shù)》仍然具有強(qiáng)烈的個(gè)人風(fēng)格,將其擅長的通過鏡頭剪輯進(jìn)行心理描寫的創(chuàng)作特點(diǎn)融入其中。迷戀于攝影技巧和鏡頭運(yùn)動(dòng)的達(dá)倫·阿諾洛夫斯基,其作品具有強(qiáng)烈凌厲的沖擊感。無論是《π》還是《夢之安魂曲》,其頹廢而具有顛覆感的影像風(fēng)格征服了眾多觀眾,大量蒙太奇剪接、分割畫面、可變鏡頭快速回放等眾多的視覺語言是他思想精髓的涵蓋。而在眾多技巧派的新銳導(dǎo)演中,保羅·托馬斯·安德森無疑是最有天賦的,他成功的將嚴(yán)肅的影片內(nèi)涵和電影技巧結(jié)合起來。安德森深受阿爾特曼和西科塞斯的影響,無論是眾多出場人物和事件的交叉剪輯還是對(duì)人物內(nèi)在的深刻挖掘都能玩得頭頭是道。獲得了2000年柏林的金熊大獎(jiǎng)的《木蘭花》是多線交織的情節(jié)劇中最具創(chuàng)意且最具控制力的一部,比起2005年獲得奧斯卡大獎(jiǎng)的《撞車》和阿爾特曼的名作《短片集》,這部作品具有難得的優(yōu)雅和出奇的想象力。
隨著眾多拉美導(dǎo)演投奔好萊塢尋求發(fā)展,新世紀(jì)的美國電影又開辟出具有熱帶風(fēng)情的拉美一派。墨西哥新銳導(dǎo)演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里圖在2000年成功的拍攝了《愛情是狗娘》之后,來到美國連續(xù)拍攝了《21克》和《巴別塔》。導(dǎo)演運(yùn)用破碎細(xì)密的剪輯技巧打破線形時(shí)間的限制,將不同時(shí)空下發(fā)生的事件交叉在一起,使影片具有某科拉美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特征。同樣來自墨西哥的導(dǎo)演阿方索·庫瓦隆在其作品中繼承了墨西哥七八十年代性喜劇精髓并注入現(xiàn)代人的語境,準(zhǔn)確地抓住了墨西哥人的心理狀態(tài)和生活方式。在其好萊塢新作《人類之子》中,在獨(dú)特的環(huán)境背景下,阿方索延續(xù)了個(gè)人陰郁黑暗的冷暴力視覺風(fēng)格,展現(xiàn)出一個(gè)破敗幽閉、沖突四起的未來世界。巴西導(dǎo)演費(fèi)爾南多·梅里爾斯在《上帝之城》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后,來到好萊塢拍攝了同樣引起巨大影響的《不朽的園丁》,影片不僅具有強(qiáng)烈的拉美風(fēng)格,而且由好萊塢明星出演,因此在商業(yè)和藝術(shù)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導(dǎo)演敘事緊湊有力、有條不紊,因此在宏大的敘事體系中維持著強(qiáng)大的控制力,在充滿暖色調(diào)的攝影基礎(chǔ)上其風(fēng)格具有一種熾熱的熱帶風(fēng)情。
期待革新的歐洲電影
歐洲電影具有濃郁的人文氣息,這和歐洲導(dǎo)演與生俱來的精英意識(shí)密切相關(guān),創(chuàng)作者長期處于在追求藝術(shù)價(jià)值,而非商業(yè)利益的語境里,這使他們大都保持著藝術(shù)家的敏感和知識(shí)分子的社會(huì)良知。在意大利新現(xiàn)實(shí)主義和法國新浪潮運(yùn)動(dòng)的帶領(lǐng)下,歐洲電影在上世紀(jì)六七十年代得到飛速的發(fā)展,歐洲影壇誕生了一大批大師級(jí)導(dǎo)演和優(yōu)秀的人文作品。然而這股電影思潮持續(xù)到八十年代中期便日漸稀薄,隨著布紐埃爾、法斯賓德、特呂弗、費(fèi)里尼等眾多大師的相繼去世,伯格曼退出影壇,安東尼奧尼癱瘓,歐洲電影在九十年代便呈現(xiàn)出低迷的局面,陷入“大師不再”的尷尬境地。
在新世紀(jì)的這幾年中,老將們意氣風(fēng)發(fā)拍攝了幾部優(yōu)秀的作品,如侯麥的《貴婦與公爵》、里維特的《去了解》、伯格曼的《薩拉邦德》以及阿倫·雷乃的《心的歸屬》,但由于年齡原因,他們并不能堅(jiān)持持續(xù)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而貝爾納多·貝爾托魯奇、維姆·文德斯、埃米爾·庫斯圖里卡等具有國際聲譽(yù)的優(yōu)秀導(dǎo)演盡管依然堅(jiān)持著個(gè)人創(chuàng)作,但創(chuàng)作水準(zhǔn)卻大不如前。與此同時(shí),眾多二線導(dǎo)演,如克萊爾·丹尼斯、菲利普·加瑞爾、南尼·莫瑞提等,盡管他們堅(jiān)持精英文化而拍攝了眾多優(yōu)秀作品,但是卻沒有取得國際上的廣泛認(rèn)同。相反,在藝術(shù)和商業(yè)取得平衡的優(yōu)秀導(dǎo)演佩德羅·阿莫多瓦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歐洲電影的代名詞,其作品兼顧藝術(shù)內(nèi)涵和商業(yè)元素,在國際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能夠在藝術(shù)品質(zhì)上成功嫁接商業(yè)號(hào)召力的年輕導(dǎo)演將成為歐洲電影的新希望,引導(dǎo)歐洲電影走向更加成功的市場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但是,對(duì)于薈萃了人類精神文明的歐洲大陸,我們還是期待出現(xiàn)更多具有強(qiáng)烈個(gè)人風(fēng)格和知識(shí)內(nèi)涵的電影作者。
隨著阿莫多瓦的巨大成功,西班牙電影特有的奇情主義和熱烈奔放的風(fēng)格使其在商業(yè)和藝術(shù)上都取得了國際的認(rèn)同。被譽(yù)為阿莫多瓦接班人的胡里奧·密譚深深根植于廣袤的西班牙歷史風(fēng)情,具有強(qiáng)烈的魔幻氣息和超現(xiàn)實(shí)主義氛圍。在《牛》、《人間昆蟲記》、《露西婭的情人》等眾多優(yōu)秀作品中,導(dǎo)演運(yùn)用現(xiàn)實(shí)與想象相互交織的表現(xiàn)手法,通過“意識(shí)流”的敘事手段,探討了在人生偶然和必然的機(jī)緣巧合下人物細(xì)密的內(nèi)心世界。多才多藝的亞歷桑德羅·阿曼巴是西班牙新生代中最有才華的電影人。在影片《睜開你的雙眼》中,導(dǎo)演探討了夢境和幻覺,真實(shí)性和意識(shí)虛幻性之間的關(guān)系。在《小島驚魂》中,他又通過人鬼關(guān)系的置換,顛覆了傳統(tǒng)的觀影邏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就在影評(píng)人詬病阿曼巴只是通過懸念和結(jié)構(gòu)贏得成績的時(shí)候,導(dǎo)演拍攝了《深海長眠》,以深厚的人文氣息和對(duì)于生命和死亡的哲學(xué)思考征服了威尼斯電影節(jié)的評(píng)委。女導(dǎo)演胡安瑪·巴赫·烏略亞少了些西班牙奔放魔幻的風(fēng)情,作品《蝴蝶的翅膀》風(fēng)格冷峻中有平實(shí)的家常。更富于女性觸感。在其最著名的作品《殺手·蝴蝶·夢》中導(dǎo)演將其堅(jiān)韌、冷峻、清晰的影像風(fēng)格發(fā)揮得淋漓盡致,通過對(duì)人物的細(xì)膩刻畫,將一個(gè)有些變態(tài)情調(diào)的故事處理的恰到好處。
法國電影仍然在人文傳統(tǒng)上堅(jiān)持自身優(yōu)秀的底蘊(yùn)和特質(zhì),法國人良好的文化教育和廣闊的文藝電影受眾群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法國優(yōu)質(zhì)電影的發(fā)展。哲學(xué)出身的法國導(dǎo)演布魯諾·杜蒙僅僅拍攝過四部作品,但兩次獲得戛納電影節(jié)評(píng)委會(huì)大獎(jiǎng)。他的作品節(jié)奏緩慢,氣氛壓抑陰沉,且充滿大量的情色和暴力內(nèi)容,從而影射人心的疏離和人性的扭曲。2004年備受爭議的作品《29片棕櫚葉》表現(xiàn)了男人在孤獨(dú)而令人絕望的力量壓迫下慢慢走向瘋狂,愛情也走向破裂分離。曾身為《電影手冊(cè)》編輯的奧利維耶·阿薩亞斯則一貫堅(jiān)持這法國新浪潮“個(gè)人化敘事”的電影風(fēng)格。電影《迷離劫》就具有強(qiáng)烈的新浪潮風(fēng)格,頗似特呂弗的名作《日以繼夜》。在2004年,阿薩亞斯導(dǎo)演,張曼玉主演的《清潔》,以其細(xì)膩入微的人物刻畫、清冷樸實(shí)的風(fēng)格技巧和具有強(qiáng)大生命力的影片內(nèi)涵,再次向世界證明了法國電影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而當(dāng)今最具國際聲譽(yù)的法國導(dǎo)演弗朗索瓦·歐容,則一反傳統(tǒng)法國電影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傳統(tǒng)特色,而具有一種強(qiáng)烈的形式感。從早期的《干柴烈火》,到風(fēng)格圓潤的《沙之下》,再到近期的《彌留時(shí)光》,我們看到多種電影風(fēng)格的結(jié)合,有法斯賓德的戲劇感,波蘭斯基的驚悚感,希區(qū)柯克的懸念感,還有布紐埃爾的超現(xiàn)實(shí)主義特征。歐容不僅保證了作品的藝術(shù)品位,而且沒有丟失電影的娛樂屬性,為法國電影在國際上贏得了一片領(lǐng)地。
Dogma95宣言是迄今為止最后一場電影美學(xué)革新運(yùn)動(dòng),要求手持?jǐn)z影、同步錄音、禁用光學(xué)器材等攝影技巧以保證電影拍攝的現(xiàn)場真實(shí)特征。該運(yùn)動(dòng)中最為突出的導(dǎo)演拉斯·馮·提爾拍攝了眾多優(yōu)秀影片,盡管不是每一部作品都恪守Dogma95的信條,但其作品中強(qiáng)烈的道德批判態(tài)度使得他成為當(dāng)代歐洲影壇中最具大師相的一位。無論是前期“金心三部曲”還是正在拍攝的“美國三部曲”,導(dǎo)演冰冷刻薄的道德態(tài)度以及對(duì)電影表現(xiàn)技法的探索,都使人們想到已經(jīng)謝世的著名導(dǎo)演庫布里克。英國電影則在古典美學(xué)和先鋒實(shí)驗(yàn)的兩極中交相呼應(yīng),不僅出現(xiàn)了一批具有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導(dǎo)演,如拍攝了《霍華德莊園》和《長日留痕》的詹姆斯·伊沃里,而且存在諸如彼得·格林納威、德呂克·賈曼這樣具有強(qiáng)烈先鋒特質(zhì)的導(dǎo)演。不同于蓋·里奇和丹尼·保爾的后現(xiàn)代傾向,英國新貴斯蒂芬·戴德利導(dǎo)演擅長處理人物內(nèi)心情感的起伏,影片透露出現(xiàn)實(shí)和詩意的結(jié)合。導(dǎo)演2002年的作品《歲月如歌》在極短的篇幅里表現(xiàn)了一本小說與三個(gè)女人的命運(yùn)之間的關(guān)系,弗尼吉亞的思辨,勞拉·布朗的彷徨,克拉麗莎的痛苦,交織在一起奏起了一段關(guān)于女性對(duì)自由、獨(dú)立、堅(jiān)強(qiáng)、愛的向往、追求和呵護(hù)的樂章。
悄然崛起的亞洲電影
亞洲電影以其獨(dú)特的文化傳統(tǒng)和思維模式區(qū)別于西方電影的戲劇程式,從而形成一派獨(dú)特的東方美學(xué)體系和世界觀。上世紀(jì)50年代,日本大師級(jí)導(dǎo)演黑澤明、溝口健二便為亞洲電影贏得了巨大的影響。之后,隨著世界電影文化潮流的變化,日本相應(yīng)出現(xiàn)了“新浪潮”運(yùn)動(dòng),其中四位主將大島渚、增村造保、寺山修司、今村昌平一反小津安二郎等前輩營造的東方景觀,向世界呈現(xiàn)了一個(gè)戰(zhàn)后破敗而充滿罪惡的日本。他們的杰出造詣保證了日本電影在亞洲甚至世界的領(lǐng)先位置,直到上世紀(jì)80年代,日本電影一枝獨(dú)秀的現(xiàn)象才被中國導(dǎo)演的蜚聲國際所打破,侯孝賢、楊德昌、張藝謀等人向世界呈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美學(xué)在新時(shí)代下的變革。進(jìn)入上世紀(jì)90年代之后,隨著亞洲經(jīng)濟(jì)的飛速發(fā)展和國際化進(jìn)程的加快,亞洲電影呈現(xiàn)出欣欣向榮、百花齊放的局面。越南導(dǎo)演陳英雄,伊朗導(dǎo)演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韓國導(dǎo)演林漢澤,日本導(dǎo)演北野武都在國際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他們?cè)趫?jiān)持本國的民族特征的同時(shí),在電影內(nèi)涵上融合西方的哲學(xué)思想,從而加深對(duì)社會(huì)和歷史的思考。
上世紀(jì)90年代的日本電影盡管在商業(yè)制片上并不成功,但涌現(xiàn)出的眾多獨(dú)立制片導(dǎo)演以其獨(dú)到的美學(xué)傾向在國際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為日本獨(dú)立電影的新一代領(lǐng)軍人物,青山真治對(duì)暴力有著異乎尋常的表現(xiàn)欲,然而不同于三池崇史對(duì)于暴力的變態(tài)展示和黑色挖苦,青山真治強(qiáng)調(diào)了政治和歷史中潛在的暴力因素對(duì)于人的巨大影響。三個(gè)半小時(shí)的鴻篇巨制《人造天堂》以一種冷峻、悲愴的紀(jì)錄風(fēng)格和過程化表現(xiàn)的鏡語方式揭示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huì)錯(cuò)綜復(fù)雜的矛盾和沖突,并且擴(kuò)展出一個(gè)超越時(shí)代和個(gè)體的表達(dá)空間,提供了一種寓言式的內(nèi)涵。另一位癡迷于暴力的導(dǎo)演黑澤清,不同于北野武的突發(fā)性,他延展了暴力呈現(xiàn)的時(shí)間和力度,在冷靜克制的生活化的場景中注入粘稠的黑色暴力傾向,使得影片呈現(xiàn)一種獨(dú)特的魅力。影片《X圣治》和《神樹》都體現(xiàn)了黑澤清一貫的冷峻陰沉的風(fēng)格和對(duì)人物精神世界分裂錯(cuò)亂的著迷。新生代導(dǎo)演是枝裕和的影片風(fēng)格則更加接近于老一代日本電影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特征。導(dǎo)演處女作《幻之光》便在國際和國內(nèi)引起了巨大反響,被認(rèn)為是上世紀(jì)90年代中最好、最細(xì)膩的電影。在2005年的新作《無人知曉》中,導(dǎo)演運(yùn)用半紀(jì)錄的風(fēng)格以清冷殘酷的影像展現(xiàn)了4個(gè)被拋下的孩子將近一年的生活以及他們的內(nèi)心世界。
韓國電影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之下,在新世紀(jì)有了巨大的發(fā)展,成為當(dāng)今亞洲電影發(fā)展的一個(gè)焦點(diǎn)核心地區(qū)。盡管韓國電影充斥著對(duì)日本和好萊塢商業(yè)電影的模仿,但在良好的市場環(huán)境下,一批有個(gè)性的電影人涌現(xiàn)出來為韓國電影贏得了眾多世界性的榮譽(yù)。導(dǎo)演金基德無疑是當(dāng)今韓國電影中最炙手可熱的作者,無論是《漂流浴室》中呈現(xiàn)的女性主義傾向,或是《春夏秋冬又一春》、《弓》所表現(xiàn)的神秘主義,都具有一種寓言特質(zhì)的指向性,因此電影本身脫離現(xiàn)實(shí)而具有某種空靈的“禪”性。不僅如此,他的新作《時(shí)間》則以冷峻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視角批判了當(dāng)今韓國的整容風(fēng)潮。同期出道的導(dǎo)演洪尚秀,雖然沒有金基德如此強(qiáng)大的聲譽(yù),但卻在韓國知識(shí)分子階層取得了相當(dāng)?shù)恼J(rèn)同。無論是《處女心經(jīng)》的五段式,還是《劇場前》的戲中戲,都體現(xiàn)了洪尚秀對(duì)于電影結(jié)構(gòu)的迷戀,他對(duì)于結(jié)構(gòu)的運(yùn)用在于段落和段落之間的重復(fù)和變化,從中透射主人公的心理狀態(tài),并在藝術(shù)媒體的自我重構(gòu)過程中削弱了現(xiàn)實(shí)和電影的差別,從而在電影中體現(xiàn)導(dǎo)演所期待的“親切的虛假性”。有明顯Cult傾向的作者導(dǎo)演樸贊旭不僅維持了自身的獨(dú)特風(fēng)格,而且保證了電影的票房收入。其“復(fù)仇三部曲”無論在評(píng)論還是商業(yè)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我要復(fù)仇》、《老男孩》、《親切的金子》呈現(xiàn)了一種“群像戲,對(duì)手戲,獨(dú)角戲”的獨(dú)特格局,并且劇情原始的爆發(fā)力和影像強(qiáng)烈的壓迫感將影片的絕望氣息推到頂點(diǎn)。
中國電影在近幾年得到了飛速的發(fā)展,尤其是中國臺(tái)灣導(dǎo)演侯孝賢、蔡明亮等人的作品在歐洲享有盛譽(yù),香港電影在商業(yè)和藝術(shù)之間尋找著平衡點(diǎn),而大陸電影在幾代電影人不斷堅(jiān)持不斷革新的過程中尋求新的出路。大陸第六代導(dǎo)演賈樟柯新作《三峽好人》在2006年的威尼斯電影節(jié)上折桂,獲得金獅大獎(jiǎng),說明第六代導(dǎo)演已經(jīng)打破第五代導(dǎo)演的藝術(shù)格局,在國際上贏得了知名度。《三峽好人》全片分為“煙、酒、茶、糖”4個(gè)部分,卻講述了兩個(gè)故事。其中“煙、酒、糖”講述了底層民眾的生活狀況,而“茶”部分則對(duì)準(zhǔn)了中產(chǎn)階級(jí)生活,通過“底層”和“中產(chǎn)”的對(duì)比,展示中國社會(huì)中普遍存在的社會(huì)移民問題。同屬第六代導(dǎo)演的王超的影片《江城夏日》在2006年戛納電影節(jié)“一種關(guān)注”單元奪得最佳影片,影片一如第六代導(dǎo)演對(duì)于邊緣人物或者底層階級(jí)的關(guān)注,呆板而凝滯的影像風(fēng)格雖然得到了許多評(píng)論家的贊許,但也和普通觀眾拉開了距離。曾經(jīng)為第六代導(dǎo)演的領(lǐng)軍人物張?jiān)?006年的新作品《看上去很美》,改編自王朔的小說,在柏林電影節(jié)也贏得了榮譽(yù)。在新的一年,在世界電影不斷發(fā)展的格局下,我們期待中國電影能夠取得更大的進(jì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