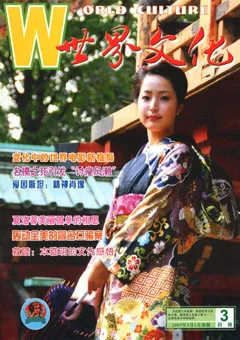深藏的“結構”
“回到弗洛伊德!”
這是法國最具影響力的精神分析大師雅克·拉康(1901-1981)提出的口號,正是在這一主張的基礎上,他創建了法蘭西精神分析學派——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派,從而將弗洛伊德所開創的精神分析學推向了后現代階段。拉康的影響遠不僅限于心理學學科,更滲透到了哲學、文學、語言學等諸多領域,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影響力日益增大,以至于有人將其評價為“笛卡爾之后最重要的法國思想家,自尼采和弗洛伊德以來最有創見、視野最廣的歐洲思想家”。
拉康出生于巴黎的一個富商家庭,他早慧而好學,在中學里教師們甚至害怕去給他上課。18歲那年他考上了巴黎醫學院,25歲專攻精神病學,31歲完成了博士論文《妄想狂精神病及其與性格的關系》,這篇文章對達利等人的超現實主義藝術產生了重大影響。1936年,他在第十四屆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年會上提交了著名的《鏡像階段》的論文,該文提出了關于主體心理發展最初階段的理論,確立了拉康在精神分析學中的地位。此后,他一面作為巴黎最著名的精神分析學家每天接待大量病人,一面繼續他的教學和學術探索。1953年拉康與其他人組成了法蘭西精神分析學會,由于他的見解的異端性,這一協會長期得不到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承認。同年9月,他在羅馬大學發表了《精神分析學中的言語和語言的作用和領域》的長篇報告(即著名的“羅馬報告”),標志著“拉康學派”的誕生。在這篇宣言中,他提出了“回到弗洛伊德”的口號,尖銳地批評了正統的精神分析學中的種種流行觀點,系統地提出了“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派”的基本觀點。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拉康籌辦了個人形式的研討班,由他本人主講,這一形式持續了30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其后半生,他創辦了巴黎弗洛伊德學院,成為傳播其思想的中心,同時他的思想繼續發展并逐漸轉向后現代主義,這種理論的創造力一直保持到他逝世的時刻。縱觀拉康的一生,其最重要的貢獻在于實現了弗洛伊德理論的法蘭西化,并且在精神分析學史上第一個為這門學科奠定了哲學根基。
在上個世紀中葉的法國思想界,彌散著一種“令人激動而又帶有些許狂放”的時代氛圍,一群人文知識分子住在巴黎相隔不遠的幾個街區,他們中有薩特、加繆、列維一施特勞斯、阿爾都塞、德里達、西蒙·波伏娃、梅洛一龐蒂、喬伊斯等人,拉康與他們交往頻繁。這是一個思想馳騁的年代,可以說,20世紀后半期的世界人文學術的面貌相當一部分是由他們所塑造的。拉康在這一時期也非常高產,寫出了一大批經典之作。1955年,他在自己的研討班上分析了美國作家愛倫·坡(1809-1849)的小說《竊信案》,這是對文本的結構主義分析的典型。盡管拉康的作品一向以晦澀著稱,但這一篇分析文字卻饒有趣味,于活潑生動之中見犀利深刻。
小說《竊信案》是一個構思精巧的偵探故事。王后收到一封密信,國王突然回來,王后在匆忙之間只好把信堂而皇之地倒扣在桌子上,希望這樣反而不致引起疑心。恰好這時大臣前來,他發現了這封信并察覺了王后的慌張,于是他用外表相像的另一封信換走了那封密信,由于國王在場,王后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封信被竊。之后,王后命令警長找回這封信,警長仔細搜查了大臣的住宅,結果一無所獲,因此只有求助于業余偵探杜賓。杜賓經過推理,認定大臣一定會將信藏在明處,因此只身造訪大臣住宅,果然密信經過偽裝隨便插在壁爐架上掛著的袋子里。他在次日再次造訪,巧妙引開大臣的注意力并拿走密信,又在原處放了一封相似的信。
拉康指出,這個故事揭示了一種“結構的重演”。這里出現了兩個類似的場景,每一場景中部有三個主體進行著觀看,為了方便說明,我們畫出示意圖(見下圖)。

圖所示,主體Ⅰ什么也沒有看到;而主體Ⅱ看到了主體Ⅰ沒有看見的東西,并且看到了這個人被隱藏的秘密所欺騙;而主體Ⅲ看到了前兩者所想要隱藏的東西,并成功地得到了想要的東西。拉康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來說明以上三者在結構中的角色,他將前兩者比作“鴕鳥”:“第二個參加者自以為有隱身術,因為第一個將頭埋在了沙中,然而第二個參加者卻讓第三個參加者安安定定地在背后拔它的羽毛。”這很像中國的成語“螳螂捕蟬,黃雀在后”。
拉康將小說中“被竊的信”視為一個“純粹的能指”,也就是一種無意識的隱喻。因為“信”這個單詞無論在英語還是法語中還有“字母”、“文字”的含義,因此小說中的“信”隱喻了語言中的無意識結構。“信”作為動態的“能指”在其“所指”的意義鏈上不斷地滑動,并且在兩個場景自動地重復著相同的運動軌跡,在其重復的過程中主體是無意識的。在整個故事中,信本身的內容并不重要,無論它是情書或是密謀信、告密信還是求救信,而重要的是它對主體的制約作用。拉康指出,“恰恰是那封信和它的轉手制約著這些主體的角色和出場方式。如果它‘被擱置’,他們就會遭受失信的痛苦。因為要從信的陰影下通過,他們卻成了它的映像;因為要擁有信,信的意義卻擁有了他們。”從以上黑格爾式的思辨之中,我們看到拉康思想的深刻之處:表面上看起來主體支配著語言(“信”),但實際上主體被語言所支配,語言符號的“能指連環”決定了主體的命運和行動,而“能指”所具有的結構實際上來自于主體的無意識。從這里可以看出拉康對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作了結構主義的發揮:在弗洛伊德那里,無意識領域對主體的支配是盲目的沖動;而在拉康這里,支配者是具有某種深層結構的“能指連環”。
故事中的“信”的所有權與隱藏過程一直在逃避自身并不斷地成為讀者所關注的焦點。故事開始時,陷入沉思的故事講敘者與杜賓及其寂靜的書房構成了一個空間,突然警長的來訪告知王后信件被竊一事,打亂了室內沉悶空氣,作為能指符號的“被竊的信”的所有權與藏匿性開始出現。這里拉康對語詞進行了細致的分析,“所有權”的英文為“ownership”,其詞根“own”在古英文和古德文中含義接近擁有與欠缺,因此擁有即欠缺、匱缺。小說中的“信”仿佛是王后的所有物,但它卻一直逃避所有權,被變形或倒置。寫信人是誰?我們只從側面知道“S公爵”;信的內容是什么?我們不得而知;國王是否會發現信件?這意味著剝奪王后的所有權——名譽、地位乃至于生命,這些都是沒有答案的疑問。拉康著眼于信的漂落、轉移過程及能指作用,他從這里開始引申:信猶如作品,其原意并不為人所知,更無所謂固定的所指,它只能是流動不居的能指。作品在讀者中流傳,僅此便構成了其存在的意義。拉康始終認為這個表面類似重申所有權的過程則暗示了其所有權是開放的:可以被肢解、被竊取、被破壞、被置于深淵之中,總之可以被一再“播撒”(借用德里達的術語)。
在對故事情節的分析中,拉康多次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論。拉康將失竊的信看作是王后“閹割焦慮”的表現,對信的追尋又變成了對“他物”的渴求。而當杜賓走進大臣的辦公室時,“被竊的信像一個女人的身體布滿整個空間”,因此杜賓的尋找也帶有某種“性”的暗示。以上內涵很難說是愛倫·坡的原意,但拉康在這里做這樣分析的目的并非要追尋作者創作的本意,甚至也并不是像一般的精神分析派的文學批評家那樣通過文本探尋作者的創作潛意識,他對《竊信案》的分析毋寧是為了闡發自己關于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的理論。
拉康對《竊信案》這一文本的解讀成了結構主義文本分析的經典之論,其自問世以來,在西方思想界、文藝理論界引發了強烈而持久的反響,德里達、巴巴拉·約翰遜、霍蘭德、戴維斯等人都曾對拉康的閱讀策略提出了進一步的闡釋。拉康關于語言中“能指”的流動性及其與“所指”的不確定關系、關于語言中的無意識結構對主體的制約作用的論述,包含了解構主義和女性主義的思想源頭。因此,他當之無愧地成為由結構主義向解構主義過渡時期具有開拓意義的思想家。當我們閱讀一部文學作品時,是否可以沿著拉康的思路對文本中深藏的“結構”進行挖掘和闡釋呢?讀者不妨嘗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