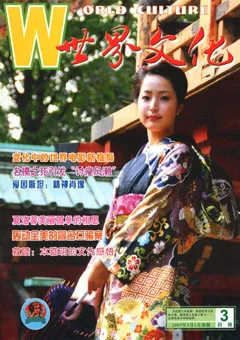教書泰國(續)
時間觀念
初到泰國大學任教,感覺這里的時間觀念極強。因為每天上班必須“簽到”,下班必須“簽去”。若提前走,還必須報告并說明原因,教師職工均無例外。即便是沒有課,也要“坐班”,從上午8點到下午4點半。“外教”就更麻煩,必須先到“外事處”簽到,然后再返回辦公室,校園里來去一趟需二十多分鐘。有兩次,因為上午第一節有課,我沒有即時去“外事處”簽到,不久電話就來了,問明了情況后,仍然要求“補簽”。后來才得知,這么做的原因,似乎與薪水有關,雖是“月薪制”,但卻要精確到“日”的。午餐是在學院食堂,下午一點就上班。無課無事,在辦公室里坐著。中國式的午睡習慣,常常潮水般地襲來,為防不雅,拼命地灌咖啡。有時也不禁長嘆,簡直是“機關”,哪里是大學!只好發揚革命精神,入鄉隨俗。
一段時間后,發現這種嚴格的時間形式,也就是形式而已,就如中國話所說的“大帽子底下開小差”。泰國的教師(不是職工!)雖然在形式上也“簽到”或者“坐班”,但實際上時間觀念并不強。我恪守中國教師的優良傳統,8點半上課,8點20分便準時到教室。而泰國教師,能夠在8點40分進入教室就算是“先進分子”了,部分教師9點才上講臺。不過,也只有部分學生,準時到教室,隨后,或者斷斷續續,或者絡繹不絕地進來,一直持續到九點半以后。甚至考試,居然也有遲到一兩個小時才趕到的。問何故?一言以答之:“堵車”。——泰國大學生住宿自定,根據各自的情況,散居在城市各處。而曼谷的“堵車”世界聞名,所以,“遲到”是有情可諒的。當然也無“點名”之舉,反正是“學分制”,考試過關,學分夠了,就可畢業。而且,學費按所選課交納。上課遲到實際上意味著精神物質雙重損失,那真是咎由自取。
其實,無嚴格的時間觀念,并非僅僅是教師和學生,領導們也是一樣。某日,接“外事處”通知,周末將安排全體“外教”去巴堤亞旅游,早上7點在學校車隊處集合出發。星期六,晨,陽光燦爛。中國人6點50到車隊,歐美人7點準時到,7點20左右,緬甸人、印度人、柬埔寨人陸續到來。7點40,大家開始議論是否改期了,但沒有通知?7點50,司機到,8點過5分,帶隊的副院長滿臉笑容,神采飛揚來到,“Hello!Youcome early.”沒有“Sorry”,沒有解釋。上車,出發。大家面面相覷。坐在我旁邊的美國小伙子,咕嚕了一句:“東方人的時間觀念……”
因無緣無故的不守時,有一點煩惱,好在也無大礙。而我初次踏上泰國大地時的遭遇,那就有點驚險了。臨行前的頭天,又是電話,又是傳真,把飛機的航班以及到達的時間等告知泰方,對方回復將有一名負責人親自到機場迎接。從成都起飛,兩個小時,還沒在意,曼谷國際機場就到了。取行李,過海關,一路順利。進了大廳,便四下環顧,尋找“WELCOME MR.LI……COMEFROM CHENGDU”之類的招牌。可是,沒人,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有人來接我們!怕有疏漏,一人守住行李,另一人將候機廳搜索一遍,無接者;不放心,換一個人,再搜索一次,無人!這一下,我們傻眼了。身處異國他鄉,無親無友,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的大學教師一般也沒有手機,而且也不知道具體的聯系方式。怎么辦?只好等。半個小時,再半個小時,又半個小時,……。我們商議,再等十分鐘,沒人來,我們便買機票,打道回府。兩小時十分鐘,一位中年泰國婦女向我們走來,“Mr.Li?”——唉,天上掉下了個“林姐姐”。在車上,她問寒問暖的,就是沒有“Sorry”!沒有解釋!——或許,熱帶氣溫高,不能急,大家都是慢性子。
相映成趣的是,臨走回國時候的告別,此幕戲又重新上演。院方通知,院長將要親自為我們送行,九點辦公室見,但一直等到十點半,院長才姍姍來到——好在已經習慣,無所謂,并且,送給我們的禮物與紀念品相當豐厚。
可是,也有嚴格遵照時間辦事的。放假回國,為了買到打折扣的機票,只能比合同規定的日子提前兩天走,反正工作已經結束了,向院方領導匯報,也欣然同意。只是臨行前去領當月工資,發現少了。一問才知,已經將這兩天的薪水扣去了,——據說,電腦控制的,不講情面。當然,這并不是泰國的傳統,而是西方文化。而且,也有很講“情面”的時候:我們的行李嚴重超重,學校專門派來送行的人,上去與海關官員耳語幾句,便立即放行——真可謂是東西文化交融。
文化交融
在當今泰國,尤其是曼谷以及旅游勝地巴堤亞、普吉島等,你會強烈的感受到現代化、西方化的氣息。大街上,林立的各種“洋文”招牌,流水般的汽車行列……與世界上其他國際化的大城市大同小異。惟一特殊的,或者說特別吸引眼球的是交通警察,因為他們是戴著防毒面具指揮著交通。
但是,實際上,傳統文化的核心仍延續千年而保持下來。例如佛教傳統,寺廟香火永遠興盛,僧人眾多到輿論都要為之辯護。某大報發表社論稱:“有些具有某種異端思想者,認為這些僧侶是‘不勞而獲’,其實正表現了這些無神論者的偏見與淺薄。一個社會,如果需要人人去勞動,才能保障全社會的溫飽,那是這個社會的悲哀——表明兩個問題:生產力低下和人間的無情。”對佛教的尊崇,甚至用法規來確定。如公交車的第一排規定是“僧侶座”,只有車上無僧人時,其他人才能坐。
清晨,日出之前,一對對赤腳僧人,身披袈裟,手持政府統一贈送的“缽”,漫步在大街小巷,接受早已等候在街邊的市民們的“齋僧”。所謂的“齋僧”并非是乞討,而是接受“供奉”,能“賜福”于供奉者。所以,市民們滿懷虔誠,對僧人們禮敬有加。而僧侶們似乎漫不經心,昂然來去。入夜,夜總會,酒吧,各種情調的歌舞,光怪陸離,恍若置身于巴黎或者紐約。——這兩道風景,相映成趣,交融相織,共同構筑出了泰國奇異的人文現象。
這種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交融混雜,表現在泰國生活中的各個方面。一方面,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民主選舉、國會、在野黨等一應俱全。另一方面,國王雖然沒有實權,卻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總理去覲見國王,應該跪下,還應吻他的腳,以表示國王的至高無上。國王的生日就是泰國的“國慶節”,王后的生日就是泰國的“母親節”。這些表現又似乎是封建社會。一方面輿論自由,媒體可以大罵政府;另一方面,又規定國王與佛教是不可評說的。一方面,政府由全體公民投票選出,應該是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另一方面,軍事政變頻繁,民選政府多次被推翻。而且,似乎并沒有強烈的抗議甚至反感。更有趣的是,這些政變,基本上不流血。就如前不久在泰國發生的政變…樣,幾輛坦克開到總理府,軍界領導在電視等媒體宣布一番,政變就算是完成。對絕大多數的泰國人的生活幾乎沒有影響。或許,大多數泰國人看待“政變”,就如看了一場演出,而且是不精彩的演出。于是,他們漫不經心地觀看著,該做什么事情就繼續做。
這種交融文化,自然而然也滲透到大學校園。泰國較為有名的大學的教師,基本上都是“海歸”。平時西裝革履,滿口英文,但這也不妨礙他們按照泰國的傳統娶上一個小妾。學校的制度也高度西化,私立大學不清楚,公立大學的校長一般是經過嚴格的競選程序,由全體教授投票推選,再由主管部門或者董事會認定,一般任期五年。但一旦就任,各院系處頭頭就由校長任命,并且等級十分森嚴,校長坐著講話,副校長就應站著回應。傳統的文化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例如,在正規的,莊重的場合,相互見面的問候仍是雙手合十的佛教禮儀;而不是握手、擁抱。即使是在教師的退休儀式上,也是請一位“高僧”,而不是“領導同志”,上法壇來主持。在頌經祈福之后,退休者便端坐中央,全體同事圍繞著他環行一周,然后依次上前獻花祝福。整個過程肅穆、幽雅,還帶一點憂傷的情調。可惜,他們不準我拍照。
當然,泰國大學校園里,最獨特的現象,就是“變性人”大學生。“變性人”的歌舞演出對于大多數來過泰國旅游的中國人來說不會陌生。泰國的“變性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是相當高的,而“變性手術”更是世界聞名。泰國法律也規定“變性人”基本上可以享受與其他公民一樣的權利,如組成家庭、求學等等。除了不能任職軍隊、警察、公務員以及教師之外,可以從事其他職業。因此,就有了“變性人”大學生。在“漢語班”上,說不定,那幾個身材高窕、長發披肩、抹著口紅、穿著高跟鞋的學生就是已經變了性的大學生。而且他們的成績大都還十分優秀,待人彬彬有禮。他們將來大多數都要從事娛樂業和旅游業,能夠講一口流利的漢語是很有利于職業的發展的。
這就是泰國——一個充滿著西方的現代氣質卻又可以深深恪守著自己傳統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