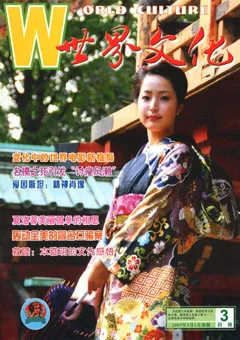彼得大帝的“東方使團”
彼得大帝的改革使俄國走上了西方式的現代化道路。他力圖使俄國融入歐洲文明社會,擺脫俄羅斯民族中野蠻、落后、保守的特征。彼得大帝致力于引進西方文化,同時也把觸角伸向了遙遠的東方。歐亞大陸上一北一東兩個民族,由于一個宗教使團的出現,發生了奇妙的聯系。
一
自16世紀晚期起,一場堪與美國“西進運動”媲美的“東進大潮”轟轟烈烈地席卷了西伯利亞大陸。僅僅半個世紀的時間,俄國哥薩克騎兵的鐵蹄已經踏入了中國黑龍江地區(即阿穆爾河流域),掠奪當地居民的毛皮制品和糧食作物。
面對咄咄逼人的沙俄入侵勢力,清朝政府加強了東北邊疆的防衛。1684年,中俄軍隊在雅克薩城爆發了戰爭。中國憑借強盛國力和康熙皇帝的堅定決心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并在1689年與俄國簽署了劃定邊境的《尼布楚條約》。
根據條約規定,戰后一部分俄軍戰俘留在黑龍江,另一部分隨清軍來到了北京。清政府把他們編為滿洲第四參領第十七佐領,駐于北京城東直門內胡家圈胡同,還為他們專門設立了一所東正教教堂——圣尼古拉教堂(中國人稱之為“羅剎廟”,又因與后來設立的俄羅斯使館位置關系得名“北館”)。為了使這些戰俘牢記自己的信仰,俄國教會通過各種途徑送來教堂用具和信函,鼓勵隨同戰俘來到北京的神父馬·列昂季耶夫將神圣的東正教事業發揚光大,爭取更多的教徒。
由于俄國戰俘的歸化,東正教在北京意外地獲得立足之地,沙俄政府對它寄予了很大希望。1698年,彼得大帝就如何精心經營東正教在北京這個惟一的據點向西伯利亞衙門長官維尼烏斯作出指示:“此事甚善,惟為上帝起見,行事宜謹慎,戒魯莽,以免結怨于中國官員及在當地棲身多年的耶穌會士。為此所需要的,不是學有根底,而是諳于世故的神父,方免偶因傲慢而使上述神圣事業一敗涂地,像在日本發生的那樣。”
為了表示對遠東傳教事業的重視,彼得大帝于1700年6月18日親自指示,在托博爾斯克設立主教區,“庶幾上蒙天恩,逐步使中國和西伯利亞那些愚妄無知、執迷不悟的生靈,皈依真正的上帝”。1712年俄方商隊專員胡佳科夫向清朝理藩院請求派人接替年邁的馬·列昂季耶夫,很快得到了康熙皇帝的準許。在彼得大帝的授意下,托博爾斯克都主教約翰迅速確定了傳教士團人選。直至1714年,清朝內閣中書兼侍讀圖理琛訪問土爾扈特部后取道西伯利亞回國,沙俄政府從托博爾斯克派神父等十余人與之隨行。
二
公元1715年4月30日,第一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抵達北京,領班為伊拉里昂·列扎依斯基,成員包括修士司祭拉夫連季、修士輔基菲利蒙以及教堂差役人員7人。領班和司祭分別被授予五品和七品官銜,每人得到了從600兩到200兩數量不等的補貼,此外每月還向他們發放俸祿。從傳教士團享受的優厚待遇來看,清政府以“懷柔遠人”政策對待遠道而來的外國“喇嘛”,清朝官員不僅經常問候俄國傳教士團和戰俘的生活情況,還為他們的工作提供了各種便利條件。
起初的俄國戰俘及其后代在新的生活環境中很快冷漠了自己的信仰,據《俄國駐北京傳道團史料》記載,“這些阿爾巴津人除少數以外,其他人從在北京定居之日起就對基督教毫無誠意”。教團在發展中國教徒事業方面進展極為緩慢,1731年僅有25名中國人受洗,與西歐天主教的勢力遠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它又被稱為“不傳教的傳教團”。在這種情況下,“傳教”更像是執行其他任務的一個幌子。
自1720年彼得大帝對教會實行改革以來,俄國取消了牧首制,設立了“俄羅斯東正教最高宗務會議”作為東正教的最高權力機構,這一機構直接聽命于沙皇。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實質上成了沙俄政府駐北京的一個官方代理機構,執行著沙俄政府的對華政策,它的工作內容已經轉為“對中國的經濟、文化進行全面研究,并及時向俄國外交部報告中國政冶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沙俄政府要求傳教團成員掌握中國語言,表面看是為了“允許北京的修士司祭可以使用漢語接受教徒的懺悔”,真正目的在于與中國的權勢階層拉攏關系,謀取有價值的信息。在“最高宗務會議”向第七屆傳教團修士大司祭的訓令中,已經明確地道出了這一點,“爾修士大司祭于駐北京期間,一有機會就應盡量把當地動態認真詳細地寫成材料上報俄羅斯正教最高宗務會議;如果國家事務有什么必須保守秘密的事情,那么絕對不能在私人信件中提及”。
許多杰出的成員潛心于中國語言文化的學習研究,客觀上促進了中俄兩個民族的文化交流活動。第三屆傳教士團學員列昂季耶夫是第一個將《易經》、《大學》、《中庸》、《三字經》等儒學經典譯介到俄國的學者。列昂季耶夫在《雄蜂》雜志上發表了《中國哲學家程子給皇帝的勸告》(即《名臣奏議》中的《為太中上皇帝應召書》)譯文,對俄國沙皇婉言勸喻。
幾乎每一位成員來華之前都被委以收集中國典籍的任務。第二屆傳教團學員羅索欣向俄國皇家科學院圖書館貢獻了107本漢滿文書籍和兩幅中國地圖,比丘林回國攜帶的書籍超過了前幾屆傳教士團的總和,總重量達到400普特(1普特相當于16.38公斤),而王西里在北京居留期間共為喀山大學收集了849種2737卷14447冊珍貴的抄本和刻本圖書。
1727年,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通過《恰克圖條約》獲得了合法地位,從而得以在中國永久地居留下去。此后,大約每隔10年教團成員就要更替一次。
三
彼得大帝去世以后,他的繼承者繼續推行“火槍與圣器并舉”的擴張政策。在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過程中,俄國通過在北京的關系維持并擴大著在華的政治經濟利益,通過加大對傳教士團的投入不斷賦予它更為重要的職能與責任。傳教士團像是深謀遠慮的彼得大帝在中國皇城根下安置的一匹“特洛伊木馬”,每當關鍵時刻便能發揮出奇制勝的作用,令其他歐洲國家羨慕不已。正如俄羅斯歷史學家伊帕托娃所言:“北京傳教士團的外交活動可以比作一座冰山,其看不到的水下部分要遠遠超過看得見的水上部分。”
與傳教士團的政治功能相比,它的文化職能影響要更為深遠。團員收集中國情報的活動雖然帶有明確的政治色彩,體現出俄國政府的野心與陰謀,但它對于俄國漢學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傳教團中涌現出許多世界知名的漢學家,如19世紀上半期的比丘林以及下半期的王西里和巴拉第,被后人奉為俄國漢學的三大巨頭,他們對中國哲學與宗教、歷史與地理、語言與文學、社會與法律,甚至農業、天文和經濟都有相當數量的專著傳世。這些足以說明傳教士團在中俄文化交流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這種交流的豐富內涵。
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后,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與蘇維埃政權下的莫斯科牧首區決裂,宣布接受流亡在塞爾維亞的俄羅斯東正教國外臨時主教公會的領導。1956年,自主的中華東正教會成立,彼得大帝開創的“東方使團”壽終正寢,它像歷史長河里的一塊巨礁,曾經引起滔天巨浪,此時被沖刷成為一粒塵埃,消失在滾滾波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