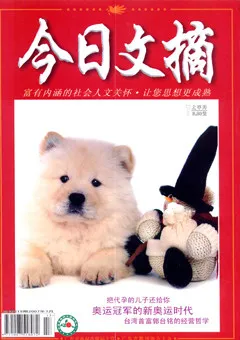人民大會堂的“蝶變”
去年12月25日,全球最大的會計律師事務所普華永道在人民大會堂舉辦了企業年會。剛剛邁進2007年,這里又成為當紅程派傳人張火丁的個人演唱會現場;此前,一家網站在大會堂舉辦了一系列展會;某汽車品牌再次發布其頂級新產品,新款轎車齊刷刷停在大會堂外——這里從前只允許國家領導人乘坐的紅旗轎車停靠。如今,人民大會堂已經在商業之旅上漸行漸遠。
商業活動的成功
來自廣州的南方測繪集團是個小公司,但在成立15周年之際,他們卻做了件頗為得意的事情——在人民大會堂舉行15周年慶典。
“測繪儀器行業,國內品牌認同度很低。我們希望通過人民大會堂這一中國百姓心目中最高權力的象征,提升品牌認同度。”公關經理黃吉海說。
南方測繪集團于是費盡周折,以6萬元/半天的價格,租到了人民大會堂的金色小禮堂。隨之而來的效果,令他們驚喜萬分。全國各地的經銷商蜂擁而至。一些遠在云南、新疆的客戶坐了幾天幾夜的火車,到北京參加這半日的慶典。“他們中很多人這輩子都沒進過人民大會堂。”黃吉海說。
當黃吉海隨著人流,手握大會堂請柬,經過安檢,踏上紅地毯時,心情激動。“這就是人民大會堂,最高權力的象征,領導人會晤外國元首的地方。能在這樣神秘而神圣的地方舉行慶典,我感到很自豪,也充分體現了這次會議的檔次。”
踏入金色小禮堂后,隨著閃光燈咔嚓亂響,所有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拍照留念。由于到會人員太多,南方測繪不得不臨時把員工請出去,為嘉賓騰地兒。
南方測繪還邀請了行業主管部門的領導出席慶典,而他們中的一些人從不參加商業活動。黃吉海認為這也大半歸功于人民大會堂。“大會堂讓這次活動顯得分外莊重而有意味。”
回憶起人民大會堂的活動,黃吉海語氣歡快,得意非凡。活動總花費不過20萬元,但公司由此極大地提升了品牌認知度。
演出公司和外企的青睞
而對于京城各路演出公司而言,人民大會堂更是2006年度大型商業演出的不二之選。“由于奧運場館維修,北京找不到第二個地方可以像人民大會堂一次容納數萬人。”北廣傳媒影視公司演出部經理杜明翰說。
商業演出青睞人民大會堂,從節目表就可看出端倪:2006年12月28日到2007年1月26日,短短一個月時間,一共有10場商業演出,既有“2007新年芭蕾盛宴《天鵝湖》”,也有“再唱西北風——阿寶2007新年演唱會”這樣的通俗節目,票價最低者50元,最貴則達到1800元。
大導演張藝謀也和人民大會堂結下不解之緣:2002年12月14日,《英雄》在人民大會堂首映,曾被解讀出“商業大片背后的政治意圖”,2006年年末,《滿城盡帶黃金甲》又一次現身于此,馬上落下“炒作”的惡名。
出沒于人民大會堂的另一股商業“生力軍”,則來自跨國公司和外企。
2001年,劉希平所在的公司為英國的路透新聞社承辦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150周年慶典。劉希平津津樂道于人民大會堂比一個足球場還大的宴會廳,數百張圓臺子次第鋪開,訓練有素的服務員穿梭其中。“他們都面目清秀,身高相仿,看上去賞心悅目,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非有錢就能進大會堂
不少人由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只要企業愿意出錢,就可以在人民大會堂舉辦一個商業活動。
事情看來沒這么簡單。按規定,如果沒有正部級的介紹信,不能在這里舉辦活動;各種產品的新聞發布會,也要有國家新聞出版署的備案。
介紹信的規定現在已有所放寬,但最起碼也得司局級的。然后,還需要提供一份盡量詳細的活動計劃書,以便于確認會議時間是否沖突,會議內容是否“健康向上”。如果涉及到外籍演員或者外籍演出團體,需要有相關國家機關的批準文件。
“正部級的介紹信”對不少的商家來說是件傷透腦筋的事情,南方測繪的黃吉海為了這封介紹信,在北京奔波了整整一周,磨破了嘴皮,發動了所有可以想到的社會關系,轉了五六個彎,終于在行業主管部門那里拿到。
人民大會堂能用來出租的場地也頗有講究,一位知情人士介紹,像大禮堂、小禮堂、宴會廳、部分省廳是可以向外租用的。有些廳因為位置關系不能對外開放,如天津廳、福建廳、新疆廳、東大廳等。
破冰帶來良性循環
自建成之日起,人民大會堂每周均會安排一到兩天的開放日,讓老百姓可以走進這個神秘的殿堂,一飽眼福。而到文革期間,人民大會堂作為神圣不可近觀之物,被封鎖起來,只限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活動,一道鐵護欄橫在大會堂東門外的廣場上,警衛線則一直向東延伸到廣場西側的馬路沿上。
“人民大會堂還是人民的嗎?”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這一做法遭到一些老同志的炮轟。1979年1月27日晚,中斷了15年的首都群眾春節聯歡晚會再度舉行,復出的鄧穎超代表黨中央宣布:人民大會堂將重新向各界群眾開放。
人民大會堂的商業化,正是在此時開始破冰——參觀將收取門票。在萬人禮堂“江山如此多嬌”圖畫前,也特意開設了兩個攝影點,收費拍照。
而后商業活動開始削尖腦袋擠進去:先是國家一些部委開始在這里辦活動,然后是大型國企,此后是外資巨頭,最后才是國內的民營中小企業。
當時大會堂的年財政支出幾百萬元,大會堂管理局曾向主管部門中共中央辦公廳遞交過一份“五年改革設想”,希望試行部分企業化管理,力爭5年內達到行政經費自給自足。人民大會堂的商業活動,此后漸入高潮。
不過議論也因此風起:2006年9月22日,韓國安七炫與中國臺灣吳建豪這對“跨國組合”的演唱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演出進行到50分鐘時,就被臨時喊停。叫停的原因是在演唱的過程中,有激動的歌迷甚至跳上了人民大會堂的桌子。
“這有點過分了,組織工作沒做好。”北廣傳媒影視公司演出部經理杜明翰說,“人民大會堂是國家議事的場所,代表著國家的尊嚴。”
“但把這么大的一個公共場所閑置起來,是不是一個最好的處理方式?”北京的一位觀察人士更看重其象征意味,“把人民大會堂還給人民,用行政命令能做到嗎?不能,但從長遠看,商業能做到。”
其實,對于承接社會性的活動,人民大會堂一直堅持三條原則:
第一,不能影響黨和國家的政治活動進行,如果有沖突,外部單位的活動就要取消、改道或者改廳室。第二,不能影響大會堂的安全,每一個進入大會堂的人都要接受嚴格的安檢。第三,不能影響大會堂的政治聲譽,所有活動必須健康積極向上。
“人民大會堂的職能是為黨和國家的政治性活動服務,為各省市、各部委、機關團體服務,為人民群眾服務。”管理局的一位人士說,“這個職能并沒有改變,只是范圍擴大了。”
“過去大會堂完全依靠國家撥款,是一個吃財政的單位。自從開放以后,人民大會堂逐步有了一定的收入,以收抵支,減輕了國家負擔。到80年代末的時候,在行政經費上我們已經可以達到自收自支了。”一位內部人士這樣透露。
“大會堂開放走的方向是正確的,但肯定有人想鉆空子,我們也面臨著如何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和抵御各種風險的能力。”
一個商人的體會
33歲的商人李志起擁有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品牌營銷公司。他做了個大致估算,2006年承接的商業活動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約占三分之一。
“近幾年,越來越多的民族品牌熱衷于進入人民大會堂。而以前,那里幾乎是外資行業巨頭的天下。”李志起說。他覺得人民大會堂對中國人的影響力難以替代。他發現50~60年代出生的人,尤其青睞人民大會堂。而很多70年代之后出生的老板,可能就會選擇一個風景秀麗的場所開會。
在媒體邀請方面,人民大會堂也有其優勢。“比如說,在其它地方,要是讓記者等半個小時,那是很難想象的。但在人民大會堂,要停車,過安檢,耽誤時間,大家就覺得很正常,似乎人民大會堂就該那樣,折騰一番后,還覺得活動規格更高了。”李志起說。
回顧起這些年的經歷,李志起覺得自己對人民大會堂的心態,經歷了一個從“仰視”,到“平視”,到現在覺得“它跟一般場所沒有區別”的過程。“我覺得人民大會堂從封閉走向開放,從高高在上到逐漸親民,是件好事。而且,在目前的國內環境下它需要做些經營養活自己,也是非常正常并且可以理解的。”
(范毅冰薦自《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