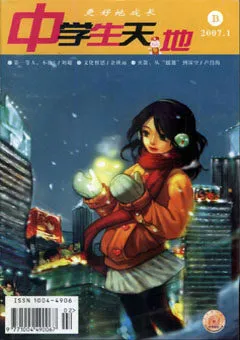師生關系在美國
一日為師,終生為父。說到老師,我們往往想到的是威嚴,是權威。對于老師,我們往往有的是崇拜,是敬畏。但在美國,老師的概念則完全不同了。在美國,教師僅僅是眾多普通職業的一種,他們的收入來自納稅人,因此更像是公仆。師生之間的關系也因此與中國的大相徑庭。
當我第一次來美國交流學習的時候,被熱情的校長領到每個教室作介紹。當時我想:大家正在上課呢,這樣打斷不太好吧。可走進第一個教室,我就完全放心了:大家正哄笑成一團呢。后來才知道,原來老師剛給大家講了一件前一天發生在小鎮上的趣事。美國的課堂,尤其是大學之前的課堂,是十分隨意的。一節45分鐘的課,可能有30分鐘花在與教學無關的事情上。一般點名就要占用10分鐘左右。學生曠課是常事,所以每節課點名是必要的。老師時常一邊點名還一邊提問:“杰西卡,你家的那條小黑狗昨天跟那只剛來的野貓打架了嗎?”“凱瑟琳,你媽媽運回的那一卡車木頭是干什么用的?”“托尼?托尼怎么沒來?托尼昨天在橄欖球賽中受傷了?”……老師趁著點名的機會,了解了每個學生的信息。點名結束之后,老師甚至會問:“歐文,你最喜歡什么顏色?紅色?好,今天我們就用紅色粉筆。”
美國中學生在課堂上回答問題跟國內學生有一些顯著的區別:首先他們從來不站起來回答問題,其次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會說“不知道”。老師需要不斷地給學生暗示,而學生則像猜謎一樣,猜著猜著就有可能引入另外一個話題,等到重新回到正題的時候,往往離下課已經不遠了。因此總體來說,美國學生上課重在發散思維,而不是系統地、有目標地進行學習。有些老師能夠很好地掌握方向,讓所聊的話題與學習內容有所聯系,有些老師則十分擅長發現學生的個性與專長,讓話題來引導教學。
在這樣的課堂里學習,進度自然快不了,但是老師從來不給學生壓力,讓學習總是在一種輕松而愉快的氛圍中進行。當然,這種放任學生、缺乏管教的做法有時也會出現一些不小的問題。曾經聽說隔壁班有個叫Peter的同學,交了一套讓人哭笑不得的數學作業。其中有一道題目是“Find x”(求出x的值,find也可譯成尋找)。Peter將題目中的“x”圈了起來,然后注釋道:“x在這里!”老師在作業旁邊詼諧地寫了諷刺性的評語“Very funny Peter”(真好笑,Peter)。
美國的老師只鼓勵學生,從不批評學生。即使是學生回答錯了,老師也會說“這不是最好的答案,請再想想”。記得有一次數學課講到概率,老師把全班同學分成四個組,讓每個組各自討論然后匯報答案。結果四個組出現了三種不同的答案。老師把三種答案一一在黑板上講解。當然,三種答案其實只有一種是正確的。在中國,另外兩種答案肯定是要得紅叉的,可美國老師卻對大家說:“這些答案都有一定的道理,只是其中的一種更加科學。”事實上,另兩種答案分明就是徹底錯誤的。美國的教育方式,鑄就了大家“沒有錯誤,只有不夠好”的觀念。
這種觀念與中國的“應試教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的應試教育往往會讓很多學生的思維逐漸單一化,即使是文科題,也都限定了十分狹窄的答案范圍。學生做的實驗是專家們經過反反復復的研究,最后印在書上的。這樣做雖然保證了實驗的科學性,卻把實驗的探索性完全抹殺了。相比之下,美國的老師一般不會要求學生做那些難度很高的實驗,但他們會讓學生自己進行實驗設計。一般實驗的材料都選用常見的廚房用品,這樣基本上不會有什么危險。雖然實驗的原理或得出的結論很簡單,但學生們在探索過程中學到了很多。老師這樣做的目的并不是為了讓學生記住實驗本身,而是培養他們的能力: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
當然,只“授人以漁”就教育而言顯然是不夠的。美國老師只注重收集信息的工具,卻不注重信息本身,因此學生經常對具體的問題一問三不知,首先想到的就是上網找答案、查書。對于一些高深的知識,這么做也許是高效率的學習方法,可是對于知識儲備而言,這是很危險的。很多場合,能夠迅速調用頭腦中的知識儲備來解決問題是一種實力的體現,也是個人素質的標志,這方面美國學生顯然不如中國學生。
較中國的學校而言,美國學校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班級里學生相對較少,因此教學過程就很人性化。老師不僅能夠對每個學生的學習情況有全面的了解,而且可以關心學生生活上的瑣事。學生因此也能得到更多特殊的幫助。第二次來到美國,我所讀的大學,學生不到10000個。現在我平均每天都會有將近半個小時的時間和系主任聊天。這在中國的大學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而恰恰是這種人數上的優勢,使每個美國學生都能夠得到充分的關注,能夠得到自己最需要的幫助。
我們大學的教授會親自打電話來詢問我們做作業的情況,有時還主動給有濃厚學習興趣的個別同學專門的資料。更令人驚訝的是,教授們平時都在不斷地“充電”,他們有的時候會坐在教室里和我們一同聽課——數學系的教授修西班牙語,政治系的教授修藝術課——這種現象在美國很常見,而這種學生和教授之間所形成的“同學關系”,更為師生間互相交流架起了橋梁。一個同時修數學和西班牙語的學生,也許可以幫助數學教授學習西班牙語,而同時也得到了教授在數學上無微不至的輔導。作為一個國際學生,我更是得到了教授們的百般關照。過節放假的時候,教授會請我去他們家,有的還做了我的免費房東。因為不像中國的校園那樣人山人海,美國的學生幾乎可以認識學校里的每一個人(美國也有大學校,但小學校居多)。要辦事,要尋求幫助就方便多了。
中國的小學生,即使是中學生,都把幫助老師(諸如擦黑板之類)當作自己的義務。而在美國,老師是為學生服務的。老師不僅要自己擦黑板,而且還有義務盡可能地滿足學生的要求,以幫助、鼓勵他們學習。我作為交流學生在美國學習時碰到過一個特別好的化學老師,每次班里有同學過生日,她都會買來巧克力分給每個人,每當學生取得一點點進步的時候,她就自己掏錢買獎品,學期快結束的時候,她還會自費把飯店的廚師請進教室來辦一桌酒席,請大家吃飯。當老師試著降低自己的地位,嘗試著與學生平等相待的時候,教育又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學生不僅得到了知識,擁有了自信,而且學會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