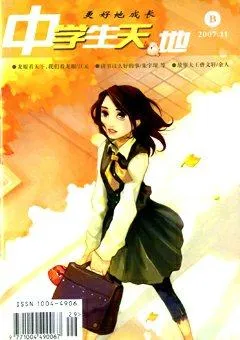故事大王曹文軒
對于那些胸懷北大夢、文學夢的年輕學子,曹文軒很容易成為他們的崇拜偶像與人生榜樣。曹文軒在青年時代就取得了諸多文學成就,令世人矚目。我終于有機會見到了曹老師,并非常榮幸地聆聽了曹老師講課,那種激情澎湃、酣暢淋漓的講課至今還回響在我的耳邊,令我久久回味、陶醉和思考。
在我寫小說之前,我就已經在聽小說了
余人(下文簡稱余):能簡單談談您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嗎?
曹文軒(下文簡稱曹):我的童年、少年是在物質極其匱乏的歲月中艱難度過的。那個世界一窮二白,非常荒涼。那又是一個極其閉塞的世界——我的祖母,一輩子就沒有走出超過五平方千米的范圍。在她看來,除了她生活的那個小小的世界以外,這個世界就只有一個地方,那個地方與她生活的那個世界同等大小。在她看來,凡是離開這個地方的人,當兵也好,上學也好,出差也好,就是到同一個地方去。因此,在我上大學以后,她就會常常站到路口去等待一個從外面回來的人,如果見到了一個當兵的或一個貨郎,就會問:你見到我大孫子沒有?由于如此閉塞,所以人們對那樣的貧窮絲毫不加以懷疑,以為這個世界就是這樣,人生下來就是這樣生存的。進入青年之后,情況有了好轉。當然貧窮也給了我巨大的精神財富。它給了我想象力。想象力是從“無”盼望“有”的過程中激發出來的。它給了我悲憫情懷,給了我堅韌不拔的性格。
余:小時候對您影響最大的人是誰?
曹:父親。父親沒有給我留下什么物質遺產,但他留給我的精神遺產卻價值連城。是他教會我用善良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對人要有善意,要肯助人,尤其是對那些弱者要給予同情和幫助。他這樣的人生理念,天長日久,融入到血液中、靈魂中。因此,不論在何種場合,我就很自然地馬上想到在那個場合誰是弱者。這幾乎成了一種本能。我不會去忌妒強者,但我更容易成為弱者的朋友。“積德”,這是父親人生中的關鍵詞。在他看來,積德會給他帶來精神上的愉悅和崇高感。并且,他相信這個世界在冥冥之中是有法則的,其中因果報應就是一條。父親積極的生活態度,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他是永遠向上的,無論是在何等艱難的情況下都是樂觀的。他連走路都是面朝天空的,并且喜歡大聲吼唱。我今天寫小說,也要感謝他。因為是他給了我敘事能力。他被那個地方上人稱之為小說家——就是會說事的意思。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一經他敘述,就立即大放光彩。因此,他不管走到哪兒,都會成為人們的中心,能夠給人帶來快樂。我就是在他的敘事中長大的,因此早在我寫小說之前,我就已經在聽小說了。
余:您覺得自己青少年時代做得最正確或最得意的一件事是什么?
曹:以為做得最正確的事記不太清楚了,最得意的事倒記得——我成功地當了一回福爾摩斯。一天,我養的一只即將會飛的鴿子丟了。我小時候是鴿迷,那只鴿子又是我最珍視的。我發誓一定要將偷我鴿子的小偷找出來并追回我的鴿子。那些天,我就將自己想象成一個精明的大偵探,開始了調查和偵探。我簡直就是一個天生的高明的偵探,因為我居然用推理的方式來破解鴿子的失蹤之謎。我躺在床上,進行了十分嚴密的、邏輯性極強的推理。最后得出的結論是,鴿子是一個家在三里外的孩子偷的。我悄悄潛入這個孩子的家中,很快就從他家的一只雞籠里發現了我的鴿子。然后,我回到家中,將我偵察的結果告訴了父親。父親懷疑地問:你有把握嗎?我說:絕對有把握。父親來到這個孩子的家,果然看到了我的那只鴿子,批評了那個孩子,并與這孩子的家長交涉,最終將我丟失的鴿子取回來了。
余:您覺得自己青少年時代做得最失敗的一件事是什么?
曹:高中快畢業時,用了好幾天時間寫了一封情書,托另外一個與我十分要好的男生將它轉交給我一直喜歡的女生,卻石沉大海。那時,我感到自己是這個世界上最失敗的人。當然,后來過了很久我才知道,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那個男生其實并沒有將我的情書轉交給那個女生。這件事后來寫進了我的一部長篇小說《紅瓦》中。
讀書寫作長精神
余:您是什么時候開始創作的?是什么力量讓您走上了文學之路?您有文學引路人嗎?
曹:18歲那年開始寫作所謂的文學作品。沒有什么崇高的目的,只是因為當時的農村,生產勞動不堪負荷。我一直在心里希望著有一天能擺脫這樣的勞動。可是除了勞動,當時在農村就再也沒有出路。后來,我終于找到了一條出路:文學創作。當時叫業余文學創作。我讀書時作文一直寫得不錯,一搞起所謂文學創作來,馬上就引起了縣文化館的老師的注意,很快我就被抽調到了縣文化館業余文學創作組。有一個人對于我的一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他就是李有干先生。他很早就是一個作家,因為政治的原因,一直在縣文化館做一個普通館員。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就是專門談他的。是他將我引導到了文學這條路上。對于他,我能說的就是一句話:永遠心存感激。
余:您覺得文學對人生有什么作用?過去的文學青年和現在有什么不同?
曹:人類的進步是與文學絕對聯系在一起的。我們無法想象,人類如果沒有文學,又將會是怎樣。我曾經寫過一篇長文,就是談文學與人類的關系的。文學在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方面,功勞巨大。人類成為有情調的物種,文學功不可沒。一個人的人生如果沒有文學的照應,不會是多么有質量的人生。過去的文學青年不玩文學。也許選擇文學的動機很功利,但一旦選擇了就很尊敬文學,更不會褻瀆它。那時的文學青年,將文學看得很神圣。文學什么時候成為過中心嗎?文學從來就不是中心,但文學是我們無法丟棄的。
余:您至今最滿意的作品是哪一部?最不滿意的呢?
曹:這個問題,我已被問過多次。我曾在一所小學問孩子們,如果不是計劃生育,你的母親生了好幾個孩子,這時有人問你母親喜歡哪一個孩子。你的母親會怎樣回答?孩子們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大聲說:都喜歡。
余:您怎么看像韓寒這樣的“偏科”現象?您怎么看文學明星化、娛樂化現象?
曹:韓寒是一個無法模仿的人才,韓寒就是韓寒,他不是造物主流水線上生產出來的,是一個例外。我是最早欣賞他才能的人之一,早在新概念作文比賽中就認識了他的文字。我還曾經與北大交涉過,希望能給這樣特殊的人一條“旁門左道”。我不喜歡文學明星化,我贊成娛樂,但今天的娛樂是質量十分低下的娛樂。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人類,總得有一桿精神標尺矗立在那里,如果這個標尺倒下了,就剩下一個樂子,是十分糟糕的。
余:您能談談您的新作《大王書》嗎?您為什么要改變您最拿手的寫實風格改寫幻想小說?
曹:我曾對一些媒體說過,其實,我在骨子里始終喜歡恢宏場面,我平時的思想風格以及表達思想的方式也都是那樣一種路數,我很難在思想和表達思想時控制我的激情。我平時喜歡的文學作品和藝術品也是偏重于大調作品。但我就是這樣一個看上去很分裂的人,在寫小說時會忽然變得十分安靜,十分細致,十分有耐心,甚至有點女性化。那時會有一種氛圍包裹著你,你的敘述自然而然地就走向了那樣一個方向。一種情調,一種趣味,會彌漫在你的心頭。所以就有了《草房子》《紅瓦》《細米》《青銅葵花》以及《天瓢》等。可是我知道,我的欲望里還有別樣的向往。海明威既寫了《老人與海》這樣很有氣勢的作品,也寫了《雨中的貓》這樣很細膩的作品。但如果仔細去研究,還是能夠發現,盡管看上去風格有這樣大的差異,但底部襯著的美學、倫理、哲學與情感還是一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大王書》不一定就是突破。當然說突破也可以,因為它畢竟是另一種面孔了。為了維持那樣一種氛圍,最近我閱讀的書都是一些大調的作品,比如《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等。我要找到那樣的場面感:風起云涌、呼嘯而過、尸橫遍野、血流成河、宏大、壯闊、具有鐵質。
余:您最想對中學生說的一句話是——
曹:讀書長精神。
曹文軒,著名作家、學者。1954年生于江蘇鹽城。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同時擔任中國作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作協副主席。最新創作的多卷本長篇小說《大王書》第一部《黃琉璃》正在熱銷中,后續作品也將陸續和讀者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