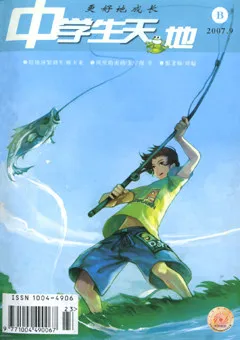少用腦子多用心
如果你要聽于丹的課,必須向守在教室門口的保安出示北京師范大學的學生證,否則會被謝絕入內。于丹的古詩詞鑒賞課是一門本科生的公共選修課,教室里學生的座位卻“一個蘿卜一個坑”地被排好了次序。不過,真的要混進教室依然有各種辦法,教室后三排的“旁聽專用座位”上就坐滿了拿著鮮花和相機的“于粉”。不一會兒,穿白色小西裝,系綠絲巾,化淡妝的于丹老師進入教室,立刻有人上前索取簽名。
和“百家講壇”中的她一樣,大學課堂上的于丹依然魅力不減。有人這樣評論她:于丹開創了一種口語表達的范式。她教的是“古典詩詞鑒賞”,然而除了引文之外,你絕對聽不到任何艱澀的詞句,所有內容她全用曉暢的大白話解釋得清清楚楚。一下課,于老師便忙得令人嘆為觀止,請求與她面談的陌生人不計其數,讓人覺得她的時間被各種力量爭相拉扯。但得知我們來自中學生媒體,她便爽快地利用課間在教學樓走廊上接受了采訪。在她轉身告別時,經過的一位北師大老師跟她打招呼:“于老師,您真是太忙了!”
不要咬牙,要Enjoy
記者:您的高中時代是什么樣的?
于丹:哎呀,我要是說出來,現在的中學生一定會嫉妒我的。我在高中時代非常快樂。當時我讀的是北京四中,這是北京最好的中學之一。當時在我們那個班里,學習不好沒關系,但不會玩不行。你一定要合群,要會玩。平時我們有很多活動,踏青、詩歌朗誦、看電影、討論會……我記得高考前一個月,我們老師還領著我們去爬山。其實我們的學習任務也是非常繁重的。當時高考升學率不像現在這么高,只有3.5%,我們一個班能考上大學的也就只有三四個。但是大家都沒把高考當成人生發展的唯一途徑。我認為,人的生命活力是學習的前提,我們應該學習把握更多幸福的能力。
記者:中學時參加這么多活動,您是不是班里的文藝骨干啊?
于丹:不是不是,哈哈,我都是跟著湊熱鬧,但參加活動本身就是一種享受,特別開心。
記者:您提到“享受”這個詞,您還說過“不要讓人生成為咬牙的悲壯過程,要懂得Enjoy”。可如今的高中生不如你們當時那么瀟灑,來自學習和生活的壓力非常大,您認為大家應該怎么Enjoy呢?
于丹:我給中學生的建議是——少用一點腦子,多用心。現在的中學生壓力的確很大,可是要記住,我們不能學到了技巧,卻失去了快樂的能力。如果學習都不快樂了,那還讀書干什么呢?我曾經看過15世紀一個宗教改革家寫的一本書,在這本書中他講了自己青年時代的一個小故事,而這個故事改變了他的一生:
有一天他路過一個烈日炎炎下的巨大工地,所有人都在汗流浹背地搬磚。
他去問第一個人,你在干什么呢?
那個人特別沒好氣地告訴他,你看不見啊,我這不是服苦役——搬磚嗎?
他又拿這個問題去問第二個人。這個人的態度比第一個人要平和很多,他先把手里的磚碼齊,看了看說,我在砌一堵墻啊。
后來他又去問第三個人。那個人臉上一直有一種祥和的光彩,他把手里的磚放下,抬頭擦了一把汗,很驕傲地說,你是在問我嗎?我在蓋一座教堂啊。
第一種人的態度我稱為悲觀主義的態度。他可以把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看作是生活強加的一份苦役,他關注的是當下的辛苦,當然這也是確實存在的。第二種人的態度我稱為職業主義的態度。他知道自己在砌一堵墻,這堵墻是一個局部成品,他知道要對得起今天的崗位,所以他的態度不低于職業化的底線,但是他沒有更高的追求。而第三種人的態度我稱為理想主義的態度。也就是說,他不僅看到眼前的每一塊磚、每一滴汗,他更明白自己的勞動是在通往一座教堂。他明白,他的每一步都是有價值的,他的付出一定會得到最終的成全。此時,他所做的事情關系到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夢想,關系到我們最終能不能建起一座教堂。而同時,因為有了這個教堂夢想的籠罩,也成就了這樣一個超出平凡的個體。
中學生面對學習的態度,要像那第三個人一樣。要有自己的人生坐標,對人生多一點規劃。這樣就不會只專注于當下學業的辛苦,而忘記了每一步都通往夢想的旅程。這樣,你們的人生才能更廣闊、自由,才能夠讀出未來的意義。
淺而能深,近而能遠
記者:在大學里,在“百家講壇”,您都一直在講古代文學經典,能不能就閱讀經典作品這個話題,給中學生一點建議?
于丹:其實高中時大家的學習任務重,讀很多經典作品不太現實。開卷當然有益,但我不太贊成在這個時候閱讀,尤其不要背太多。因為這些東西是需要領會的,領會了,自然就通了。經典閱讀是一個一生相伴的過程,從高中開始已經有些晚了,應該從小學有空時就開始積累。經典文化是需要大家用一輩子慢慢接觸的。
記者:那么如何寫作呢?在您眼里怎樣才算是好文章?
于丹:啟功先生是我一生都無比敬重的老師。讀本科的時候,我曾問他:“什么時候我們寫出來的東西才能符合中文系的身份,能專業化一點啊?”你知道啟功先生怎么回答嗎?他說:“什么時候你們寫的東西不像人話了,那就是你所謂的那個‘專業化’了。”這句話留給我很深的印象。從那以后我知道,好的文章應該“淺而能深,近而能遠”,而不應該“掉書袋”。我們很多時候為了顯示自己的學識,把文章寫得佶屈聱牙、晦澀艱深,那絕非文章的至境。你看真正的大家有誰把文章寫得不像人話?淺近直白、通俗易懂的,才是真正的好文章。
一生修煉,未必完滿
記者:您對于爭議怎么看?
于丹:舉個例子,關于荊軻刺秦,歷史的評價是從是否有利于文明進步出發的,從這點看,秦滅六國統一天下是進步的標志。而道德評價是從倫理的角度出發的,從這點看,荊軻刺秦被認為是義舉。荊軻刺秦本質上就是以秦王為代表的文明與荊軻為代表的倫理的沖突。這是一個久遠的二元悖反。悖論是貫穿整個中國歷史的。其實歷史上真正引起爭鳴的,都是各個角度看都有道理,但都得付出代價的故事。
記者:高中生正處在一個對外界評價很敏感的狀態,會很在乎別人對自己的看法。您對大家有什么建議?
于丹:人生是一個成長的過程。十六七歲的年紀讓他完全不在乎別人的看法是不切實際的。中國有句古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從心所欲是真正尊重生命個體,聽從自己內心堅持的聲音;不逾矩是尊重社會規則,不超越規矩法度,能夠尊重他人情感。按照古語,要到七十多歲才能做到這樣,所以現在要慢慢來。人的成長有一個過程,一直是在對于自我的確認和對社會規則的融合、掌握中達到平衡,一輩子也就在追求這個平衡,不能太強求。
記者:“百家講壇”之后,您紅了,同時也成了一位富有爭議的人物。您也是用這么平和的心態去對待爭議的吧?
于丹:(笑)我不敢說自己有那么高明的境界,我也一直在追求這個狀態。有句話叫“一生修煉,未必完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