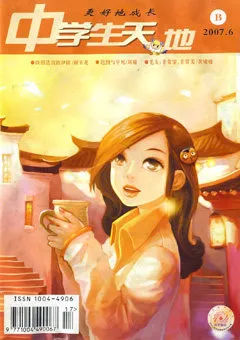毛尖:非常罪,非常美
毛尖,知名作家、影評人,籍貫浙江寧波。獲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外語系學士學位,中文系碩士學位,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學位,現任教于華東師范大學對外漢語系。著有《非常罪,非常美——毛尖電影筆記》《當世界向右的時候》《慢慢微笑——毛尖自選集》《沒有你不行,有你也不行》等。
我讀過毛尖的兩本書,《非常罪,非常美》和《慢慢微笑》,想象中的她是個敏銳的、瘦而高的女子。但是麗娃河畔(華東師大內)的會晤,讓我看見了一個想象之外的毛尖。她戴著粗框眼鏡,扎著馬尾,一身運動裝束,談吐中滿是不假思索的直率。飛速的話語在舌尖上一圈圈地旋轉,像激流串起了一大堆小石子,“嘩”地涌下去,錚錚亂響。
這是朋友之間的絮叨,如同拉家常般親切。雖然她比我大了十幾歲,但是沒有一絲孤高睥睨的“過來人口吻”。所有年紀的孩子在她面前都是平等的,因為她也是個孩子,只是歲月鍛煉了一種成熟。
記:你是一個著名的影評人,能否談談電影在你的成長中留下的印象?
毛:小時候,父母給我們的精神獎勵一般就是看電影,所以看電影從小就和我最輝煌的人生記憶相關。回想起來,年少時看了那么多次電影,真的一次都沒遲到過。
記:你在書中曾透露,你大學時候為了看電影曾經自制假票。這聽上去挺有趣,能談談嗎?
毛:這事情無論如何不能當成英雄事跡說,不過,當時各大學影院賣的電影票真是非常簡陋的,只要知道當晚的電影票是什么顏色,撕一塊相同顏色的海報就可以在20分鐘內炮制一張假票。我們的手工大概是不錯的,因為曾經有人持著盜版票去跟人家爭座位,居然成功了。
記:你喜歡看什么樣的電影,喜歡哪位導演?
毛:當年我在香港讀書,有時間就看安東尼奧尼和費里尼的片子,甚至像阿侖·雷乃導演的《去年在馬里安巴德》這樣沉悶的電影,我也由衷地喜歡。也許是因為當時自己的腦子比較閑吧,喜歡看難度系數高的影片。但這些年,自己忙,就喜歡看香港電影,看武俠,現在最喜歡看《24小時反恐》。
記:再談談咱中國電影吧,現在的中國電影市場似乎越來越好了。
毛:恐怕不是這樣吧。現在的中國電影還是有很多限制的。有一次電影節,我帶學生翻譯字幕,所有影片中的臟話,各式各樣的都只能翻譯成‘他媽的’,真沒意思(笑)!還有那些大片,難道你們不氣憤嗎?我只喜歡拍紅高粱的張藝謀,他現在拍的是什么呀?還有陳凱歌,看到他在電視上為了《無極》和老婆到處自我吹噓時,我哭啊!當年那樣心高氣傲的一個人,現在居然也商業化到了這個地步。
記:可我們不能否認,雖然沒有口碑,但在市場方面,這些大片還是有一定意義的。
毛:要說市場,80年代那才是電影的市場時代,《大眾電影》有高達800萬份的發行量!我記得小時候去看電影,電影院是沒有空位的。電影票總是很緊俏,大家都是排隊買票。現在的電影正在努力挽回一部分流失的觀眾。電影沒落是一件沒辦法的事情,雖然我更喜歡看《三峽好人》,但是我媽媽他們就不喜歡,因為誰愿意掏錢在銀幕上再溫習一遍自己的生活呢?生活是平淡的,甚至是不順遂的。
記:既然這么不滿意現在的電影,那有沒有想過自己操刀,做個編劇呢?
毛:沒有,我沒這個才能。還有,我們現在坐在這里說別人容易,但是真要自己動起筆來,也有各種牽制。有時是不得不加戲,比如寶馬制造商投了錢,那也不得不給車子露個面。
談起讀書時代的故事,共有的話題使人覺得她不過比我們早讀了幾年書而已。她說她小時候喜歡看武俠小說,就是那些當年的“禁書”給了她想象力,使她對文字擁有了一種不受束縛的能力。再大些,她讀了不少名著,各家的文風都對她產生了影響。我劈頭就問她喜不喜歡張愛玲,因為覺得她的文風似乎有張愛玲的影子,她說喜歡,但談不上“張迷”,因為博愛而不是單戀,才能造就一個作家。
我打趣說讓毛尖談談少年時候的“風流歲月”,她不禁啞然失笑,稱她小時候其實是個很乖的孩子。
毛:其實我小時候是個乖孩子,小學時還是大隊長。后來讀中學了,漸漸開始叛逆。只要是老師家長不支持的閱讀,我都如饑似渴。有一次,因為看一本閑書逃了圖畫課,被老師批評還不服氣,直接跑到校長室去理論,但是校長不愧是校長啊,春風化雨地消解了我的“革命熱情”。
記:那么大學呢?
毛:大學時候我們有青年修養課,但沒勁得很,于是大家都逃課。有一次老師點名,當時只來了二十多個同學,點名顯示全部到齊了,原來是這二十多個同學替八十個人喊了“到”,老師的臉色那叫一個難看啊。哈哈哈……
談到這里,我不由自主地記起大學時代一位老師的諄諄叮囑——“不會逃課的孩子是不會學習的”。這句話的意思當然不是蠱惑青少年往歪路上走,而是鼓勵大家在有限的時光內選擇真正值得自己做的事。這種逃課是一種節儉。我正歪想著,毛尖突然發問了,你大學的生活快樂嗎?在她看來,人生最快樂的就是本科和研究生階段無憂無慮的生活了。
毛:我讀大學時,學校里有數不清的文藝沙龍,雖然我是讀外語的,但也去參加詩社什么的玩玩。當時也沒想別的,就是因為好玩,而且社里男生多(笑)。其實現在想起來,沙龍里到底討論了什么已經完全不記得了,只記得在沙龍里誰跟誰戀愛了。
記:記得你書中提到過有一次詩社搞了個活動,和海子有關。
毛:對。那次社里說有大事宣布,我們到現場后,社長用沉痛的聲音說,海子自殺了。其實當時我們很多人對海子并沒多少感情,甚至有人問“海子是誰”,可是后來高年級的同學一個接一個上去朗誦海子的詩,當時就有人哭了,我也覺得悲傷,跟著哭起來了。
也許這就是大學文藝生活給毛尖的印象,再往后,她慢慢接觸這些詩,漸漸用自己的方式在文學里成長。到現在,她已經習慣于在文字里安家。于是采訪的最后,我們希望她用自己的經歷為青少年提供一個成長范本。誰知她竟連連搖頭。
毛:我的經歷不具有普遍性。你知道我很大了還在看小人書,后來念了初中就看武俠書,這可一點都不具備示范作用啊(笑)。
記:那你對青少年閱讀方面有什么建議?多少談點吧。
毛:現在很多孩子都喜歡看《哈里·波特》之類的書,倒不是說這有什么不可,但是閱讀是個往上的過程,你要以此為階梯,慢慢去閱讀更高級的東西,而不能看了之后,再去看那些層次比它還低的東西。也就是說,看了《哈里·波特》,再看狄更斯,就比較好。
記:你覺得現在的孩子需要怎樣的為人準則?
毛:首先做人要正直,還要愛國。是真的,雖然這話挺不像我說的。記得曾經有一個調查,調查青少年下輩子還愿不愿意做中國人,超過一半的人不愿意。我現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從小就要明白自己是個中國人,要愛自己的國家。
訪談匆匆結束了,發現毛尖并不像多數讀書多、寫字多的人那樣“敏于思而拙于言”。她是話匣一開,滔滔不絕,做她的學生應該是幸福的。這個直率又銳利的人將更鋒利的言辭藏了起來,深埋在文字里,等待讀者會心一笑。而她自己,卻是不加修飾的,如同我們喝茶時她點的白開水一樣,滿盛了一碗的清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