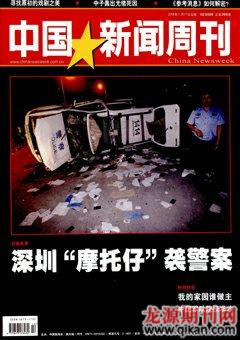“不予受理”的訴權困境
韓 永
一些案件常常為法院不予受理,使公民陷于一種訴權困境,以至于當事人救濟無門,不得不直接求助于信訪,或是卷入群體性事件中去。

在湖南,從汝城到郴州,往返700多里路。黃由儉,一個69歲的老人,從今年5月6日到現在,在這條路上總共跑了8趟。
但狀告汝城縣政府、要求其公開對于該縣自來水公司調查報告的案子,至今在郴州中院仍沒有立案。
在北京,律師唐吉田、張立輝、李仁兵等正遭受類似的境遇。因倡議北京律協“直選”而被扣上“全方位否定我國現行的政治制度”帽子的上述律師,近期相繼對北京律協提起訴訟,卻在受理環節連吃“閉門羹”——北京西城法院既不受理,又不給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就像這樣的起訴從未曾發生”。
類似的遭遇還發生在代理“三鹿奶粉”系列索賠案的律師李方平、因戶口和暫住證問題起訴多地公安機關的律師程海身上。
立案之爭
“我要是跟你說依法做出答復,那不太虛了嗎?我說要請示領導,這才是實話”。
律師唐吉田和張立輝沒有想到,到北京西城法院立案的過程,竟然如此富有戲劇性。
2008年9月24日上午不到10點,唐吉田來到西城法院立案大廳。他參與倡議的北京律協直選一事前途未明,但對此進行定性的北京律協“嚴正聲明”言猶在耳,至今還掛在網上。該聲明將這一行為定性為“妄圖擺脫司法行政機關的監督指導和律師協會的行業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國現行的律師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
這一聲明在網上流傳甚廣,讓組織者之一的唐吉田感覺“很受傷”,決定將北京律協推上法庭,告其民事誹謗。
在7號或者8號窗口,他將起訴狀、身份證復印件、執業證復印件、35位律師的直選倡議以及律協的“嚴正聲明”從立案窗口遞入,一位姓史的法官看了看,說道:“材料我先收下,再研究。”
唐吉田說你研究可以,但要給我出一個收據。史姓法官想了幾分鐘,進去請示一位值班的副庭長后答應了。
唐吉田把此視為一個小小的勝利,因為遞上材料卻拿不到收據的大有人在。《民事訴訟法》第112條規定:“人民法院收到起訴狀或者口頭起訴,經審查,認為符合條件的,應當在七日內立案,并通知當事人;認為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在七日內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對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訴。”如果拿不到收據,那就無法計算決定是否受理的“期間”。很多律師認為,這是在很多“敏感”案件上據理力爭的開始。
10月8日,距離提交起訴狀的時間已有7個工作日。當天下午,唐吉田打電話給史姓法官,詢問立案事宜。史姓法官的答復是:領導已經研究了,該案不能受理。理由是該案“比較特殊”。
唐吉田說:再特殊也是個法律事件,你得用法律的理由來說服我。史姓法官讓唐抽空來一趟。
10月20日上午10時許,唐吉田攜江天勇、李仁兵、張新云、林小建以及專程從通州趕來支援的劉輝5位律師,再次來到西城區法院立案大廳。
6人徑直來到史姓法官窗口。史說此事已不歸他管,可找3號窗口的一位副庭長。還沒靠近副庭長,大廳里來了三四位身穿法院制服的人,領頭的一位四五十歲的女士問:“你們是不是律協的事?”唐說是。這位女士說:“跟我來吧,我們管。”
雙方找了間屋子坐下。這位女士自我介紹,說自己是立案庭的負責人,姓劉。劉姓庭長開門見山,說這個案子是你們協會內部的事情,法院管不了,建議唐吉田與北京律協進行調解。
唐吉田對立案庭是否有權做此建議表示懷疑,并說訴訟之外的調解已經不可能,訴訟之內的調解尚可考慮。
劉姓庭長說這要請示領導,然后再做答復。唐吉田說立案的四個要件明明白白地寫在法條里,為什么還要請示領導?劉姓庭長說了句:我要是跟你說依法做出答復,那不太虛了嗎?我說要請示領導,這才是實話。
會談持續近兩個小時。讓唐吉田頗為費解的是:對方撇開法律上的立案條件不談,卻重點闡述該案的“特殊性”以及自己的無能為力。
此后幾天,唐吉田兩次打電話給這位劉姓庭長,詢問立案的進展。最后一次,這位庭長向唐吉田攤牌:告訴你吧,這個案子不能受理,也不出書面的東西,院里就是這么定的。
對于該案應否受理,中國人民大學民商法博士熊丙萬認為尚存爭議的空間。一個案件是否受理,立案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就本案來說,就是對北京律協是否侵犯唐吉田的名譽權有權做一個簡單的判斷。
熊丙萬認為,法官的這一權力來源于《民事訴訟法》對民事案件受理條件規定的第三項。民事案件受理的條件共有四個:一、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二、有明確的被告;三、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四、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
熊丙萬說,侵犯名譽權的一個基本要件是要有對事實的歪曲,以及由此造成對當事人社會評價的降低。在此案中,立案法官或許認為,《嚴正聲明》對唐吉田社會評價方面的影響并不明顯。
但也有人認為,社會評價降低與否,顯然是審判階段法庭調查階段的事情,因為它依賴于當事人提出證據并進行質證,顯然不是立案法官一眼就能看得出來的。
但是,即使不予受理,法院也必須給予不予受理的裁定。
救濟無門
“這只是憲法上的規定,沒有落實到具體的法條,很難操作”。
律師李方平和老人黃由儉立案遭拒,得到的理由與唐吉田一樣,都是“情況特殊”。更進一步的解釋,給李方平的是:“要等上面的統一部署,”給黃由儉的則是:“要等省高院和最高院的批復。”
黃由儉因此專門跑了兩趟湖南省高院。接待的法官說:要有一個中級法院的裁定,我們才能受理。黃再跑到郴州中院要這個裁定,中院的人說:“要等省高院和最高院的批復。”黃由儉開始認為這是一個“陷阱”。
一位叫馮正虎的上海人,在上海市閘北法院起訴236天后,沒有收到是否立案的通知,決定求助于有關監督部門。他首先來到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室。接待的法官說,實在沒有法律依據讓他受理這個把法官也列入被告的訴狀,建議他去信訪室反映情況。在該院信訪室,接待的法官也表示無能為力,還是應該去找閘北法院信訪辦。
馮正虎沒有馬上去閘北法院,而是先去隔壁的上海市檢察院第二分院。受理的檢察官表示無法受理這樣的控告,因為他們沒有這項監督權。“檢察院一般監督公安局立案后的案件,或者法院終審后的申訴案件,還沒有法律規定可以對法院不受理的案件進行監督。”
馮正虎說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法院不受理的問題,而是法院既不受理,也不按法律規定出具裁定書,剝奪了公民訴權的問題,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應當
有權監督法官的違法行為。接待的檢察官說這只是憲法上的規定,沒有落實到具體的法條,很難操作。并說這是人大應該管的事,建議馮正虎找一下人大。
最后,馮正虎來到閘北區法院信訪辦。事先在二中院聯系好的一位法官表示不清楚此事。
上述程序,黃由儉差不多也走了一遍,結果相似。10月9日、12日,黃由儉沖進郴州中院,指著法院里懸掛的“公正執法,一心為民”的牌匾開始罵人。“你們公什么正,為誰的民?我看都是假的。”“你們就是不敢主持正義。寫這樣的牌子,你們不覺得有愧嗎?”
黃由儉邊走邊罵。這一過程持續半個多小時,“沒有一個法官敢吭一聲。”與黃由儉同去的73歲老人胡桂生也“罵得很兇”。
黃由儉對于司法長達半年的等待從此畫上句號。11月5日、6日,他和另外5位老人出現在汝城縣委、縣政府大門前,脖子上掛著的一塊牌子分外顯眼,上寫“為民請命”。這一行為吸引了很多人圍觀,聲援的群眾多達千人,交通一時陷入癱瘓。
黃由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本來很多下崗職工也要來,縣里37位離休干部也要來,都被他阻止了,“還是不要搞群體性事件,影響不好”。
11月7日晚上,黃由儉又接到很多人的電話,他正在琢磨要不要組織大家去一趟長沙,“去跟張春賢討一個說法”。
法院的“成本”邏輯
那些在法院看來吃力不討好的案件大多被過濾,剩下的都是些既無政治風險又無經濟風險的案件。
有些人將這些群體性事件的蠢蠢欲動,歸咎于法院作為“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崩潰。北京法院系統的一位退休法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的法院不堪任這樣的角色。
他說,一個案子在中國法院所走的程序,跟書本上寫的和國際上的通行做法有時恰恰相反。一個案子在中國能不能立,很多時候要參考這個案子審判的難易程度和執行的難易程度。如果這個案子不好審,或者即便審了也不好執行,立案庭就很有可能將其“扼殺在搖籃里”。
其中的邏輯在于,如果這些不好審或不好執行的案子“冒失”地接下來,很可能會長期“爛”在受理的法院里,法院不得清凈不說,還要支付巨大的應付成本,并有可能失去依據結案率所頒發的各種榮譽。
陜西省某市一位退休政法委書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旦遇到“敏感”案件,一個通常的做法就是召開政法委會議,而作為委員的法院院長鐵定要出席。會議的中心議題在于統一思想。
“領導一干預,案子就不好審了,”上述北京退休法官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與其最終出一個飽受爭議的判決,還不如剛開始就干脆不受理。每一個長了記性的法院都會這么做。”
執行則是更大的難題。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嶸在一次演講中提到:中國已生效判決的執行率有明顯下降的趨勢,其中行政訴訟最為明顯,已從1998年的44.8%下降到2004年的21.1%。他說,這已成為群體性事件的一個誘因。
這一數字變化對于法院來說,意味著執行越來越難。上述退休法官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民事案件的執行尚可使用一些強制性手段,對于行政訴訟中的一些行政機關,法院要適用這些手段還是心存忌憚。
經過縝密的反向推理后,那些在法院看來吃力不討好的案件大多被過濾,剩下的都是些既無政治風險又無經濟風險的案件。
對于不受理案件不出裁定,也成為控制風險的一個重要考量。北京兩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就此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有些明顯符合受理條件的案件,如果一定要出一個不予受理的裁定,要么是語焉不詳,要么是漏洞百出,當事人如果據此上訴,法院就會非常被動。所以寧愿對當事人裝瘋賣傻,也不會出一個書面裁定,免得后患無窮。
這一切做得密不透風,以至于很多當事人已不寄希望于這一道救濟,而是直接求助于信訪,或是卷入群體性事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