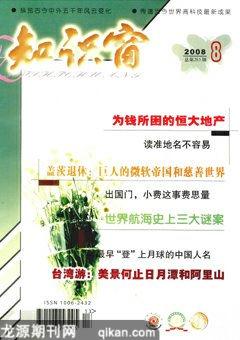讀準地名不容易
曾經的漆樹
據說在80年前,馮玉祥手下的一個參謀在書寫作戰命令的時候,把部隊集結的地點沁(qìn撳)陽隨手寫成泌(bì畢)陽。沁陽在河南北部的焦作地區,而泌陽在河南南部的駐馬店地區。只多了一筆,部隊瞎跑了幾百公里,整個戰役也就完全失敗了。
我也有過把岷(mín民)江洪水讀成閩江洪水的經歷。岷江在西南,而閩江在東南,比沁陽和泌陽之間距離更遠。
誤讀地名是一件很郁悶也很難堪的事情,而且很容易成為一種笑柄。而讀對地名,是對人家起碼的尊重。
浙江的麗(lí離)水被誤讀成麗(lì立)水,臺(tāi胎)州被誤讀成臺(tái抬)州。
安徽的亳(bó駁)州,經常被讀作多了一橫的毫(háo豪)州。
湖北的監(jiàn見)利被誤讀成監(jiān尖)利。
河南的浚(xùn訓)縣被誤讀成浚(jùn俊)縣。
湖南的耒(lěi壘)陽被誤讀成來陽,而真正的萊陽在山東。
郴(chēn抻)州被誤讀成彬(hīn賓)州;
新疆的巴音郭楞,楞(léng)被誤讀成愣(lèng),這兩個字長得很像,一不留神就讀錯。
內蒙古的巴彥淖爾,淖(nào鬧)易被誤讀成卓(zhuó)。所以有一次和巴彥淖爾的同志一起聯歡,他們的第一件事就是熱情地感謝我讀對了他們家鄉的名字,可見平時誤讀率很高。
有些誤讀是因為地名中含有多音字,需要堅持的是“名從主人”的原則,例如:
河北的蔚縣,正確讀音是yù(玉)縣。
安徽的歙縣,正確讀音是shè(社)縣;六安,正確讀音是lù(路)安。
山西的繁峙縣,正確讀音是繁shì(是)縣;長子縣,正確讀音是zhǎng(掌)子縣。
山東莘(shēn深)縣,學生們一般讀不錯,因為有莘莘學子之說;但我到上海又讀錯了,上海莘(xīn新)莊,不念shēn莊。
江西鉛(yán鹽)山,誤讀率一定很高。因為少有人想到普通的“鉛”還是多音字而且是地名專用的字音。反正一不留神我可能就會讀錯。
像福建廈門、廣東番禺、安徽蚌埠,雖然也含有異音字,但因為知名度高,被誤讀的幾率相對比較低。
讀錯山東東阿的比較少,感謝關于阿膠的廣告;讀錯涪陵的比較少,感謝來自涪陵的榨菜。
讀錯山西洪洞的也比較少,因為那句“蘇三離了洪洞縣”起到了積極的推廣作用。
遼寧阜新,在遼寧一般被讀成fú(扶)新,在北京一般被讀成fǔ(撫)新,而正確的讀音卻是fù(富)新。
另外很多情況下是因為有些字根本就沒見過,望字猜音,跟著感覺走。包括我們這些以說話念字為職業、普通話水平一級甲等的人在內,如果能第一眼就讀對95%的中國地名,那就算超水平發揮了。
山西的隰(xí席)縣。
山東的莒(jǚ舉)縣,茌(chí池)平。
河北的井陘(xíng行),蠡(lǐ李)縣。
四川的郫(pí脾)縣,珙(gǒng鞏)縣,犍(qián前)為。
安徽的黔(yī一)縣,樅(zōng宗)陽。
湖北的鄖(yún云)縣。
江西的婺(wù霧)源。
浙江的鄞(yín銀)縣。
江蘇的盱眙(xūyí需宜),邗(hán韓)江,邳(pī批)州。
河南的柘(zhè這)城,武陟(zhì志)。
看著其中的某些字,仿佛回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很多文化和城市的歷史密碼,往往都固化在地名里了。當然,語言是流動的,是液態的,今天的錯誤有些或許就成為明天的正音了,字典只是一個特定時代的語音規范。語音的確定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而這一切都是人逐漸造就的。
(摘自《教師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