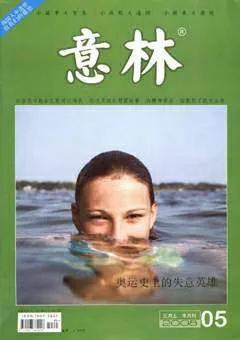文革中遺失的日記
張抗抗
我在這里記述的,是一段真實的往事。
這個遺失的日記的故事,同一個名叫過大江的年輕人有關(guān)。
那一年年初,由于文革中一場突然的變故,我丟失了心愛的日記本。
那兩個日記本,其實是被人強行搶走的。日記中記錄了我剛剛萌發(fā)的一場初戀隱秘的心跡。而我那個初戀的對象,另一所中學的“老高三”學生——那所學校的一派紅衛(wèi)兵頭頭,此時已被另一派“打倒”。那另一派的紅衛(wèi)兵涌入我家翻箱倒柜,發(fā)現(xiàn)了我的日記,認定其中必有可置其于死地的線索和材料,在我同他們發(fā)生了爭吵而又勢不敵眾的情況下,他們拿了我的日記本揚長而去。
幾乎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個人假如在日記中傾訴了自己的心里話,而又不慎將其丟失,肯定意味著一場大禍即將臨頭。
那段日子里,幾乎每一天,我都等待著厄運的降臨。就是在那一年,我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已經(jīng)堅持了10年之久的寫日記的習慣,被我自己徹底放棄。
然而奇怪的是,我日夜擔心的那種情形,卻始終沒有出現(xiàn)。沒有什么人再來找我的麻煩。那兩本日記似乎那樣不明不白、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那一天,過大江這個陌生人的名字,從一封來自杭州師范學院英語系的信中,忽然跳了出來。
他在信中以急切的口氣探問道:在這11年的時間里,我一直珍藏著那兩本日記。如果我能確定你就是日記的主人,我愿意把它們歸還給你……
我當即就給這個叫過大江的大學生回了信。我說,我就是你要找的那個人。
他說那一年自己還是個調(diào)皮的小鬼頭。那天,他被帶到工宣隊的辦公室去談話。但那會兒工宣隊的領(lǐng)導(dǎo)恰好很忙,讓他在旁邊的一間屋子里先等一會兒。
他似乎在無意之中,拉開了桌子的一只抽屜。他好奇地翻開了其中一個本子,胡亂看了一會兒,覺得那好像是本日記。扉頁上寫著一個人的名字。
他又接著看了一會兒,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女孩子的日記。上面有一些關(guān)于感情的話語,朦朦朧朧地使他感到新鮮。他的呼吸有些急促起來,他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心里忽然強烈地涌來一種想讀下去的愿望。
他說后來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他把那兩個小本子很快塞進了衣服里,然后從窗戶上跳出了那間辦公室,一口氣跑回了家。
在那夜里他讀完了這個不相識的女孩的日記。那個少年很久沒有睡著,他只覺得有一行清涼的淚珠,從他臉上莫名其妙地淌下來。
他說他甚至有些震驚。在那以前的日子,除了“革命日記”,他從不知道還有人竟然這樣寫日記。那樣娓娓地、悄悄地訴說著自己的心事,像是在對世界上一個最知心的朋友說話。
他忽然勇敢地決定,他將要永遠保存這兩本日記。
他從此記住了那個女孩的名字。
直到1980年,有一天他在圖書館閱報時,忽然覓見了那個熟悉的名字。
那個名字對于他來說,實在是太熟稔了。許多年中,他一直以為那是他獨一無二的珍藏,是一個屬于他自己的秘密。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他在11年后再度發(fā)現(xiàn)她的時候,這個名字已是一個隨隨便便就會在報紙雜志上露面的作家。
然而在他看來,作為作家的她,對于他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意義。這個名字已不再屬于他獨有。但他仍然十分守信地將那兩本日記,很快托人帶來了北京。
那年春節(jié)我和過大江終于在杭州見面。
他和我想象中的那個孱弱內(nèi)向的少年,似乎有很大的差別。他已是一個高高個子、結(jié)結(jié)實實、有著寬大的身架、嗓音洪亮的年輕人。惟有那一雙微笑而溫和的眼睛,輕輕松松地洋溢著善良和誠實,眸中折射出點點純凈的閃亮恰是在我心中無數(shù)次勾勒過、確信過的,一點沒錯。只有這樣的眼睛,才會看透和珍惜我日記中的那份真誠。
后來的許多年,日子就這樣在沒有日記的匆匆忙忙中,一天天流逝。過大江從大學畢業(yè),先是在一所中學當英語教師,后又去了一家外貿(mào)公司。我許多次回杭州,他似乎忙得連見我一面的時間都沒有。所有關(guān)于過大江下海經(jīng)商的消息,都曾使我十分迷惑不解。至少同我心中,那個有一雙溫和善良的眼睛,迷醉于純情和真誠的過大江,相去甚遠。長長的25年,一個人的半生,時間足以改變一切。包括當年的那個小男孩。一個美麗的春天,我偶過杭州小住,總算用呼機將過大江找到,相約在湖堤散步。由于那無法忘記的日記,我希望解開自己心里的疑惑。
我們已在湖堤走了好一會兒,我覺得有些累了。我的眼睛一次次望著那張綠椅,真希望能在那兒坐一小會兒。可惜,那張椅子上有一個人,一個穿著藍色工作服的女人。過大江說那是個園林清潔工人,看樣子她正在這里休息,坐一會兒就會離開的。
我們在她不遠的身后等了一會兒,她沒有察覺,似乎沒有走的意思。
我看了看表,我的時間不多。過大江也看了看表,他的時間也許更少。
后來過大江就朝那張椅子走過去。他很快地從衣袋里摸出了10元錢,微笑著遞給那個女人。他似乎說對不起給你添麻煩了你能讓我們坐一下嗎?
那個女工受驚一般地站起來,推開他的手,連連搖頭。她說我不要你們錢你們坐吧我該走了我該去干活了……
她以極快的速度離開了那張長椅,消失在樹叢中。
她不是傻,不是。大江用肯定的口氣說,眼睛像湖水幽幽眨動。所以我還是認為,世界上的人,不會個個都是那么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我還是相信這個地球上,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我們活著。你說呢?
我無言地望著他,忽然想起大江如今已是不惑之年的人了,略略顯得疲倦的面孔,比我十幾年前第一次見他,顯然已經(jīng)成熟許多。惟有那雙微笑的眼睛,卻依然清澈、明凈如初。
我似已沒有必要對大江說出我的疑惑。分手時我們都很輕松。
我永遠不會再寫日記了。所以我只能將這個真實的故事,做以上的筆錄。
(鄧偉明摘自《北京文學》圖/亓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