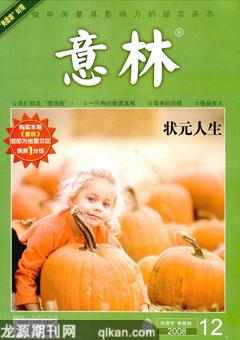我們怎樣生,我們怎樣死
三 井
若干年前,我做過一個“無聊”的測試題,題目是:面對你的死亡。問題包括:你第一次親眼見到的死人是誰?你最厭惡自己死亡的哪一面?死亡對你意味著什么?倘若人們告訴你,你已病入膏肓,大限將至,你會怎樣安度時日,直至死去?倘若你已結婚,你想比你的配偶活得更久嗎?倘若你有選擇余地,你會喜歡哪一種死亡?倘若你有選擇余地,你會何時去死?你愿意為誰或為什么而獻出自己的生命?在備選答案中選擇完畢后,我忽然發現,整個測試題竟然沒有任何結果。
直到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我才明白了這個測試的答案——真的就像題目那樣簡單:面對你的死亡。那一天,我在書架上看到了《生命的肖像》。它記錄了一些人的生與死,他們中有科學家、作家、銀行家、醫生,甚至還有幾歲的孩子和剛出生不久的嬰兒。
不管他們的身份、地位和年齡有何差異,攝影師對他們的記錄大多是兩張黑白照片:一張記錄他們活著時的狀態,另外一張則是他們死亡后的表情以及一段不長的文字,那是根據他們生前在臨終關懷醫院的采訪記錄整理下來的故事。
封面和封底是其中的一位主人公——一個1歲多的小女孩。在有關她不到5頁的文字中,我們能看到的只是一個母親的痛苦與不舍。在此之前孩子的知覺已經幾乎沒有了,大部分是在靠藥物維系著生命。盡管在母親看來她走得并不平靜,但是在那張記錄孩子死亡后表情的照片上,一點兒也看不到痛楚。
文章的標題是:“至少她來過這個世界。”我倒更相信攝影師瓦爾特觀察中得來的經驗:“新生嬰兒的臉上表情都很恐怖,而人在死亡前后的臉上表情卻很安詳。”記起劉小楓在《沉重的肉身》里對“I am born”的解釋——英文是被動態,直譯成中文是“我被出生了”。我的生命起點不在我自己的手里,不是由我決定的。
不過,我并不認為攝影師的經驗適用于所有人。你會發現,書中記錄的人物的臉上,有不甘心、平靜、滿懷希望,也有絕望、放棄、哭泣、害怕,還有深深的哀傷。
曹女士是瓦爾特采訪的一個病人。她住進臨終關懷醫院前,已經大約10年沒有出過家門了,但她表現得一直非常樂觀。她常常笑,很少抱怨,她很有耐心,態度泰然自若。因為她已經不止一次地面對過死亡了,她保證說,她不害怕死亡。每天她都會做冥想,她希望在自己的最后一秒鐘舍棄一切牽掛。然而,到最后,她還是被某種緊張和不安控制住了。
曹女士是帶著怎樣的心態走進另一個世界的?她的女兒回答說:“人在面臨死亡時,他的一部分會很高興,他的另一部分會充滿恐懼。”我想這恐怕才是常態。
讀過書中故事,不難得出一個結論:之前有過更多留戀更多恐懼、做過更多掙扎與奮斗的人,走的時候反倒平靜。
湯姆·彼得斯在他60歲的時候說,他不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刻下這樣的文字:“他本來可以成就一些非凡的業績,但他的老板卻不讓他那樣做。”他希望生命能夠再延續幾年,他希望墓碑上的文字是:“他曾經是一個‘玩家”。
而對死亡與生活,我還沒有認真想過。
“我把每個睡醒后的早晨都當成一件禮物,因為這表示還有一天可以工作。”貝聿銘的這句話總嫌矯情。還是喬布斯更本色。他說,他每天早晨都要對著鏡子問自己:“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還愿意做我今天原本應該做的事情嗎?”當一連好多天答案都是否定的時候,他就知道做出改變的時刻到了。
(塵中塑摘自《職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