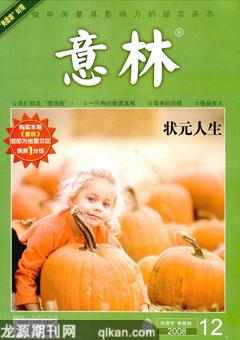極品女人
張 放
她名叫南希·古諾,英國人,航運富豪家中的千金小姐。1965年,她活了69歲之后離開了這個世界。
有傳記作家將她的一生寫成書,最近在美國出版。她的一生充滿著浪漫色彩和傳奇經歷。最主要的是,她對文學詩歌非常喜愛,人又長得非常漂亮,她的愛情生活中的眾多男主人公的名字,都是世界級的文學大師,這使得這本新出版的書變得精彩好看。
法國人有條諺語:告訴我你與什么人交往,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南希小姐交往圈中的人物,則絕對是文學女青年最夢寐以求的了:世界級著名詩人T·S·艾略特、諾獎得主塞繆·貝克特、諾獎得主巴西詩人聶魯達。
艾略特所寫的經典詩品《荒原》中女主人公的原型就是這位南希小姐。聶魯達則稱贊她有一雙藍天般清澈的眼睛。塞繆·貝克特對她的“勇氣與魄力”給予了高度評價。三位諾獎得主都與這位魅力四射的南希小姐擦出了愛情火花。此外,還有一些重量級的人物也與這位美麗的小姐有過不尋常的關系:A·赫胥黎、達達派藝術家T·查拉、詩人E·龐德、詩人L·阿拉貢等等。她曾跟我們非常熟悉的E·海明威打過網球,接過著名意識流文學作品大師詹姆斯·喬依斯的私人電話。她還給著名畫家布朗庫西做過模特兒。美國黑人作家藍·休斯曾這樣描述她:她是這個世界上“我最鐘愛的人兒”。美國詩人W·C·威廉姆斯在書房中一直懸掛著她的畫像,并稱她為“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現象”。
從上面的情形看,我們完全可以下這樣的論斷:她是20世紀最受寵愛的繆斯。只是在她死后近30年,才有人出版關于她一生的書。書中說,她的本意是更希望人們更把她看做一個詩人、出版商和記者。如果把她看為是對底層民眾最大的精神支持者,則是她更感快活的一件事情。書中這樣轉述了她說過的一句話:“我總覺得,人活這一輩子,總能做點兒有益的事情出來。”
她出生于一個英國伯爵家庭,之后來到美國,成為一名社會精英。她回憶自己小時候的時光時,覺得家里的生活氛圍與紐約公共圖書館里的情形差不多。她小時候并不開心,父親整天出去狩獵、釣魚、騎馬。母親則對文化與社會進步充滿巨大興趣,對當時文化界的領軍人物都能做到如數家珍般的熟悉。由于母親瘋狂地喜歡與這些社會名流進行社交,以致出現了幾次婚外情。但令南希感到不解的是,父親竟然默默地接受了母親有婚外情的事實。由于對父母親的“模糊不清的道德觀”感到巨大失望,后來南希對父母和他們那個階層的人們做出的一切,都持一種蔑視的態度。
歷史進程成全了她的這種叛逆精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她與眾多青年人一樣,進入了一個“蔑視父母與社會設定的各種繁文縟節的時代”,進入了一個“藝術與性的試驗時代”。她將眾多的藝術家變成了自己的浪漫生活的每個篇章。這時,她遇到了詩人龐德、艾略特、劉易斯,當時他們正在英國進行著“文學革命”運動。用南希的話說,這場運動“徹底改變了我的整個人生觀”,她更加相信:“藝術的神圣使命就是改變歷史進程。”
1916年,她突然決定嫁給一位一戰受傷的退伍軍人,但沒過半年,倆人即分開了。1921年,她與龐德展開了五年的愛情生活。沒多久,又使艾略特臣服于她的石榴裙下。她對男人們取得成功感到不服,盡管艾略特用尖酸刻薄的字眼把她和其他女人的“智慧”一起加以諷刺,但她還是出版了自己寫的三本詩集。有評論家說,她寫的《視覺差》一詩,完全可以與艾略特的《荒原》“平起平坐”。當然,這樣說有些過于樂觀,不過總體說來,她的詩句寫得還是不錯的。
正因為她出版了自己的詩集,也使得她與“遠離塵世的一群人”走得更近了些。她與先鋒派的人們有了更進一步的聯系。這時,她遇到了海明威和詩人威廉姆斯,也參與到了達達派和超現實主義派的各種活動之中。這些人都與她一樣,堅信藝術的使命就是改變歷史的進程,并認為自己承擔著揭露統治階層的虛幻夢想與空洞價值的責任。
1934年,她發現自己愛上了一個非洲裔美國鋼琴爵士演奏家。正是這個黑人使她看到當時社會對黑人的嚴重歧視。于是,她出版了近900頁的關于黑人歷史的書,并呼吁譴責種族歧視。這引起很多著名人物的注意,有多達200位名人參與進來,其中有著名作家T·德萊塞等。但這也給她帶來很多麻煩:白人的憤怒譴責和撻伐。
可她一點也不懼怕,更沒有屈服的意思。進入30年代,她開始將炮火集中于法西斯主義。她公開譴責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亞,譴責西班牙弗朗哥政權。
此外,她還自己建立救難所,為近4000人提供食物。
二戰爆發后不久,她已經變得不名一文,慘不忍睹。但她仍然堅持說:“我本來就應該什么都沒有。”
她的這種無私行為,隨著年齡的增長,變得有些過火了。書中有一段描述她情形的話:“一天晚上,只見她喝得醉醺醺地從一家咖啡館里出來,兩個鼻孔里各插著一根煙……”從這樣的話中,也可以看出來,她已經有點破罐破摔了。1960年的一天,她被確診瘋了,被送進了瘋人院。后來又被放了出來。但她一直連續五年天天喝醉,什么也不吃地活著。1965年,她過完69歲生日,又跑到一家咖啡館喝酒,但此時的她已經形容枯槁。有朋友說,當時她好像完全瘋了。幾小時后,警察在一條街上發現了她,她已經完全喪失了意識。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兩天后,她離開了人世。
聶魯達得知這一消息后,不無傷感地說:“她的身體在與不公平抗爭的戰斗中消失了,給她的回報,則是顯得越來越孤獨的生命形式,她得到的最后結果,就是連上帝都遺棄了的死亡。”其實,她對自己也有一個評價:“我將留給這個世界的,是一種憤怒的情緒。”
(石景瓊摘自《海外文摘》2007年第8期 圖/孫勝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