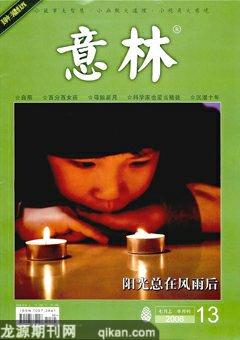私奔
張悅然
小時候,我的夢想是,在長大之前,可以找到一個可心的男子,和他一起私奔一場。從知道這個詞開始,就覺得它非常美妙。“私”的隱秘,和“奔”的狂野,是這樣沖撞的交合。
記不清在多少篇小說中,曾寫到過私奔的情景。寫過那么多次,寫得那么縱情。是因為直至長大,我都未能私奔一次。
我的中學。就是我在小說中曾描述過的,那個在哥特式教堂的對面,隔街就是一座大學的老校園,那是我們的樂園。傍晚時我們走到學生宿舍盡頭的白樺樹林,看到大學里的男生和女生,坐在殘缺的石頭椅子上。面對一條骯臟的小河。擁抱和接吻。他們的愛情感動了我,可是我的疑惑是:他們為什么要留在這里,他們為什么不私奔呢?
在每周上交的作文本的最后幾頁,我開始偷偷地寫私奔的故事。就在這座沉悶的校園里,周一升完國旗,英俊的升旗手和美麗的護旗手,白手套都沒有來得及摘,背起裝滿衣服和食物的書包,就上路了。雖然故事寫得很凌亂、隨性,但潛意識里,是希望那位優雅的語文老師可以看到,并且賞識。可她非常粗心,一直沒有發現。
初二念完,我和女伴靚靚坐火車去海邊。我們并排躺在旅館里煞白的床單上,睜著疲倦的眼睛,不肯睡去。這一場遠途春游。因為瞞著父母,騙了一點錢,事先做過充分的謀劃而變得刺激起來,簡直被視作一場偉大的私奔了。我們相約等到高中畢業的時候,要和兩個男生再私奔一次,去很遠的地方。那時候,我們都不懂得愛情,以為那是一種和自由、流浪、揮霍無度緊密相連的神奇能量,所以必須私奔。私奔是這種能量的爆發形式,惟一的,必需的。
初三的寒假,我和臨班的男生坐在白樺樹林,面對結冰的小河親吻。我希望可以吻得久一點,直至被經過的老師抓住。我們將受到懲罰,被驅逐,最后只有私奔。我向男生說了對私奔的向往,他的眼神里掠過一絲恐懼,很快用一種成人的口吻說:事情沒有你想象得那么簡單,要做很多準備。我想也沒想就說:那么就開始準備吧。
這場戀愛,是以準備一場私奔為繼續的。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去哪里,背包里要裝什么,穿什么樣的衣服。還設想了路途中會遇到一些什么樣的困難。買了地圖、指南針,他有一只容積可觀的登山包,到時可以派上用場。我們還特意去了一次火車站看列車時刻表。
沒有具體的目的地。只是打算去南方。沒有確定的出發時間,一拖再拖,直至初中生活結束。我們安靜地分開。最后一次見面,私奔的事只字未提。可是不提這件事,兩人幾乎是沒有話題的。面對面干坐,希望這個下午快點過去。放在書包前層口袋里的指南針,原本是打算還給他的,也沒有拿出來。
畢業后不久,我們的校長和副校長就私奔了。校長四十三歲。是非常好勝、專制的男子。副校長,那個已經四十六歲的女人,美麗優雅,但神情恍惚,上課的時候總是不斷地扶眼鏡。他們雙雙辭去工作,棄下伴侶和孩子。離開了這座城市。有與他們相熟的人,曾收到過寄自浙江某個小鎮的包裹,上好的茶葉和清潔飽滿的無花果干。據說是在鎮上的中學教書。這是發生在那年夏天里。最振奮人心的事。我許多次回到學校,校長再也不會昂胸站在門口,過問植物的長勢,檢查學生是否都穿了校服。學生們也不會再看到那個女人,穿開司米開襟毛衣和印著大花的漂亮裙子,抱著語文課本及教案,從二樓緩緩走下來。但這里到處充斥著他們的氣息,抑或是一種因為缺了他們而顯露出來的荒涼氣息。總之,他們和這里有關,這里是他們一段旅途的起點。我迷上了他們的愛情故事,雖然永遠也無法知道更多。
次年春天。曾在學校對面的大學校園里,看到過校長非常寵愛的獨生子。他比我們高兩個年級,很英俊。與另外兩個男孩打籃球,累了,就靠在一邊的圍欄上休息。他看起來那么憂郁。非常與眾不同。不知道為什么,我忽然覺得,他也許并不記恨父親,相反地,他非常喜歡這個私奔的故事。這種強烈的直覺,幾乎令我想要走上去和他說話。
(魯東平摘自《人民文學》2008年第2期圖/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