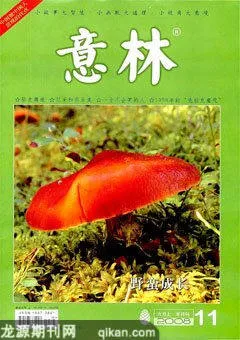文學是要講緣分的
二月河
我的父親沒有上過中學,他的學歷是初小。但父親告訴我,在他小學那幾年,從來沒人和他爭第一。
他說這話的意思,就是想讓我也弄個“第一”。但事實上,我上小學、初中乃至高中,我都是班里的“底線”。混得好些時,是個中等,一般情況下,總是個坐紅板凳的主兒。小學6年,我留級一年,初中、高中更慚愧,又各留一次。一共足足上了15年才讀完高中。我不曉得上大學有“留級”這一說沒有。我那樣的“臭”,自然是考不上的。倘若考上了,估計還得“留”。
我這人浮躁。沒有耐性,不喜瑣碎的邏輯推理,不愛刻意地背公式,遇到“沒意思”的東西死活鉆不進去。比如說外語,我原在一個學校讀的是俄語,轉了一個學校又學英語,俄語學得還有點興味,到英語就不行了。我們家好像對外語有天然的排異反應,一提ABCD就蒙了,我弟弟、妹妹們外語都不行,但他們比我有坐性,似乎好點。
數學很枯燥。每轉一次學,都是不一樣的進度,聽不懂,不想聽。坐在那里,茫然盯著窗外,老師的話都變得很遙遠,老師的面孔都變成一塊模糊不清的白板,嘴一張一合不知他在念叨些什么。偶爾,一個粉筆頭砸過來,打在我臉上,我會被砸得一愣,那是老師砸過來的。我轉過不計其數的學校,老師砸粉筆頭的水平都極佳,大致都在耳朵旁邊。絕對打不到眼睛。我在多少年后寫小說涉及武林好漢打鏢水平時,常常想到老師這一招,天下老師練起武來,恐怕都是高手吧。
理化的情況稍好一點,不似外語那樣全靠硬背,也不像數學那樣一步跟不上,一學期都追不上了,倘仔細看看課本,能搞個差不離,考個及格。
數理化都不景氣,這就是我的中學寫照。然而我有強項——語文,作文無論轉到哪個學校都是出色的。
語文老師沒有不賞識我的,不但不砸粉筆頭,且常常當堂誦讀我的作文,或在學校的黑板報上刊登。
我缺乏死記硬背的能力,但好文章,到手基本過目不忘。我的嫂嫂曾把毛主席的《反對自由主義》拿來,我看了一遍就還給她。她問:“難道不好嗎?”(那時《毛選》尚未在社會上發行)我即開始背誦,從頭到尾一字不差。《愚公移山》不但毛選上的章節全背,原文也能背得滾瓜爛熟,看兩遍就行了,不需要第三遍,第一遍“大致”,第二遍“找一找”就成,我有這個能力。
再有就是讀小說。《西游記》是小學就讀了的。不能全懂。囫圇吞棗看故事——到初中就真的讀懂了。1980年,我在《紅樓夢》學刊發表了《史湘云是祿蠹嗎》,還有《鳳凰巢與鳳還巢》,在紅學界引起了一點反響。其實文章中的基本觀點在高中時我就研究了,只是那時手中沒有脂批本資料而已。考試不許“看閑書”,但似乎所有的閑書我都愛看,什么《三俠五義》《七俠五義》《大八義》《小八義》《彭公案》《施公案》《江湖奇俠傳》,這些“不正經”的書,都讀光了,還有算命揣骨、手相這些書,是“徹底不正經”的書,也看了幾本。
就這樣讀完了高中,加上兩年學校“文革”時間,我畢業時已是23歲,這個年紀,許多人大學也差不多畢業了。我自己總結是;一塌糊涂數理化,一枝獨秀是文史。這么著說,或許對看我這篇短文的中學生是有副作用的。但是我想,我還是應該誠實說話。若有人問我:是不是像你這樣讀書就一定能在文學上有所造詣?我同樣誠實地告訴你,不見得。慢說讀這點書,就算再加十倍,再加你的閱歷、見識、胸懷,加生活條件,加……那也未必就成。文學是要講緣分的,你愛文學,還有個文學愛不愛你的問題。讀書是沒錯的,功利是另外一回事。
(鄧偉明摘自《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