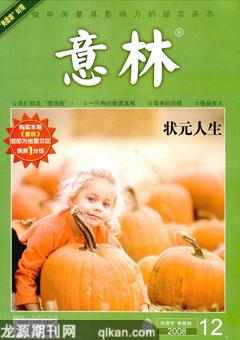無為的境界
張 鳴
曹參是漢高祖劉邦在位時僅次于蕭何的親信班子成員,蕭何死后,他馬上讓仆人為他收拾行李,說是他就要當丞相了,果然,相國的大帽子最終落在了他的頭上。可是做了丞相之后,曹參卻終日飲酒,醉時多,醒時少,百事不興,屬員有過,能遮便遮,有人看不慣,想過來提意見,便被一并拉去喝酒,喝到大家物我兩忘,意見也就沒了。最后連皇帝都看不過去,轉彎抹角表示了不滿,也被老先生用一套蕭規曹隨的鬼話蒙混過去,每日依舊沉在醉鄉里。
王導是東晉王朝的開國功臣,晉元帝能從王爺變成皇帝,多半虧了王導,登基的時候,皇帝還要拉王導坐在一起。此老也是出了名地糊涂,人家罵他“聵聵”,自己也很以聵聵自得。酒量如何不知,但下面的官員胡作非為肯定沒事。有次王導裝模作樣地派出人員出去考察,回來后大家紛紛說下面官員的不好,只有一個人一言不發,最后等大家說完了,此人才說,做宰相的理應網漏吞舟,何必管官員的好壞。王導居然夸這個人說得好,深合其意,害得大家都覺得自己不僅無趣,而且見鬼。
不過,兩個宰相的“聵聵”,結果卻不一樣。曹參得到的是好評,老百姓編出歌謠來夸,結出了“文景之治”的果。而王導,不僅老百姓不夸,而且官員也未必念他的好。東晉政治混亂、國勢微弱,中原涂炭卻恢復無望,當時人罵他“聵聵”,后來人依舊罵他“聵聵”。
曹參的時代,承秦末大亂,人口減半,六國貴族豪強已經被秦剪滅殆盡,社會組織也被破壞殆盡,社會只有按自然規律,慢慢恢復元氣,國家才有指望。這時對社會恢復最大的敵人,不是別的,正是來自政府的權力。因為這個時候,只有政府是社會中惟一有組織的勢力,而且這個勢力沒有什么東西可以與之抗衡。作為政府官吏,往往有自身的強烈沖動,出來指手畫腳,為公也罷,為私也罷,一時間難說清楚。總之從長遠看,“做”未必就比“不做”更好。顯然,此時的最高行政長官,能夠做的最好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盡量抑制官吏的沖動。這一點,曹參做得很好。當然,當時的老板配合得也好,皇帝身子弱,沒主意,又好色,不當家,當家的呂后,只關心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地位,別的都馬馬虎虎可以將就。漢初尊崇黃老,據說是膠西蓋公的主意。曹參做丞相前,請教了本地的儒生,結果沒有一個人說得合他的意,只有蓋公的清靜無為,才真正打動了他。當然,也只有這個主意,才合乎時代的需要,后來很得史家稱道的“文景之治”,恰是曹參開的頭。事實證明,合乎時代需要的,最難的恰是不作為,因為讓古今中外的政府官吏盡量少作為、不生事,的確太難了。
王導之世,門閥豪族勢力已成,而且斷送了西晉江山。社會對新王朝的呼喚,是抑制門閥豪強、恢復中原、改變政府由門閥勢族壟斷的局面。然而,王導卻模棱兩可,在南渡的中原門閥和江南豪族之間搞平衡,放縱門閥豪族把持政權,胡作非為,從而換取他們的支持。王導處在一個本該抑制政府官吏的時候,但他恰恰不抑制,反而更加放縱。僅僅由于進入中原的各個游牧民族之間的爭斗,以及中原漢人對本族王朝的依戀,才使得偏安的小朝廷得以茍延殘喘。這樣的丞相,這樣的“聵聵”,當然沒法得分。
對于政府而言,無為是種境界,在這種境界里,民間社會可以自然地生長,實現自己的均衡發展,但是,只有在抑制了官吏的權力沖動的情況下,無為才有可能。
(吳清貴摘自《中華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