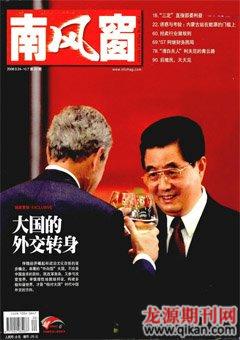“拉拉扯扯”的中歐關系
熊 煒
近來中歐關系出現了一系列不和諧因素,先是德國總理默克爾推行“價值觀外交”對中德關系產生劇烈沖擊,繼而歐州國家又對蘇丹、緬甸等問題上的“中國責任”持續關切,甚至少數歐洲政客還曾公開鼓吹抵制北京奧運會。
有觀察家認為,上述現象不僅是中歐關系中深層次矛盾累積后的爆發,也預示著中國一貫以經濟利益驅動政治關系發展的對歐外交策略遭遇困難。鑒于今年10月北京將主持召開亞歐會議(ASEM),有必要先對中歐關系的癥結進行一次初步的診療,俾使國人更好地理解這種挑戰。
中歐關系的“競爭性”
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與歐洲特別是西歐的關系經歷了1980年代的逐漸升溫,1989~1994年間的起伏發展后,從1990年代中期起進入了快速穩步發展的階段。自1995年以來,歐盟連續發布了6份對華政策文件,明確提出要使用政治、經濟等多方面資源加強與中國的合作,而中國也于2003年10月發布了新中國外交史上的第一份對歐政策文件,系統闡明了中國的對歐政策,表明了密切發展雙邊關系的良好愿望。

由于各方面機緣巧合,中歐關系在這不到10年內連續上了3個臺階:1998年構建面向21世紀的長期穩定的“ 建設性伙伴關系”,2001年確立“全面伙伴關系”,2003年達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之后的2004年,還被稱作是中國的“歐洲年”,中歐雙方領導人互訪創下歷史記錄,中方有6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兩位副總理訪問了包括新成員國在內的16個歐盟國家和歐盟總部,歐盟國家和歐盟機構共9位領導人相繼訪華。
但從2005年下半年開始,歐洲國家開始流行“中國威脅論”,歐盟對華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增強,越來越多的歐洲戰略人士開始探討中國崛起對歐盟的挑戰問題。2006年10月,歐盟委員會發表了第六個對華政策文件《歐盟-中國:更緊密的伙伴,擴大的責任》;同年12月,歐洲理事會發布《關于歐盟-中國戰略伙伴關系的結論》,顯示歐盟針對中國崛起調整了對華政策。它雖然保持了要同中國發展“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基調,但是強調歐盟對華經貿關系定位已經由“成熟的伙伴”轉為“競爭與合作伙伴關系”。
伴隨著雙邊貿易額的大幅增長,中歐經貿關系也進入問題多發期,貿易逆差、知識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和產品安全等各個領域的摩擦此起彼伏。歐盟對中國的要價也越來越高,2006年秋,歐盟委員會貿易委員曼德爾森直白地說:“中國的經濟增長使得人們對它在商業誠信和公平競爭方面的期望值越來越高。”由于雙邊經貿關系中的這類矛盾具有長期性,盡管中歐都強調通過務實合作的方式來協調,但解決這些問題并非易事。
在政治關系上,隨著希拉克、施羅德等對華友好的領導人相繼離職,中歐政治家之間的信任感大大降低,中歐關系的整體氣氛趨于冷淡。以默克爾會見達賴喇嘛為開端,歐盟國家對華政策開始出現借人權、宗教等問題向中國施壓的傾向。歐盟對華外交不僅加強了其內部的協調,而且采取了“議題聯系”的策略對中國進行牽制,放大了中歐關系中的競爭性、復雜性和長期性因素。在某種程度上,中歐關系已經進入“拉扯期”。
“戰略伙伴”定位仍模糊
1998年,歐盟提出要和中國建立建設性伙伴關系,因為它認識到“中國國內進行了持續的、巨大的經濟社會改革。在國際舞臺上,中國已成為國際安全和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要將中歐關系提高到與歐美關系、歐俄關系同等的地位”。5年后,中歐終于達成“戰略伙伴關系”共識。雖然溫家寶總理指出,所謂“戰略”是指雙方的合作具有長期性、全局性和穩定性,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差異,不受一時一事的干擾,但是雙方并沒有解釋具體什么樣的關系才是“戰略伙伴關系”。所以,有人認為這種“戰略伙伴關系”只是外交上的一種善意姿態,并無真正的戰略涵義。也有學者指出,中歐戰略伙伴關系的實質是一種介于“對手”和“朋友”之間的結構,具有安全上的非對抗性、合作與摩擦并存等特征。
近兩三年來,中歐雙方都對所謂的“戰略伙伴關系”面露失望。對中方來說,歐盟對華武器禁運和市場經濟地位(M ES)問題遲遲不能解決,使得歐盟作為戰略伙伴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歐盟則認為中國的非洲政策缺少與歐盟的協調,打亂了歐盟的非洲政策。這些分歧表明,中歐“戰略伙伴關系”缺乏足夠的支撐與動力。事實上,盡管雙方領導人一直強調要在全球政治層面加強溝通,但是中歐關系的主動力還是經貿合作;由于歐盟內部意見分歧以及中歐雙方都力圖避免招惹美國,中國和歐盟在全球政治與安全領域的合作一直流于形式。因此,經貿關系中日漸增多的競爭性因素不僅殃及雙邊經貿,也給雙方的政治合作投下陰影。
觀察家們普遍認為,在中歐“戰略伙伴關系”歷經5年風雨后,如果這一機制在中國成功舉辦奧運后還不能煥發活力,那么雙邊關系的未來走勢堪憂。考慮到中國正從傳統的政治大國轉變為經濟大國,而歐盟則希望上升為政治上的“全球行為體”,筆者同意歐洲問題專家馮仲平先生的論述,即中歐雙方亟須借當前談判“中歐新型合作伙伴關系協定”之機明確“戰略伙伴關系”的內涵,且應強化這一關系的兩大支柱:貿易戰略伙伴+全球負責任伙伴。
拋開能源和環保等領域的全球性挑戰不談,即便在全球政治層面上,歐盟也能與中國找到共同的敵人,例如貧困、武器擴散和侵略性戰爭。何況中歐在倡導多邊主義、推動建立以國際法為基礎、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方面有著近似的立場;中國所倡導的“和諧世界”理念,也能通過歐盟在全球建立良政規則的行動得到實現。所以說,在當前新冷戰陰霾籠罩歐洲的形勢下,雙方領導人應該抓住機會,把中歐“戰略伙伴關系”落到實處。
歐盟是個復雜的伙伴
與歐盟打交道是件麻煩的事,因為歐盟對外表現出不同的層面。根據歐盟條約的規定,歐盟對外關系分為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其中對外貿易、對外發展援助政策和對外環境政策等屬于第一支柱,這方面歐盟委員會等共同體機構具有很大的決策權,歐盟的決策也采取特定多數表決制;而外交和安全政策是第二支柱內容,各成員國政府在理論上都還享有否決權。歐盟決策機制的特性可以概括為“行為體的多樣性”和“層次的復合性”相結合,歐盟對外政策是在多種行為體于多個層面進行跨國、跨政府和國際間互動的模式下“綜合”出來的。
因此,中歐關系也不僅僅是中國同歐盟機構之間的雙邊關系,也并非中國同歐盟成員國之間關系的簡單相加,而是雙邊和多邊交錯的網狀結構關系。這種特性既導致歐盟對華政策在某些方面缺乏實質性內容和可操作性,同時也給中國對歐外交帶來相當大的困惑。例如,中國希望歐洲一體化進程平穩發展,因為真正具有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歐洲將是一個更加清晰的伙伴。但是,當前歐盟自身的發展困難卻使得它越來越難于打交道。某種程度上,毛澤東在1970年代評價西歐的話仍然適合今天的歐盟,那就是歐洲“太弱、太散、太怕打仗”。
傳統上,德、法等國一向被認為是歐洲一體化的發動機,然而在全球化壓力之下,歐陸流行的社會經濟模式遭遇重大挑戰,伴隨著歐盟擴大為27個成員國,德法等國對歐盟決策的影響力明顯下降;中小國家在歐盟內部形成新的不同組合,對歐盟對外政策的影響力有所上升,而這對中國傳統上注重歐盟大國的對歐外交策略構成一定挑戰。此外,老牌歐盟大國經濟不振還影響到公共輿論的涉華態度。當前,在歐盟中下層民眾中,很多人認為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他們的利益則在受損,這些偏見的匯集就是“中國威脅論”流行的土壤。
歐盟擴大的另一重后果就是美國對歐盟的影響力由此增大了。在1990年代,由于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西方國家失去了主要對手,德、法等國在安全上對美國的依賴性減弱,歐盟具有了在全球政治層面發揮自主影響力的機會。然而近幾年來,由于新入盟的中東歐國家普遍親美,比如波蘭領導人就曾稱波蘭是美在歐的“特洛伊木馬”,美國乃得以推進在東歐的反導計劃。再加上俄國不時向歐洲揮舞能源大棒和炫耀武力的緣故,東歐國家普遍將安全寄托于美國所主導的北約,歐盟也不得不默許北約不斷東擴。這樣,中歐關系中的美國因素非但沒有削弱反而更強了,甚至可以認為,在中歐外交談判桌旁,總是可以看到美國的影子。
由于歐盟的復雜性以及歐盟傳統大國內政外交的局限性,中國對歐外交應加強間接戰略,以迂回方式取得更大效果。譬如,可大力加強針對歐洲民眾的公共外交工作,在人權、環保、能源等歐洲人關心的全球性議題上贏得歐洲民眾的尊重;在世界政治層面上,通過外交努力展現中國在全球性問題的解決和維持歐亞大陸戰略平衡方面都起著關鍵性作用;最后,不把希望僅寄托在“大國主宰”上,而同時加強針對中、小國家特別是東歐國家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