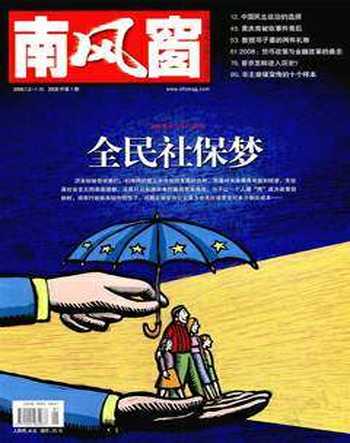誰玩轉了土地“魔方”?
黃赤青
土地資源是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最重要的、有限的戰略資源。當前,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迅速發展,用地需求與土地供給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耕地總量逐年減少。近幾年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嚴格保護耕地、從嚴管理土地的政策措施。如前些年叫停了高爾夫球場的建設用地,去年5月又規定對別墅項目的土地申請停止審批。這些措施無疑是符合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和子孫后代的長遠利益的。
上世紀90年代,在對外開放、招商引資的熱潮中,各地競相仿效,興起了一股建設“開發區”熱,各級政府畫地為牢,財政出錢搞三通一平,“筑巢引風”,吸引外來投資,結果是不少地方的開發區“養在深閨人未識”,造成大量土地閑置。
時下,與過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火爆的樓市、股市,無不與土地有關,迅速攀升的房地產價格的背后,是日益膨脹的固定資產投資需求造成的可供利用土地資源的緊缺和土地升值的巨大空間。

誰掌握了土地資源尤其是優良的土地資源,誰就掌握了經濟發展的主動權、獲利權。土地在成為政府財政“聚寶盆”的同時,也變成了房地產開發商的“搖錢樹”。于是,一場爭奪土地資源和開發權的競爭由此展開。
在這種形勢下,政府及有關部門管好用好土地的責任就越來越重。然而遺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地追求GDP數字的增長,熱衷于搞“面子工程”,在引進大項目、大品牌,資源“有水快流”的思想驅動下,不惜犧牲生態環境和公共利益,用土地換投資,只要對方肯來投資,土地可以賤賣甚至白送,契稅可以減免。
個別政府部門與房地產商結成利益共同體,在土地使用權出讓過程中違背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名為“招拍掛”,實為暗箱操作。如事先內定拍賣競得者,向投標方泄露出讓底價,更有甚者,與投資方私下商定土地出讓價,以保證對方獲得最大利益。有的地方違反用地和審批程序的法規,祭起“變通”的法寶,國家不準建別墅,有人就搞產權式酒店出售;法律規定征收土地超過多少畝要報國務院批,有人就化整為零或用限額接近數申報來規避;土地應先批后用,有人就默許邊批邊用。有的部門放棄土地監管職責,土地一賣了之,對開發商土地開發的期數、規模和竣工期限等均不作任何約束,悉聽尊便。
可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在政府仍然充當土地資源配置的主體和地方投資活動組織者角色的情況下,它的管理職能行使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市場機制作用能否有效正常發揮,直接關系到國家土地調控政策能否落實并實現土地資源配置的科學化、集約化和效益最大化。
如果說我國實行市場經濟之初,遍地開花的經濟開發區是當地政府直接運用行政手段進行土地儲備的產物,那么在國家建設可用土地越來越少的今天,一些大的房地產商表面上憑借實力獲得發展,實地里則是利用行政權力之手在大量圈地。
2007年4月才在香港掛牌上市的碧桂園公司,到8月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就新增土地儲備3500萬平方米,共圈地4500萬平米,成為目前中國房地產業最大的地主之一。持有碧桂園七成股份的楊惠妍,10月以個人160億美元的凈資產,一躍登上福布斯亞洲版2007年中國(內地)富豪榜首。
低成本、大規模的圈地運動造就了一代新富豪,可謂“點地成金”。土地——資本(市值)——土地形成的資金增值循環流,讓房地產大鱷們的財富如滾雪球般迅速變大。有限的土地資源大量聚集在少數地產商手中被用于商業開發,加劇了土地市場供求關系趨緊和供地結構失衡的矛盾,造成公共建設用地和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用地的緊張,同時推動了商品房價格的急劇惡性上漲,并形成房價壟斷的趨勢。難怪近年來樓市開盤越多,房價反而越貴。
目前,印度農民人數已超過中國。這一消息令人欣喜之余,又不免產生憂慮。因為隨著我國城鎮化的推進,農村土地大量征用,失地農民已達4000多萬,他們因失去土地可以失去“農民”的身份,但這些失去了生產資料又缺乏知識技術的農村人口成為了新的弱勢群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涌進大中城市謀生,就業、居住、生活等問題都需要解決,給城市容納帶來很大壓力。政府應提供和保障土地供應以建設更多的廉租房、經濟適用房,滿足農民工和其他低收入階層的基本居住條件。因此,農民數量的減少,城市人口的增加又帶來新的社會問題,加大了對城市土地供應的需求。
現在是到了警惕新的“圈地運動”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