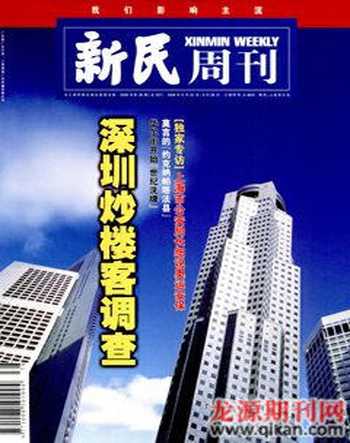樓市炒客眾生相
楊 江

“斷供潮”至少短期內在深圳不會出現,但在斷供邊緣的人卻不是一個小數目。
一年前,深圳樓市炒客云集,有說法70%的購房者都是炒客,在這個偌大的炒盤中,各色炒家、開發商、營銷機構、中介,還有那些身披多重外衣的“網絡劍客”以及若隱若現的銀行,各自承擔著自己的角色,推動著炒盤瘋狂地運轉,門檻之低,以至連掃馬路的清潔工只要愿意都可以炒上一把。
上帝欲讓其滅亡,必先讓其瘋狂,深圳的教訓讓人們明白了沒有只贏不輸的賭局。而當泡沫驟然破裂時,眾生開始現形。
全身而退的炒房“大鱷”
57歲的溫州商人張素芹愜意地躺在真皮沙發上,神色飛舞:“我們溫州人做生意天生有頭腦,很敏銳,炒房也是,不會虧的。”這是深圳市華強北,全國最大的電子批發市場,張素芹是一個在圈子內很有名的炒房“大姐大”。
要走進炒房客尤其是溫州炒房團的圈子,讓他們拂去面紗、接受采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長期以來,他們就是一個飽受爭議的神秘人群。2007年,記者在深圳調查樓市時,一位同樣在華強北做電子生意的溫州炒房團小角色向《新民周刊》透露了張素芹這位炒房“大鱷”。
小角色說,僅以她對張素芹脾性的了解,“張姐一出手就是大手筆,一買就是幾十套房子。”但當時的深圳,對炒客的罵聲一片,張素芹婉拒了記者的采訪要求。因為有了上次的交道,一年后,當記者再次提出采訪要求時,張素芹欣然答應。
這位炒房“大鱷”現在是華強北某電子城的老板,擁有多達5個樓面的商鋪。“我去年7月就把手上的房子拋出去了,那正是深圳房價炒到的最高點。”張素芹很豪邁地一笑,“那時候爭議也到了頂點,做生意,頭腦不能發熱,漲瘋了,肯定要出事的。”
張素芹說,多年的經商經驗告訴她,該下手時就下手,但是絕對不能貪心,要見好就收。“我拋售的時候,還有人不解,勸我再等等,說還會漲。我心想,都炒成這樣了,連我都不敢再接盤了,還能炒到什么程度?你看,現在他們都被套牢了。”
張素芹炒房已經炒了5年,征戰上海、溫州、杭州、深圳多地,“2003年,我在你們上海的康橋花城,一下子買了50套別墅,那時候多便宜啊,不到6000元的單價。”
那是她覺得最驕傲的開始,“開著車子去買樓,后備箱里直接放著一捆捆現金,售樓小姐,絕對被這個氣勢嚇懵。”不到一年,她把這些別墅全都轉給了外國人,“價格翻了一番,若是等到現在,那不得了,我估計單價起碼也有五六萬元吧。”
張素芹原是溫州某政府機關的公職人員,上世紀80年代下海,一直在深圳華強北經商。因為舉家搬遷到了深圳,2005年開始,她將炒房的主戰場轉移至深圳。她一貫秉承的原則是,要買就買當地最高檔的樓盤,要買就買豪宅,“若是無法轉手,大不了自己住。”
她對在深圳具體炒過多少套房子有所保留,我試探性地問她:“那,賺了幾千萬元總是有的吧。”她有點不屑,“幾千萬元?那算什么?!”
“我不僅炒樓,還炒鋪面,對面那個電子城鋪面出售時,我一下子出資兩個多億,一到三層全包了,然后租了一間辦公室,睡在那里,一日三餐讓人送,炒了一個星期全脫手了。”
張覺得那一次賺得很神奇,“我不貪,一個鋪面我賺五六萬元就夠了,也真怪了,我一炒就穩賺,那些接盤的人,現在焦頭爛額,虧十幾萬元出售也沒人要。”
2006年年底,張素芹又重回上海樓市,那時,上海樓市正好迎來了一個降價周期,她在淮海路與普陀區蘇州河邊又購進了好幾套房,“這回沒想炒,小兒子在上海工作。”
談及深圳去年樓市的瘋癲,張會心而笑,“當大家都狂熱的時候,你就要冷靜。當大家都很低迷的時候,就是你的機會。不過,可惜的是,在炒股時我忘記了這一條,現在已經虧了600多萬元。”
趕在深圳樓市暴跌臨門一腳的關口,張素芹全身而退,現在她最喜歡和鄉黨們侃的就是每天回家含飴弄孫的樂趣,偶爾也會故意透露一下兒媳準備換怎樣高檔的跑車。張現在在深圳還有多套別墅,在水榭花都還有幾套房子,那里的房價現在還是4萬多元的單價,張購進時只有1萬多元,“隨它跌,跌不回從前”。

不過,像她這樣有實力又全身而退的炒家并不多,更多的二流炒家則是處于被套牢的焦灼狀態。采訪期間,一名來自浙江金華的炒家就專門來請教張素芹,這名炒家在去年上半年投身樓市,眼下房產已經縮水三成,每個月要還貸數萬元。
“張姐,你說我該怎么辦?很著急,不知道要跌到什么程度?”
張頭也沒抬,“早著呢,還要跌,我看起碼要到2010年后才能回暖。如果想撤,那就早點出貨,虧一點算了。”
“可是,張姐,有人接盤嗎?!”
被套牢的二流炒家
就像沒人愿意輕易透露自己賺得盆滿缽滿到了怎樣的程度,虧到海底的那些炒家,也輕易不肯浮出水面,傳出去,多少是有些傷面子的。這是深圳福田區上沙某城中村,同樣經一名圈內人士的介紹,記者找到了35歲的浙商王強。
已是深夜10點多,王強坐在弄堂口的蘭州拉面店,6元錢一碗的拉面,店主給他夾了些許牛肉,這就是王強的晚餐。他是一個失敗的炒家,本來是做電子生意的,后來覺得還是炒房錢來得快,于是把店鋪置換出去,專門炒房。2007年9月之前,他買進了20多套商品房,絕大多數房款都是貸款而來。
那時候,他很是春風得意,一方面,跟著老鄉到新盤搶購,然后轉手賺取“喝茶費”,最甚時,一套房的“茶水費”高達七八萬元;另一方面,跟著中介公司“左手倒右手”,賺得不亦樂乎。
在“神話”破滅前,王強其實已經意識到,普通置業者已經沒有能力購房,都是炒家之間在互炒,但是他就是屬于張素芹所說的那種期待末日瘋狂的那一批“倒霉蛋”。“我總以為不至于這么快崩掉,總以為可以等到更高的價位。”王很沮喪。
2007年9月,樓市開始走向滑鐵盧,王強想脫手,可是已經晚了,沒有炒家愿意接盤,普通置業者又在觀望。“除非我愿意割肉,割小一點還不行。可是我舍不得,總想,就像股市一樣,下跌時會有一個沖高誘買的過程。”
然而,深圳樓市就像深圳的股市一樣,綠線一探到底,沒有給王強留下一點回旋的余地。
房子無法脫手,每個月還貸就要十幾萬元,他硬撐了大半年,此前做生意、炒樓賺的錢都貼補了月供。
“繼續耗著吧,我都耗到現在了,現在割肉更不劃算。”無奈之下,王強在兩個月前拋掉了2套房子,“每套虧了起碼20多萬元。”
“這樣便有了資金鏈,可以再耗一段時間。”王強搬到了現在住的這個城中村,不到20平方米的出租房,每天吃盒飯、拉面慘淡度日。他不知道這樣的日子還要“耗”多久,計劃中,過一陣子資金鏈斷了,再賤賣幾套,“總要留著一些籌碼,等到市場回暖了,翻本。”
就像那些坐著過山車從6000多點一路沖至2000點的股民,王強臉上的焦慮、不安、懊惱甚至憤怒,已經逐漸轉為麻木。
他正在逐漸學會不去關心樓市,除非到了每個月的還款日。他想找一份工作貼補房貸開支,在深圳已經有不少被套牢的炒房者通過信用卡套現還貸,王強認識的一個炒客,手上就有十幾張信用卡,不斷透支拆東墻補西墻。
夜空忽然劃過一道閃電,驚雷隨后而至,王強不想多談傷心事,他起身離去,一個穿著暴露的年輕女人牽著一條博美犬從他身邊而過。
“媽的,我混得連個二奶都不如。”他憤憤地罵。
一場暴雨隨后而至。
“網絡劍客”與斷供風波
即便在最困難的時候,王強也沒有想過去斷供,因為那樣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高,不過,在深圳,斷供已經出現,而且并非孤案,并在8月引發了一場斷供潮的風波。9月1日,在深圳某房地產經紀公司工作的段雁飛接到了深圳市仲裁委員會的通知,銀行提出的仲裁申請已經被受理,要求他在10日內上交有關欠款的答辯狀。這應該是目前曝光于媒體的斷供案例中,唯一一個確實出于經濟壓力,斷供目的也是最經得起推敲的案例。
2007年8月,段雁飛與某銀行深圳南山支行簽訂了一份《個人購房借款合同》,該行發放個人住房貸款63萬元,期限360個月。段以所購的南山區南光路某小區房產作為抵押。原本,段雁飛是沒有實力支付首付的,但當時的深圳,開發商、中介、投資客普遍在鉆銀行放貸審查不嚴的漏洞,聯手虛構房價、制造假合同以騙取銀行貸款,甚至可以做到零首付、負首付。而炒家也可以在找到下家之前,利用多貸的錢維持月供。
段雁飛的這套房子總價68.5萬元,首付二成應該是13.7萬元,但是在負責評估的擔保公司的幫助下,這套房子被提高了估值,這樣,段雁飛便申請到了更多的銀行貸款,然后用多余的貸款來抵充首付金額。實際上,段雁飛只支付了5.5萬元首付款。
在樓市交易活躍時,段雁飛這樣的地產中介一個月收入過萬是很容易的事情。因此,段雁飛以為自己供貸不會有問題,孰料,就在他供樓一個月后,央行與中國銀監會聯合發布了《關于加強商業性房地產信貸管理的通知》,提出了嚴格放貸管理的新政。
深圳樓市也很快進入“秋天”并向冬天一路邁進,房價暴跌,成交量急劇萎縮,最先受到沖擊的就是中介公司。大部分段雁飛這樣的中介人員月收入銳減至一兩千元,于是,月供便成了負擔,到今年5月,段雁飛難以維持,于是部分斷供,一方面是向銀行表示自己不想斷供的善意,另一方面也擔心斷供產生他難以承受的后果。
其實,從今年6月,斷供潮的傳聞就已經在深圳傳開,并在7月一度甚囂塵上,最終引起中央有關部門的重視,派出國務院調查組實地調研。
斷供潮現在已經被證實是一個陰謀,最先發出斷供潮警示信號,也是掀起這場風波的始作俑者是一名網絡劍客。現在這名“劍客”被揭發為本身就是一個炒家。
“劍客”是深圳樓市特有的怪象,有透露,深圳樓市有一百多名“劍客”,他們本是一些活躍于各個論壇的網民,熱衷于地產評論。后來,逐漸被房地產商重視甚至利用。這些“劍客”很多都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有些還以樓評家的身份面對公眾,但實際上是靠房地產商養活,幫助房地產商以及代理機構營銷策劃、控制網絡輿論、引導消費者。
用一句時髦的話說,他們就是在利用公信力幫助地產商搶占輿論陣地。伴隨斷供潮傳聞而來的,還有一些主動的斷供新聞報料者。但是最后,當深圳市銀監會等部門出來辟謠后,這些所謂的斷供新聞報料者很多都不知所蹤。
炒作斷供潮的醉翁之意在于試圖營造輿論,逼著政府出手救市。
斷供邊緣人
斷供潮至少短期內在深圳不會出現,但在斷供邊緣的人卻不是一個小數目。廣東中圳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子儒從8月以來已經接到了20多個斷供咨詢。來咨詢的幾乎都是段雁飛這樣的中介公司員工,他們在2006年抵住了誘惑,在2007年7月前抵住了誘惑,卻在2007年7月之后失去了理智,成為了炒家中最后一個接棒者。
錢,在那個時候真的是太好賺了。在利益的驅動下,這些大多來自湖南、江西農村的小伙子在主管的培訓下,整天煽動更多的人加入炒房大軍,他們幫助炒家騙貸,給炒家洗腦,他們給炒家吃的“定心丸”就是,“如果虧了,大不了把房子扔給銀行,損失留給銀行。”
但現在,深陷房貸壓力的他們卻赫然發現,這句話原來是一個天大的誤導。
劉子儒說,幾乎所有的咨詢者都以為斷供后大不了損失一個首付款,“那本來就做過手腳,沒有多少。”但實際上,斷供后,銀行會向法院提起訴訟,拍賣房產,如果房產拍賣的價格能抵充貸款,那就沒事,但問題是,拍賣價往往遠低于市場價,而且因為拍賣,還要產生很多手續費。
“也許你100萬元的房子,最后拍賣只能拿到50萬元。剩余的欠款,銀行會繼續追討,查封你其他的財產,直至還清,而且信用記錄將跟隨你一輩子。”當劉子儒作出這番解釋后,大多咨詢者都愣住了,于是不敢斷供,很多人到了還款日便四處借錢,但借的次數多了,只借不還,朋友們再也無人肯借。
影響于是輻射至他們遠在老家的父母、親友,但他們大多原本就是貧困家庭,親友救濟只能是杯水車薪。“很多人開始兼職,或者跳槽謀求更高的薪水,問題是,他們的知識結構決定了他們在這個城市的薪水水平。”劉子儒說。
“我原本想在深圳賺一筆錢回家娶親過日子,沒想到現在被困在這里還債。”某中介員工抱怨,他也想壯士斷腕,把房子掛在公司房源下出售,但一直無人問津。這名員工感嘆,前不久,有一名炒客急于脫身,提出只要有人接盤就附送自己的寶馬車一輛,但據說到現在,這輛寶馬也沒能找到新東家。
房價的下挫也引發了大量購房者與開發商的矛盾,劉子儒接手了一個案子,深圳碧水龍庭的75名業主聯合以斷供為要挾要求開發商解決房屋質量以及小區規劃等問題。
碧水龍庭在梅林關外,2007年8月,房價炒至14000多元每平方米,甚至更高,現在房價已經縮水近40%。這引發了前期置業者極大的不滿,在這場糾紛中,開發商說,斷供者名義上是維權,實際上是對降價不滿,要求開發商補償損失或者補送裝修。
劉子儒說,斷供者沒有跟他講心底的真實想法,但他可以肯定將來這種案子會越來越多。
“現在的勢頭是,業主與開發商的矛盾不是一個兩個地出現,而是上百個,與房價肯定有關,斷供,也許只是一個手段。”
中介慘淡經營
9月4日下午,中原地產福田區南C區區域經理熊贊科組織旗下4家門店的經理召開會議商討應對市場慘淡的對策。熊贊科門店業務量較高峰期削減至少四成,原本他管轄的區域一個月傭金收入最高200多萬元,但現在平均下來不過60萬元。“這當中90%是出租傭金。”
中原地產占據深圳20%的市場份額,在整個中原地產福田區,19家門店在2007年高峰期,一個月的傭金收入高達2400多萬元,但現在不過600多萬元。“市場觀望情緒濃厚,有時候一個區域一天成交不了一套房,以前隨隨便便都可以十幾套。”
熊贊科所在的主要是口岸區域,置業者以港人為主,他說,因為港人的購買力比較強,所以泡沫相對小一點,斷供的案例還沒有聽說。
片區內的港田花園、海悅華城,去年高峰期的房價是18000元每平方米,現在已經跌到11000元左右,差不多是去年4月的房價水平。由于市場不景氣,很多港人將房子裝修后出租,“港人和大陸的置業者不同,經歷過香港樓市的暴跌,心態很從容。”
“剛性需求的人放棄買房,改為租房,因此片區租金普漲。”他介紹,一室一廳的月租金從2000元漲到2800元也不過用了兩個多月。
依照他對市場的了解,真正被套牢的是去年4月尤其是7月后入市的炒家,以前也從樓市中賺了一些錢,現在是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走得快的走了,走得慢的死撐著,誰都希望在自己崩潰前,政府能救市。”
他承認樓市火爆,中介是幕后推手之一,現在樓市蕭條,最先倒霉的也是中介公司,他承認中介行業內有人參與炒樓被套。“但是我們去年9月就發現市場不對勁,開始調整。”他以自己為例,2006年以72萬元購進了一套房子,自住加投資。高峰時達到110萬元,但是他沒有舍得脫手,期望賣到更高的價錢。
2007年11月,這套房子跌到了95萬元,熊贊科決定拋售,“有一個買家看中了,說要還價,我說那你還啊,他說90萬。好!就90萬,我立即就賣給他了。”半個月后,這套房子市價很快降至80萬元,熊說,現在很多房子就算再虧十幾萬元都沒人來買,剛性需求的人都在等,大家都看不到頭,不知道底在哪里。
深圳樓市現在出現三級市場賣新盤的怪象,原本新盤都是由二級市場的代理公司銷售。
“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去年我們帶客去新盤,二級代理不理我們,他們自己的客源都消化不了,對我們態度很不好,我們對此意見很大。現在,新盤賣不動,二級代理對我們很客氣,請吃早茶,給我們提高分成的比例,希望我們幫他們一起賣新盤。”
熊贊科在接受采訪時不斷收到二級代理的短信,他說,現在新盤業務大概占到三級市場的一半業務量。“房地產商還擺出擂臺,讓幾家中介對擂,自己坐收漁翁之利。”
他認為中介公司已經進入冬天,樓市的泡沫也沒有完全擠掉,“斷供不會出現,政府現在完全沒有必要救市,我們希望借助這一輪調整,促進房地產業、中介行業的健康。”
中介公司關門的現象在深圳還沒有大規模出現,熊贊科說,大家都在期待金九銀十,如果這兩個月再不景氣,可能就有很多中介公司關門了。
遮遮掩掩的開發商
沒有一家開發商肯公開承認自己的資金鏈出了問題,也沒有一家開發商承認旗下的樓盤正在降價銷售。甚至,沒有開發商肯痛快地接受媒體調查。但在深圳樓市走一遭,你會發現,幾乎所有的樓盤都在打出類似送手機、送裝修,甚至每20戶抽獎送一輛轎車的促銷,可是,購房者似乎并不買賬,售樓處依舊門可羅雀。
也不是沒有人,剛到大門口就有幾個神情懶散的人盯著你看,知情人士透露,當中一些其實是中介假裝的“托”,營造樓市已然正在回暖的假象。深圳市房管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最近幾個月以來,深圳樓市新盤日均成交量最多不過一百多套。
此前,房管局網站曾經爆出日成交量5套的數據,被輿論認為是崩盤征兆,但房管局此后很快辟謠,說是系統升級所致的技術錯誤。不過,市場對于這個解釋至今仍是將信將疑,不少中介公司的人說,以他們對市場的切身感受,事實恐怕確實是那么慘淡。
深圳市房地產交易中心,去年7月還是摩肩接踵,現在已是空空蕩蕩,少了至少三分之二的人流。一級市場土地流拍也已經發生,上個月剛公布的2007年上半年深圳房地產調查報告顯示房地產開發商的信心已經降至歷史低點。
普遍的觀點是,在寶安、龍港,個別樓盤降價幅度已經逼近50%,而一向被視為房價指標性區域的關內,降價幅度也有30%,整個深圳樓市平均降幅38%。
但在鄒濤看來,這只是一個降價假象,確切地說,是關外某個樓盤的某棟樓的最差的某套特價房降價50%。“開發商為的就是吸引人氣,你真去買房,會發現特價房就一套,其他的房價不過下降了10%。”
鄒濤,2006年在深圳發起不買房運動,今年7月又發起萬人團購行動,“地產商的日子絕對不好過,資金很緊張,只是對外強硬,死撐著而已。”
深圳一家地產商不久前跟鄒濤訴苦,欠了幾千萬元債務,想用房子抵充工程款,打了八折施工隊也不要。“他希望,抵充工程款后的剩下的房子,我們能接手。”
“對很多開發商而言,能賣掉30%的房子就是勝利,這樣便有了資金過冬。”鄒濤說。
炎炎烈日炙烤下的深圳樓市,冬天的寒風,前梢已至。
(本文炒房者應采訪對象要求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