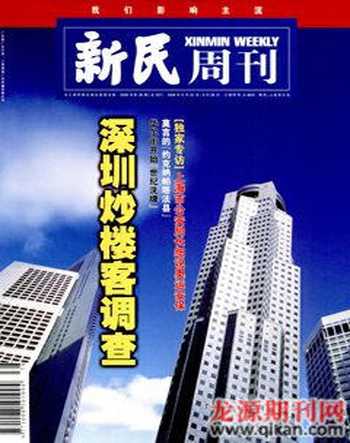成熟的代價是平靜
殷冬明

如果一個市場沒有經歷過深重的危機,它的繁榮就有很多脆弱之處。房地產市場也是一樣。
我常常讀《紐約時報》作家紀思道(Nicolas Kristof)的專欄,有一段對話讓我記憶深刻。他曾經問一位在中國居住了15年的大學教授:中國發達部分與西方的差距在哪里?后者想了很久,回答道:中國發展很快,但他們的繁榮還不夠成熟,因為很久以來,這是他們第一次繁榮。
我想,他的話里是有深意的。比如說,如果美國人不曾經歷過30年代的大蕭條,他們可能很難學會一個現代證券經濟中必須具備的概念,那就是:投機心態是有害的,而全民投機則是災難性的。事實上,從記者曼徹斯特的名著《光榮與夢想》中我們會發現異常極其有趣的景象:1920年代后期左右的美國證券市場像極了中國近20年的證券市場——全民炒股,尤以缺乏金融知識的家庭主婦為甚。盡管整個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有各種原因,但是全民投機炒股所引發的金融泡沫的確是大堤上的第一個破洞。如果我們今天從美國的金融市場的成熟體制中看到了中國的證券投資業所缺乏的現象,即基金超過散戶成為投資主體,那并不是因為美國人天生比我們聰明,而是因為他們從1929年以來比我們多學了好幾課而已,而且每一課的學費都是驚人的。
房地產市場也是一樣。今天中國房地產市場中所表現出來的躁動,實際上是很多成熟的房地產市場早已經歷過的。比如,要說價格異常波動,且不論美國,近在香港的樓市和東京的樓市,在過去15年中就曾經猛烈地坐過電梯。1998年我去香港訪問,正趕上回歸第一年,量子基金和港府(應該說,是有中國撐腰的港府)在股市和匯市上打得你死我活,樓市則已經一瀉千里,握有樓花或樓盤的廣大普通市民成了“負翁”。東京則是更加慘淡,2005年房地產市場跌到25年來最低點,很多人的投資僅剩下百分之幾。然而令人吃驚的是,香港和東京的市民對于房地產市場價格波動的承受力很強。歷史教會他們,房子的價值會跌,也會漲,這只是一個周期問題。資產為負數并不是世界末日——當年我認識的幾個炒樓失敗的香港朋友,早已抖擻精神,再戰江湖,在深圳置下四五套高端物業了。而最近深圳市場下跌,他們依舊早茶吃得倍兒精神。問他們:難道不慌嗎?他們說:98香港都經歷過,這點兒下跌算什么?
平靜是成熟的標志。一個成熟的市場自然不應該對于正常漲落過于敏感。但是,中國的樓市價格波動異常,無論是開發商還是老百姓,都顯得頗為急躁。這急躁表現在:明明房地產市場已經發生了變化,需求明顯降低了,大量的開發商還扭扭捏捏地不好意思直接降價,而是變著法子出花樣:送裝修也好,送公共基金也好,打折也好,就是不說直接降價。而業主呢,看到自己的房產價值低于自己的預期,也怒氣沖天,無法接受。可問題是,房地產市場的漲跌是個正常市場規律,一旦有漲,總有一天要跌的。而無論怎樣發怒,我們既然享受了房價上漲給我們帶來的喜悅,就必須接受房價下跌可能給我們造成的損失——其實,只要不是投機炒房客,那損失也有限得很。畢竟,房子還是會漲回來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為什么一個成熟市場對于起伏波動的反應是平靜的?那是因為他們對于類似的經濟戲劇,已經看得太多了。(作者為易居中國·上海克而瑞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戰略規劃總監,清華大學客座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