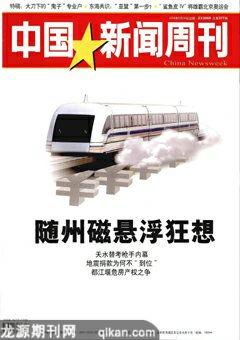“冷藏”的新聞與“歷史”
雷 頤
有人說“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有人說“新聞是歷史的底稿”。總之,新聞“存”久了,就成為歷史。然而,有一種“新聞”卻非常特別,不是為了公開報道公眾傳播,只是為極少數(shù)人“通消息”。在中國特色語境中,這種“新聞”叫“內(nèi)參”。重要的是,“內(nèi)參”受到的限制不能說沒有,但比一般意義上的“新聞”卻要少得多。所以,當(dāng)經(jīng)過幾十年“冷藏”后,這種具有特殊價值的新聞開始“解凍”,便是格外珍貴的昨天的“歷史”。
從1959年大學(xué)畢業(yè)到1982年調(diào)離,張廣友先生在新華社總社當(dāng)了二十多年的記者,寫了許多公開報道,但寫得更多的,還是那些設(shè)有公開的“內(nèi)參”。“文革”中,作為只送政治局領(lǐng)導(dǎo)參閱的高度機(jī)密內(nèi)刊的骨干,他幾乎寫了近十年的“內(nèi)參”。記者、尤其是“內(nèi)參記者”的特殊身份,使他親歷并詳細(xì)了解共和國歷史上許多長期不為人知的重大事件。當(dāng)把這些公之于眾,便成為我們集體“抹不掉的記憶”。
在《抹不掉的記憶:共和國重大事件紀(jì)實(shí)》中,張廣友記述、分析了“三年困難”、沒有公開報道的1975年淮河大水災(zāi)、大動蕩中到鐵道部“蹲點(diǎn)”、農(nóng)村改革初期的激烈爭論……
1960年,到新華社當(dāng)記者的第二年,張廣友“下放”到山東農(nóng)村,詳細(xì)了解了大饑荒的真實(shí)情景。他的筆記本上記錄著以下片斷:惠民北鎮(zhèn)全公社近4萬人不到一年已經(jīng)死了1000多人,全社只出生了3個孩子;麻店公社大部分社員得了水腫、干瘦病,4594名16至45歲的婦女中,有2188名閉經(jīng),子宮脫垂者84人……他來到西馬小隊(duì)時,正是死人高峰期。他寫道:“我進(jìn)村第三天就聽說有一家3口人都死了。最后死的那個人,隊(duì)干部找不到壯勞力去抬尸,我自告奮勇去了。”人們已無力深埋尸體,只好找點(diǎn)浮土壓上。他說:“這怎么行?尸體被狗吃了怎么辦?”農(nóng)民回答說:“哪里還有狗,有狗人們怎能不把它先吃了,還能等到它吃人?”他往旁邊看了看,還有三具尸體都是這樣“埋的”,已經(jīng)一個多月了。村莊、鎮(zhèn)子,死一般沉寂……
從1961年起,農(nóng)村政策開始調(diào)整,解散了公共食堂,包產(chǎn)到戶,嚴(yán)峻的形勢迅速好轉(zhuǎn),生產(chǎn)開始恢復(fù)——張廣友興奮不已,寫了《李家店村包產(chǎn)到戶調(diào)查》作為內(nèi)參發(fā)表。沒想到,這篇“調(diào)查”剛發(fā),風(fēng)向突變,“毛澤東重提階級和階級斗爭,把一些農(nóng)村出現(xiàn)的‘包產(chǎn)到戶以及鄧子恢、陳云等中央和各級領(lǐng)導(dǎo)干部、群眾對此的支持,批判為‘單干風(fēng);并說,‘右傾機(jī)會主義就是修正主義,黨內(nèi)有人搞修正主義。”他的這篇稿子正好撞到“槍口”上,成了被批判的對象。然而,令他終身感激的是,新華社國內(nèi)內(nèi)參部主任夏公任主動承擔(dān)了全部責(zé)任,當(dāng)記者不久的他才過了關(guān)。
“我深深感到,作為一名新華社記者,能夠親歷這場災(zāi)難,能夠有這么多的第一手材料,并且保存到今天,實(shí)屬不易。它是歷史的見證,我不忍心讓這以成百上千的農(nóng)民生命為代價換來的沉痛教訓(xùn),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淡漠、蒸發(fā)。這種責(zé)任感是我克服重重困難的力量源泉。”他說,這是“堵在心口的話”。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