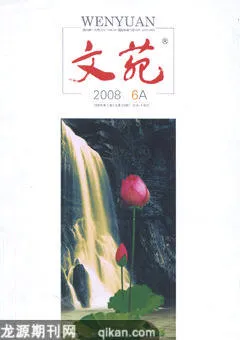一寸春心早已灰
方 帆
與好友外出踏青歸來,剛好是路燈點亮的時候,這時的城市顯示出讓人熟悉的溫情。于是打開計算機,想寫一點什么,無意發(fā)現(xiàn)了這句哀婉的詩。上網(wǎng)一查,原來是蘇曼殊的一首詠物詩,名叫《櫻花落》。“十日櫻花作意開,繞花豈惜日千回?昨來風(fēng)雨偏相厄,誰向人天訴此哀?忍見胡沙埋艷骨,休將清淚滴深杯。多情漫向他年憶,一寸春心早已灰。”
在我的記憶中,這個出生于日本橫濱的中國近代學(xué)者一生寫滿了坎坷,卻是一個完全可稱天才的文人。不僅詩境別有風(fēng)味,善于丹青,而且還翻譯了雨果的《悲慘世界》和拜倫詩集。因為承襲了李商隱的風(fēng)格,有評論說他的詩文“清艷明秀,為后時鴛鴦蝴蝶派所慕”。但或許是天妒英才,這個年輕的才俊卻經(jīng)歷了幾度磨難后,在34 歲的盛年即飄然離世了。
蘇曼殊的一生中,大部分時間在東瀛度過,其間又加入了與彈箏女百助和另一個日本女子兩段不如意的愛情,于是感情的挫折加劇了他對故土的思念,使他帶著一顆疲憊的心回到廣州出家。然而世俗的心并沒有在寺院的暮鼓晨鐘里得到撫慰,終究還是走出山門,漂泊塵緣。
似乎在他的心里,報國還家的志向始終得不到實現(xiàn),面對一片狼藉的祖國,卻只能寄情于景了。而長期浸淫在日本文化中的經(jīng)歷,又擺脫不了日本人對櫻花的激賞中那種初綻即逝的審美心態(tài)。這又不禁引起了我對日本的一些思索。日本是一個值得探究的民族,他們對自然界短暫的美景迷戀向往,執(zhí)著地認為沉浸在其中可以洗滌心志。為了維護這種“向往”,他們能夠決然地面對一切毀滅,包括自己的生命。這是一種命運的劫數(shù),還是一種“自我”的坦途?其實,這種對日本人的理解我們早已不再陌生。前不久剛剛讀過美國作家露絲·本尼迪克特的《菊花與劍》,這本書在世界文化人類學(xué)的專著體系中的知名度已經(jīng)無須贅述,甚至被西方學(xué)者認為是“剖析日本人心理的最佳力作”。在其中,無論是作者談到“報恩”、“盡孝”還是“美德”的問題,其實都離不開對“自我”意識的一種高度關(guān)注和反省。這些原本屬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載體被日本人完全地繼承了下來,并且在他們的人生中嚴格地貫徹,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國人深思嗎?當(dāng)我們還在熱烈地討論“到底該不該重視傳統(tǒng)文化的教育, 該不該重拾傳統(tǒng)的道德禮儀”時,當(dāng)我們在所謂的東西方文化的岔路口彷徨而疑惑的時候,日本這個曾經(jīng)與我們交戰(zhàn)的民族卻悄然間給我們作出了回答,他們用美國人的體系構(gòu)筑了國家的民主和進步,思想上卻表現(xiàn)出了對中國傳統(tǒng)道德文化的信奉,這難道不是我們應(yīng)該反思的嗎?
手撫著這些猛然間喚起的思緒,腦海中不禁浮現(xiàn)出蘇曼殊曾繪的一幅《寫意翁詩意圖》中的題詩:“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無主月自圓”,簡單的十四個字,有他的身世、他的情感和他心里的佛。
寫來寫去,除了兩首詩和一個人,竟是空空如也,不知所云。只好借用一下李煜,這位與蘇曼殊身世相似、本應(yīng)該只是個文人的落魄皇帝的詩結(jié)尾吧:
“誰在秋千,笑里輕輕語。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