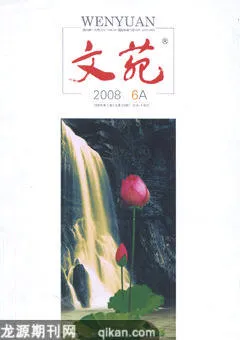拔牙記
2008-07-28 06:34:32陳蔚文
文苑·感悟 2008年6期
陳蔚文
這顆阻生性智齒在拍片后終于決定要拔了,醫生說,早拔就好了,就不會把前面那顆牙頂松并造成齲齒。
拍片回來,有個女人躺在那拔牙,各種工具擺在托盤里,閃亮的刀鉤鉗錘,十八般武器,女醫生手腳麻利,她的生涯由無數口腔構成,她無疑富于經驗,但她還是被面前這個女人的牙弄得心煩,她拔了許久,對探頭進來的我說,你再等等!
已近正午,她喊了個男牙醫過來幫她診斷處理這牙。躺在那的女人盡可能地將嘴巴張到最大,像在呼喊。男醫生身量孔武,但這也沒讓進展變得更快。我差點等得失掉耐心。總算,女醫生讓我進去,她看了眼口腔,“你這牙要預約,拔起來很傷元氣的!”
預約了兩天后。兩針麻醉下去,還好,可以忍受,射燈下,牙齦和面頰漸漸麻木,放棄對疼痛的抵抗。我準備一場艱巨工程的開始。
女醫生的小錘和榔頭一記記落下,另一名女醫生托住我的腮幫,然后是鉗子,我的口腔里像進駐了一支裝修隊。她準確地使用著那些武器,不管牙齒對牙床的依戀有多深。
出乎意料,牙迅速地拔出來了,迅速得令女醫生吃驚,令我遺憾,我忽然覺得和一顆牙齒斗爭的過程是有趣的,雖然它艱巨,充滿血腥。像上回那個女人,我甚至有些羨慕她,拔牙的難度和拔出后的輕松是成正比的,它會使一顆牙顯得重大,像一次小型手術,拔完后的當事者可以當作又完成了件人生之事,但沒想到,我的牙如此快地離開了身體,它像早在此處待膩了,急于換個地方。
臺灣詩人夏宇寫過首詩,“為蛀牙寫的一首詩/很短/念給你聽:拔掉了還疼/一種空洞的疼/就只是這樣/仿佛愛情。”
走下樓,口腔里塞著厚的藥棉,喉嚨散發著淡的血腥氣,半小時后,吐掉藥棉,那顆空掉的地方空洞,但并不疼——像有些人的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