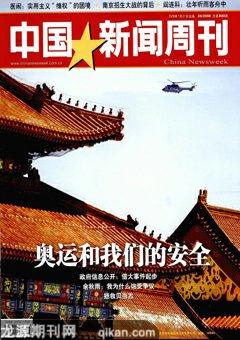香港藝術(shù)隱秘生長(zhǎng)
楊時(shí)旸
當(dāng)大陸藝術(shù)家在西方拍賣市場(chǎng)上異軍突起的時(shí)候,香港當(dāng)代藝術(shù)似乎卻一直處于失語(yǔ)的狀態(tài)
中國(guó)當(dāng)代藝術(shù)以超常的速度進(jìn)入國(guó)際視野的時(shí)候,香港當(dāng)代藝術(shù)和藝術(shù)家們卻幾乎被人忽略。雖然香港的拍賣公司一次又一次為內(nèi)地的藝術(shù)家制造出令人咋舌的高價(jià),但是對(duì)于香港本土藝術(shù)卻視而不見(jiàn)。
當(dāng)香港的設(shè)計(jì)、戲劇、電影這些藝術(shù)形式逐漸進(jìn)入大眾視野,香港的當(dāng)代藝術(shù)和藝術(shù)家卻一直以非主流和業(yè)余的姿態(tài)徘徊在自己的小圈子內(nèi)。
退休后成了藝術(shù)家
今年73歲的朱興華在1992年退休之后,他的身份成為了藝術(shù)家。在此之前,他是香港一家精神病院的護(hù)工。雖然在他做護(hù)工的25年里,業(yè)余時(shí)間一直堅(jiān)持畫畫參與展覽,但除了周圍有同樣愛(ài)好的朋友,沒(méi)人當(dāng)他是一位藝術(shù)家。在香港,沒(méi)有多少普通人會(huì)關(guān)注藝術(shù)。
朱興華是老一代香港藝術(shù)家的典型樣本——有一份穩(wěn)定工作,業(yè)余時(shí)間創(chuàng)作,默默無(wú)聞卻心甘情愿。
1972年,香港大學(xué)開(kāi)設(shè)了全港唯一一家藝術(shù)訓(xùn)練班,學(xué)校邀請(qǐng)一些國(guó)外藝術(shù)家和香港本土老一輩水墨畫畫家教學(xué)。每年學(xué)費(fèi)兩千港幣。很多對(duì)藝術(shù)有興趣的年輕人紛紛報(bào)名。朱興華是其中一位。訓(xùn)練班三年一屆,每周四天晚上上課,每次課程四個(gè)小時(shí)。課程包括繪畫,雕塑以及中西藝術(shù)史。
因?yàn)榕嘤?xùn)課程以國(guó)外老師為主,所以很多繪畫技巧都從西方視角進(jìn)入。“即使畫水墨也有很多西方元素,我的作品到現(xiàn)在也有很多西方的東西。”朱興華用磕磕絆絆的普通話說(shuō)。
3年里,朱興華白天上班晚上上課,“我從沒(méi)逃過(guò)一次課。”直到現(xiàn)在,朱興華對(duì)此仍很自豪。那個(gè)訓(xùn)練班報(bào)名時(shí)有20多人參加,3年之后,只有三四人堅(jiān)持到畢業(yè)。
除上課外,朱興華一直在堅(jiān)持自己的創(chuàng)作。他的作品大多都與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guān)。他在精神病院工作的那段時(shí)間,作品幾乎全部是醫(yī)院中病人的舉止和行為,深色的背景中滲透著古怪的氛圍,朱興華把那些病人當(dāng)作朋友,畫面氣氛雖然古怪但絕不猙獰。退休后的一段時(shí)間,朱興華移居鄉(xiāng)下,作品中開(kāi)始出現(xiàn)鄉(xiāng)村生活的圖景。2000年之后,他開(kāi)始關(guān)注世界各地發(fā)生的災(zāi)難,“年紀(jì)大了,對(duì)這些悲傷的東西越來(lái)越關(guān)心。”朱興華說(shuō)。
朱興華嘗試創(chuàng)作期間,香港并沒(méi)有太多可供展覽的場(chǎng)地,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gè)地方收費(fèi)是三天一萬(wàn)塊港幣。“一個(gè)人負(fù)擔(dān)不起場(chǎng)地費(fèi)用,我們大家就一起湊錢。”朱興華說(shuō)。當(dāng)年,這些致力于藝術(shù)的年輕人開(kāi)始組織畫會(huì)。朱興華所在的“香港視覺(jué)藝術(shù)協(xié)會(huì)”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畫會(huì)之一。
從1972年創(chuàng)立到現(xiàn)在。它不同于大內(nèi)地官方美協(xié),也與八五美術(shù)新潮中的派別有異。這個(gè)畫會(huì)成員沒(méi)有共同風(fēng)格,類型從油畫到多媒體藝術(shù)全部囊括。日常開(kāi)銷由會(huì)員交納的會(huì)費(fèi)支付,每年100元港幣。直到現(xiàn)在還不斷有新人加入。
現(xiàn)在,朱興華有作品被香港藝術(shù)館收藏,也有一些朋友私人購(gòu)買,但“仍然不能靠畫畫生活”。香港至今沒(méi)有專業(yè)的藝術(shù)院校,非商業(yè)性的藝術(shù)批評(píng)和報(bào)道也相對(duì)較少,藝術(shù)家只能處于“自?shī)首詷?lè)”的層面。
而香港藝術(shù)圈沒(méi)有過(guò)如內(nèi)地80年代興盛的藝術(shù)運(yùn)動(dòng),也沒(méi)有批評(píng)家把藝術(shù)家送入國(guó)際藝術(shù)視野,朱興華和其他香港藝術(shù)家似乎注定了默默無(wú)聞的命運(yùn),這樣的情形在年輕一代藝術(shù)家身上仍沒(méi)有太大改觀。
新一代藝術(shù)家的“蝙蝠俠”生活
馮力仁剛剛從工作的電訊公司請(qǐng)了年假,他對(duì)老板說(shuō),“我要去北京看看奧運(yùn)場(chǎng)館。”實(shí)際他是到北京參加一次展覽。“我個(gè)人藝術(shù)家的身份,公司里沒(méi)人知道,我就像蝙蝠俠,白天晚上是不同的人。”馮力仁說(shuō)。
馮力仁有MBA的學(xué)歷,卻癡迷于藝術(shù),他經(jīng)常自己從網(wǎng)上找一些教材學(xué)習(xí)雕塑的基本方法,“小時(shí)候因?yàn)殚L(zhǎng)輩都覺(jué)得做藝術(shù)會(huì)窮一輩子,沒(méi)機(jī)會(huì)學(xué)。”馮力仁說(shuō),他家人的想法代表著香港絕大多數(shù)人對(duì)于藝術(shù)家的看法,但是馮想成為職業(yè)藝術(shù)家的念頭“經(jīng)常在腦子里一閃一閃”。
如今在香港,有一些年輕人開(kāi)始像十幾年前的內(nèi)地藝術(shù)家一樣,尋求群落式的生活方式。火炭藝術(shù)村是最大的一個(gè)香港藝術(shù)家村落。那里曾經(jīng)是食品廠、木材廠等等工廠的聚集地,現(xiàn)在也仍然有一些廠房仍在開(kāi)工。“基本都是幾個(gè)藝術(shù)家合租一個(gè)單位,有的工作室樓下就是肉制品廠,味道特別不好。”馮力仁說(shuō),“和北京798沒(méi)法比。”居住在這里的年輕藝術(shù)家基本上靠一些平面設(shè)計(jì)的工作勉強(qiáng)為生,各自進(jìn)行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永遠(yuǎn)不知道何時(shí)能嶄露頭角。
馮力仁雖然與火炭藝術(shù)村的藝術(shù)家們有交往,但沒(méi)有勇氣放棄現(xiàn)在的工作。“一是香港的生活壓力太大了,二是,我的創(chuàng)作靈感都是來(lái)自生活,我擔(dān)心一旦不工作,靈感也就沒(méi)了。”馮力仁說(shuō)。
馮力仁的作品全部為雕塑,以木雕為主。人物形態(tài)幾乎全部都是香港的市井上班族,西裝領(lǐng)帶、公文包,重壓之下垂頭喪氣的表情,呆板、凝滯,生氣全無(wú)。“以前我是那個(gè),現(xiàn)在我是這個(gè)。”馮力仁分別指著作品中的管理層和底層說(shuō)。在SARS之前,馮力仁在一家公司做管理,疫情之后公司倒閉,馮失去工作。“那段時(shí)間,我才把創(chuàng)作的方向放在香港上班族身上。”現(xiàn)在,香港地鐵里擺放著幾件馮力仁的作品,呆板的雕塑和周圍麻木洶涌的人流相映成趣。但是馮力仁依然無(wú)法靠藝術(shù)謀生。香港人更多地把這些雕塑當(dāng)作一種充滿趣味的擺設(shè),沒(méi)有人把這些看作藝術(shù)。
如果馮力仁生活在藝術(shù)市場(chǎng)火熱的大陸,只要作品在地鐵這樣的公共場(chǎng)所展示一定會(huì)引起一些畫廊的關(guān)注,這些對(duì)市場(chǎng)嗅覺(jué)敏銳的藝術(shù)機(jī)構(gòu)會(huì)抽取出作品中最有市場(chǎng)價(jià)值的概念進(jìn)行包裝,推出個(gè)展,邀請(qǐng)?jiān)u論家撰寫文章,藝術(shù)家會(huì)成為整個(gè)鏈條中的一個(gè)環(huán)節(jié),最終被推向市場(chǎng)。
面對(duì)內(nèi)地藝術(shù)家動(dòng)輒幾百萬(wàn)的拍賣價(jià)格,馮力仁有時(shí)也會(huì)羨慕,“我只有下班之后才能做藝術(shù),有時(shí)候很累就會(huì)想,要是能賣到幾百萬(wàn),就不用工作了。”
自?shī)首詷?lè)還是與君同樂(lè)?
香港相比于內(nèi)地,無(wú)論是文化資源還是市場(chǎng)力量,似乎都有著得天獨(dú)厚的一面。但是當(dāng)內(nèi)地藝術(shù)家在西方拍賣市場(chǎng)上異軍突起的時(shí)候,香港當(dāng)代藝術(shù)卻似乎一直處于失語(yǔ)的狀態(tài)。
“香港人普遍對(duì)于文化藝術(shù)還是比較陌生,藝術(shù)家和藝術(shù)圈、博物館里做的展覽,普通人都不太感興趣,這是環(huán)境和歷史的問(wèn)題。”香港藝術(shù)館館長(zhǎng)譚美兒說(shuō)。
由于香港一直缺乏專業(yè)藝術(shù)院校,到目前也只有香港大學(xué)和中文大學(xué)設(shè)有藝術(shù)系,所以無(wú)論對(duì)普通民眾藝術(shù)欣賞的培養(yǎng)還是藝術(shù)家的基本技巧都處于起步階段。從大多數(shù)香港藝術(shù)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無(wú)論是油畫還是雕塑,基本技巧都與內(nèi)地相差甚遠(yuǎn)。手法、技巧的粗糙都是藝術(shù)家走入國(guó)際視野的障礙。
香港藝術(shù)家深知自己的短處,也沒(méi)有沉溺于對(duì)技巧的訓(xùn)練,而是尋找用更為討巧的方式,例如很多年輕藝術(shù)家直接選擇了多媒體,而放棄了需要長(zhǎng)年訓(xùn)練的架上繪畫。
也由于商業(yè)誘惑少,香港藝術(shù)家更多通過(guò)創(chuàng)作表達(dá)觀念或自我感情。“香港藝術(shù)家沒(méi)有一些特別沉重的東西,作品都是很生活、很內(nèi)心、很哲學(xué)的東西。”譚美兒說(shuō)。
因?yàn)橄愀坶L(zhǎng)期以來(lái)生活相對(duì)安定,又多崇尚獨(dú)立思維,所以作品中極少出現(xiàn)宏大主題和背景,這樣的作品一方面使香港當(dāng)代藝術(shù)風(fēng)格各異,頗具活力,卻也讓收藏界摸不到香港藝術(shù)的主題,而放棄收藏。
“現(xiàn)在香港的畫廊幾乎沒(méi)有只做香港藝術(shù)家的,大多數(shù)做畫廊的都跑到內(nèi)地做生意了,做香港藝術(shù)賺不到錢。”譚美兒說(shuō)。
香港也沒(méi)有專門的基金會(huì)支持當(dāng)代藝術(shù)發(fā)展。只是在1994年,香港政府成立了藝術(shù)發(fā)展局,政府每年向藝術(shù)發(fā)展局撥款
1000萬(wàn)港幣,作為舉辦藝術(shù)展、出版藝術(shù)類書籍的支持。藝術(shù)家可以自由申請(qǐng)。每一屆威尼斯雙年展香港館的經(jīng)費(fèi)也由藝術(shù)發(fā)展局撥款資助。
沒(méi)有藝術(shù)批評(píng)家的推介,沒(méi)有圈子內(nèi)的運(yùn)作,更沒(méi)有被國(guó)際資本看中的標(biāo)志性符號(hào),而在商業(yè)高度發(fā)達(dá)的香港,只表達(dá)藝術(shù)家個(gè)人內(nèi)心的當(dāng)代藝術(shù)又無(wú)法迅速轉(zhuǎn)化為產(chǎn)品,香港藝術(shù)家像是在自?shī)首詷?lè)的散兵游勇,這也使得香港當(dāng)代藝術(shù)一直處于尷尬地位。
現(xiàn)在,有一些香港藝術(shù)家也開(kāi)始嘗試重大主題。比如香港“九七回歸”后的身份認(rèn)同。這樣的作品相比其他有著更好的市場(chǎng)前景。
而在這些年輕藝術(shù)家努力向職業(yè)身份轉(zhuǎn)變的同時(shí),香港當(dāng)代藝術(shù)是否還能保持之前的豐富和活力,尚不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