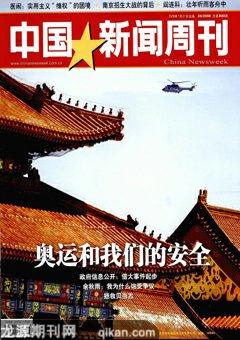“神鬼史觀”應當終結
徐慶全
歷史本身的不可復原性和對歷史原貌不可能完全客觀的認識,決定了人們對歷史解釋見仁見智的多元性。因此,諸多史觀異彩紛呈:唯物史觀、唯心史觀,英雄史觀、文明史觀等等,不一而足。而對于威權國家來說,歷史又是構筑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尋找歷史的現實意義遠遠高于尋找已經逝去的歷史真實的學術價值。當構筑意識形態的意義超越探究客觀歷史的意義時,用歷史構筑意識形態就會演變為一定程度的用意識形態來構筑歷史。這,我姑且稱之為“國家威權史觀”。而所謂的“神鬼史觀”即是“國家威權史觀”的一種表現形式。
“神鬼史觀”是一位搞黨史的朋友提出的,其解釋是:出于意識形態的需要,在歷史中活動的人物,要么是神、要么是鬼,總之,不能是人。著名學者楊天石多年對蔣介石的研究成果,一個實際的意義就是在沖擊“神鬼史觀”——不過,他沒有用“神鬼史觀”這個詞,而是用“人的本相迷失”來替代。他在新出版的《尋找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一書中說:“人的本相迷失的情況很復雜。一種是因‘捧。將某一個人捧為天縱之圣,絕對正確,永遠英明,仿佛斯人不出,世界就永遠處于黑暗中一樣。一種是因‘罵。將某一個人罵成十惡不赦,壞事做絕,禍國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殺的天字第一號大壞蛋,仿佛一切罪惡,一切黑暗,均源于斯人。”
這是楊天石有感于對蔣介石的妖魔化所發出的慨嘆,也是對“神鬼史觀”最好的注解。
長期以來,對于蔣介石的妖魔化,使其亦“神”亦“鬼”、時“神”時“鬼”。這種情況的出現,有國際背景和國內政治的相互作用。國際背景是指大約30年(1949~1979)的全球冷戰架構,大陸和臺灣分屬這個架構下的敵對兩方。國內政治是指兩岸各取所需的“威權史觀”,國共兩黨以意識形態的取向構筑各自的歷史,“神”化自己“鬼”化對方的領袖就成為各自的必要。因此曾幾何時,在臺灣,蔣介石是“神”,在大陸,他又變成“鬼”。而蔣介石的“人的本相”,也就在“神”“鬼”之辨間“迷失”了。
顯而易見,“神”“鬼”兼具一身的蔣介石,不是歷史上真實的蔣介石。依據原始資料還原其本來面目,一直是史家的興趣和宗旨。楊天石就是其中之一。上個世紀90年代初全球冷戰架構解體后,兩岸政治與學術氣氛日益寬松,“威權史觀”有所松動,“神鬼史觀”也隨之被逐漸解構,對蔣介石的研究也朝著去“神”、去“鬼”的方向邁步。楊天石由此開始追尋有關蔣介石的原始資料,尤其關注蔣介石的日記。在大陸,查“類抄本”,赴臺灣查《事略稿本》及5種“記”本。2006年藏于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蔣氏日記“手稿本”開放后,他又數度赴美。板凳坐得二十年冷,成果匯于一書中,蔣介石也從“神”“鬼”之辨,逐步還原成為有成有敗、有功有過的歷史“凡人”。
楊天石尋找蔣介石“人的本相”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去“神鬼史觀”的過程。因此,本書除了史學價值之外,還有另一層值得重視的意義——向學界提出的忠告:“神鬼史觀”應當終結。
(作者為《炎黃春秋》雜志執行主編)
- 中國新聞周刊的其它文章
- 目擊
- 防衛性醫療害人害己等
- 經濟政策調整應有長遠視野
- 看板
- 健康新知
- 潮流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