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選”人民陪審員喚醒公民意識
陳統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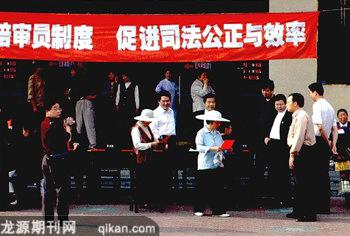
學生們看了趙萍的一張照片后,個個神情緊張,“怕哦!”——這一場景,趙萍刻骨銘心。5年前趙萍第一次以人民陪審員的身份去南京濱江中學開法制講座,給學生們展示了自己在法庭上的照片:她一身藍色正裝,嚴肅地坐在法庭上,面前還有塊牌子,寫著“人民陪審員”5個字。
“他們不懂,以為這個就是法官,是開庭的,是要宣判的。”其實,那時趙萍自己亦懵懵懂懂,不太清楚何謂人民陪審員,她是被組織推薦到下關區法院的,一邊當“法庭上的稻草人”,一邊將一些活生生的司法案例帶進校園,警示學生。
不只是中學生對人民陪審員茫然無知。2007年底,趙萍這一屆人民陪審員5年期滿,下關法院打破組織推薦的慣例,面向社會公開“海選”人民陪審員,報名的300多名社會各界人士對這個制度有起碼了解的很少,人民陪審員“知名度”太低了。
不過,“海選”人民陪審員卻引起轟動,各地媒體紛至沓來,央視《新聞聯播》亦罕見地花了3分多鐘的時間進行報道。
“要我當”還是“我要當”
英國近代著名法官丹寧勛爵說,陪審制是“自由的明燈,憲法的車輪”。現代意義上的陪審制形成于英格蘭,并隨著英格蘭殖民運動擴散到世界各地。
“人民參與司法審判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偉大成果,集中體現了人民主權論的精華,我們現在依然享受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南京工業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劉小冰教授告訴記者,人民參與司法,有英美陪審團制度和法德參審制兩種模式,英美制的陪審員只負責事實認定,中國目前更多師法德國的參審制,“人民陪審員”與法官擁有同等權利,既認定事實,又適用法律。
5年前,金陵新四村社區黨總支書記趙萍被街道辦推薦并被聘為下關區法院人民陪審員時,她可不懂這些道道,“我是被動的”。即使到了法庭,端坐在人民陪審員座位上,趙萍也不明白自己該干什么,能干什么,整整一年,“感覺到腦子老是不夠用,心里很緊張”,不言不語,成為法律規定必須坐在那里的一個人,“認為自己是擺設”。
趙萍覺得,一是自己欠缺法律知識,在職業法官面前存在心理障礙,“法官比我好,不敢講話”;二是個人偏見,對法官有敬畏心理,“覺得法官個個是瞪著眼,沒有人情味的”。不過,當了一年“法庭上的稻草人”后,法庭經歷不僅讓趙萍跨越了這兩道心門,更讓她認識到人民陪審員的獨特性,即能平衡職業法官的專業偏見,“做到人性化的量刑”。
職業法官往往由于職業思維和職業習慣,可能存在專業偏見的判決,雖是合法,但對普通當事人來說卻不盡合情理,帶出新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即所謂審判的“專業困局”。而人民陪審員來自社區,他們是“公序良俗”的代言人,“公道自在人心”,熟悉民情民意,能夠將“普通人的視角”帶入法庭。“人民陪審員憑良心對案件做出事實認定,這是一種原生態的審判。”劉小冰說。
因此,人民陪審員是法律與社區,法律與人性之間的一道橋梁。
“法律是無情的,但量刑可以有情有義。”趙萍舉例說,有一個丈夫犯了罪,依法應處3~6年有期徒刑,但具體如何量刑卻大有文章,滿判6年可能會導致父母經不起打擊倒下,妻子離異,孩子無人監護,“對社會是另外一種危害”。然而,如果考慮到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且認罪態度好、有悔罪表現,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則可能挽救這個家庭,當時被告人的小孩還有3個月就要參加考試,“他可以盡父親的責任,照顧備考的兒子”。
依程序,庭審之后,審判長(職業法官)召集人民陪審員進行合議庭評議,同情被告家庭命運的趙萍便將這些家庭信息提交審議,于是形成一個適法而有人情味的判決。事后,趙萍再利用社區工作者身份去做家庭教育工作,被告認真服刑,年邁的父母寬了心,妻子則表示安心撫養孩子,念初三的孩子亦心存感恩發奮學習,“這個判決對家庭負責任,對社會有好處”。
趙萍用“完美判決”來形容這種判決。趙萍看到通過自己的參與,改變了一個個人和一個個家庭的命運軌跡,很有成就感。5年任期結束,恰逢下關法院革新人民陪審員產生程序,在保留組織推薦10個名額的基礎上,普選20名人民陪審員。“我提前問街道,街道說,沒推薦你,那好,我自己報名!”趙萍說。
以往,趙萍們都是通過“基層推薦”當上人民陪審員,這是一項“政治任務”,種種原因使得人民陪審員“陪而不審,審而不議”,飽受詬病。2005年5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正式實施,在人民陪審員的選任方式上,規定了“基層推薦”和“本人申請”兩種模式。
既“有法可依”,又逢換屆契機,下關法院適時推出人民陪審員普選制度,這在全國是首次。從“有熱情,有時間,有精力”的選拔標準中不難看出,下關法院的出發點是調動人民陪審員參與案件審理的積極性,但客觀上,“海選”讓更多富有公共精神、熱心于公共事務的各階層人士有著均等的機會參與公權力部門的治理,擴大了司法民主,為普通民眾參與司法、監督司法開了一扇門。
“海選”進入后期考察階段時,下關法院調研室主任肖朝暉一一拜訪當選者所在單位,大多數企業管理者“態度一般”,倒是一家日資企業老板認為,他的員工參與民主政治,這是企業的光榮,他全力支持,因為參與案件陪審而請假一定批準,并且不扣工資。
49歲的趙萍參選成功,再次成為了人民陪審員。最近,趙萍又準備到濱江中學開講座,她打算給學生們講一講人民陪審員制度,“社會在進步,法治要從學生娃抓起”。
精英化還是平民化
張爭先走進來時額頭滲著汗,這是他的第一次庭審體驗,“有點激動,有點緊張,神圣與壓力都有”。36歲的張爭先也是通過下關法院人民陪審員“海選”勝出的,云南大學政治學研究生畢業,現在是南京陸軍指揮學院的一名政法學教官,2006年還通過了國家司法考試。
張爭先向記者描述第一次當人民陪審員的經歷。這是一起行政訴訟,一名普通公民狀告某行政機關的規劃侵犯個人的通風采光權,即民告官案件。
“從頭到尾都聽得懂嗎?”記者問。張爭先答得很干脆:“那當然,理論積累發揮作用了。”
張爭先給記者回放一段庭審過程:——被告當場提交行政行為證據,他當場發言,指出證據應該在法庭取證期間提交,庭審時提交無效,可以認定當時做出的行政行為是沒有法律依據的,行政行為涉及老百姓利益,任何行政行為必須事先有法律依據。“為什么不在舉證期間提交?”張爭先發問。被告考慮到自己的利益,說“當時鎖在柜子里拿不出來”。
一場經歷,讓張爭先感到人民陪審員肩負的責任:“你的意見會影響判決的結果,實際影響雙方的利益調整。人民陪審員的本質是享受權利,監督權力。”他說,人民陪審員從老百姓中來,參與審判,這既是司法民主的一個抓手,也體現了法治精神——實質是對公權力的一種約束。
如果在審理案件中,自己的觀點與法官意見不一致,或者認為法官在裁判中存在著不公正的行為,怎么辦?“認真把不同意見記錄下來,問題大的話,就使用動議權,提請院長將案件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張爭先答。《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規定,人民陪審員可以動議將案件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職業法官并沒有這項權力。這是中國特色,意在監督法官。
《決定》還規定人民陪審員與法官擁有“同等權利”。那么,何謂“同等權利”?
趙萍回答:“我會尊重法官,因為法官的法律知識是專業的,我掌握的法律知識是很膚淺的,而且我更多摻和了人情在里頭,我有這種傾向,所以我特別尊重法官。”
張爭先則說:“從立案到執行,整個環節權力都是一樣的。但由于人民陪審員大部分來自于不同的工作崗位,精力、專業背景、時間等因素的制約,對權力的行使,深度、廣度都是不一樣的。”張說,如果人民陪審員是一個花瓶式擺設的話,能否勝任陪審員的能力可以忽略不計,但如果要真正成為一個“不穿法袍的法官”,則要有能力要求,“但不是要求都是社會精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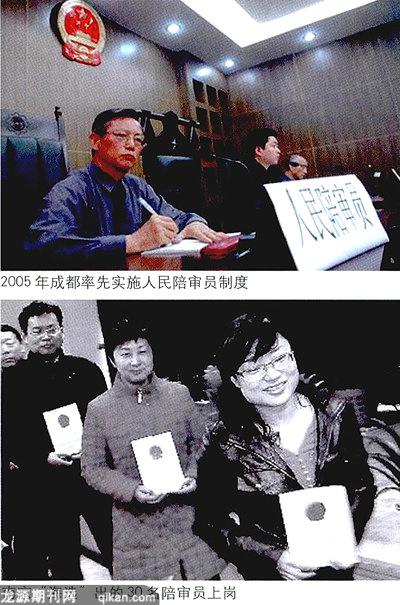
事實上,趙萍和張爭先兩個人便代表了兩個向度,一個是“平民”,一個是“精英”。在本次下關法院“海選”人民陪審員的過程中,決定中規定的“大專以上學歷”這一硬性指標即淘汰了報名者的一半,30位新任命的人民陪審員中,文化程度在大專以上的占93.3%,研究生5人。
“這勢必造成人民陪審員精英化。”這個結果引起了一些法學專家的憂慮,認為這個規定剝奪了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普通老百姓擔任人民陪審員的參與權,與人民陪審制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理念不符。
環視使用陪審制國家,對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資格限定主要是“保證不是法律專業人士、沒有擔任公職的普通公民參與司法裁判”。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李昌林認為,這樣規定,一是體現司法民主,真正讓老百姓而不是官方的代表參與司法裁判;二是認為民眾參與司法裁判,主要是利用其在價值判斷方面的優勢,民眾對法律的無知可能正是制度的需要。
如以此種理念檢視,張爭先便無資格當人民陪審員。因為他既是一位“法律專業人士”,又是一名軍校教官。而新任下關法院人民陪審員中,“有省、市勞動模范,大學教師、現役軍人、醫生,機關、企事業單位干部,也有普通職員、工人、社區工作者”。
陪審制還是參審制
不過,結果出現精英化傾向,并不是下關法院這樣一個基層法院所能決定的,這是制度設計的問題。人民陪審制是陪審制還是參審制?如果是前者,則是平民至上,如果是后者,則必須精英參與,否則形同虛設。
在中國,更多時候,人民陪審員被邀請參審只是為了解決法院案件多人手少的矛盾,陪審員不過是一種緩解法院人力不足的手段而已。雖然歷史地看,12世紀陪審制的出現,首先是為了應對司法任務繁重、法官數量不足的實際需要。
“陪審制度在中國已有100年歷史,并曾出現在1954年憲法中成為一項憲政原則,后遭遇‘文革破壞,改革開放以來進行了一些簡單的恢復,1979年以后修改的憲法里已經沒有陪審制度,從憲政的角度講,是一種倒退。2005年全國人大頒布決定,意圖是好的,希望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人民陪審制。”劉小冰說。
“基于中國國情,實行陪審制更現實,中國那么多人去了解那么復雜的法律,這是一種浪費,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劉小冰說,中國人民陪審員制度是穿“陪審員”外衣,內核是陪審制的變種——參審制。下關法院邀請他去給新任命的人民陪審員做培訓,他對他們說:“如果真的實行陪審制,我希望你們不要受任何法律培訓。比如說,在美國,你會被問有沒有當過兵,如果當過兵,你紀律性強、組織觀念強,總以為法官說的是對的,缺乏獨立的思考,不能當陪審員。”
嚴格意義上說,人民陪審員制度既不是英美的陪審團制度,也不是德法的參審制,而是介于兩者之間,兼以吸收兩邊的優點,“同時保障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最終把矛盾化解掉,中國陪審員擔子很重。”肖朝暉說。因此,這次下關法院“海選”標準,后來又加了“三個有”,有認知,有能力,有聲譽。
最近有消息稱,中國司法體制改革下一步將借鑒英美陪審團制度,對疑難案件試點實行陪審團制度,由陪審團對案件事實的認定行使決定權,法官只負責適用法律,以減少涉訴上訪。“你不需要懂多少法律,你只需要憑你的良心就行。”劉小冰說。
這一消息印證了肖朝暉的判斷。中國制度設計者的愿景是,讓人民陪審員“樂于、敢于、善于參與審判,不是附和法官意見,而是產生實際效果,確保司法公正”,至于這個制度被歸類為陪審制還是參審制并不重要。
與其他領域的探索一樣,人民陪審員制度實踐中依然會出現各種問題。有一位擔任人民陪審員的大學教師2005年8月就參加了9件案件的陪審工作,2005年12月上半月參加案件陪審9次,2006年3月6日至9日連續4天參加了4起案件的陪審,和法院大部分專職法官辦案數相同甚至更多,結果被同事戲稱“專職法官”。
導致這種“專職化現象”,主要原因是原來由組織推薦的人民陪審員多是各單位的骨干,一旦繁忙的工作與審判工作相沖突,就出現了“聘請容易參審難”。以下關法院為例,2007年該院原有的20名陪審員中有4人因為種種原因,一年都沒有參與過案件的審理。這使得法院極有可能將陪審任務固定交給少數積極性較高的陪審員,導致他們成為變相的“編外法官”。“這會導致參與權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與人民陪審制的民主性背道而馳”。
此外,類似人民陪審員該不該穿制服,陪審員該不該由人大任免等一系列難題,還在等人們去探索,去變革。
“給民眾一些啟示,以激發更多的思考。”下關法院政治部主任李向紅認為改革的目的,公民的覺醒是最重要了,有了國民觀念與素質的同步發展,恢復并逐漸完善中的人民陪審制度才能真真正正地發展起來。
劉小冰說,下關法院“海選”人民陪審員,敞開大門歡迎系統外、制度外的人參與司法改革進程,這既是對公民權利的尊重,也促進了公民的覺醒。而以前我們總以為,老百姓對這些東西不感興趣,那我們來代表他們干吧。事實上,不是這樣。
(摘自《南風窗》200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