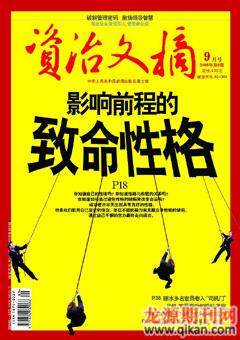漏雨
趙心瑞
真正的雨季還沒開始,就下了好幾場連陰雨。家住6樓的老張,已是滿臉愁云。房子漏雨,整個屋頂像一張世界地圖,海洋面積遠遠大于陸地面積。老張老伴兒叨叨著讓老張想法子修房頂。
以前樓頂漏雨,向單位告知一下,就會有人來管。如今,老張的房子剛辦理了私產,房屋修繕得靠自己解決。
老張是在單位的辦公室工作。辦公室是全單位的心臟,指揮著各個科室的工作,所以其他科室人員對辦公室的人畢恭畢敬,即使辦公室的一般人員,骨子里也透著一種傲氣。可老張沒有這份優越感。
老張的父親在“文革”期間,由于說錯話,站錯隊,被批斗,后打入牛棚。父親的教訓,讓他刻骨銘心,環境的壓抑,使他沒了說話的底氣,久而久之,性格變得沉默寡言,唯唯喏喏。“不惹事,不生非”成了他一生做人的信條,和同事相處忍讓為先,對領導更是唯旨是從。因此,干了這么多年依然是個科員,也沒人想起提拔他重用他,只有年終時人們才想起他,一大堆材料等著他駕馭組織編排成文。也只在這時,領導夸上一句:“不錯!”老張聽了,心里頓時生出個太陽,暖乎乎的,似乎全年都沐浴在陽光下。
這幾天房子的事情搞得老張是心煩意亂,夜夜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有一天臨明,老張忽然想起朋友的兒子是泥瓦工,眼睛一亮,抓起床頭電話就拔,一旁老婆發話:“天還沒亮,你發什么神經?”老張才意識到自己的魯莽,放下電話又鉆進被窩復了個二覺。
泥瓦工來了,爬上6樓頂察看,談妥工錢,定下一周后的周日來處理,臨走囑咐老張,一定讓樓下的住戶把太陽能熱水器拆卸下來,否則不能挑油氈,抹泥灰。
老張送走了泥瓦工,陰沉著臉,好像又有一場雨到來了。
安這太陽能熱水器的,是從辦公室提拔起來的付副局長家。按理老張與他是直接的上下級,關系要比一般人近些,可老張做了一輩子科員,從未要求過領導做什么事,讓人家付局長拆卸熱水器,老張犯難了。
上班時間,他不好意思找付局長談自己的私事,下班又怕打擾人家休息。每次上下樓路過付局長的門口,他都盡量放慢腳步,想碰巧遇到付局長走出家門,借機說出自己的要求。
修房的日子越來越近,老張愣沒瞅準個機會。眼看著第二天工人要來了,晚上老張決定去一趟付局長家。他看著墻上的掛鐘,算計著局長吃晚飯看電視的時間,時鐘指到9點,老張硬著頭皮下了樓,站在局長門前。他先深深地長出了一口氣又咽了一口唾沫,這才抬起手用指頭肚慢慢地敲了3下門。他敲得太輕太輕,醫院的大夫敲病人的肋條,也不過是這種樣子。等等,沒人來開門。他在指頭上加了些力,又敲了4下,還靈機一動地咳嗽了兩聲,然后前合著身子側起耳朵聽。好的,里面有腳步聲過來了。他稍微地直了直腰,臉笑笑地做著說話的準備。
付局長在單位值班,太太正集聚了一伙人打麻將。付局太太一貫驕橫,老張平日里見著她就躲著走,今兒個面對面,很簡單的事情,吞吞吐吐說了好半天。這時,正巧趕上付局太太輸了牌,心里亂亂槽糟的,老張的話,讓她氣不打一處來,柳眉倒豎,說:“這大晚上的,明兒個再說!”
“哐當!”老張被冷在了門外,站了半天,灰頭土臉上了樓。
第二天一大早,泥瓦工帶著一幫人來了。老張向他們道歉,說往后推推修頂日期。泥瓦工急了,好容易糾集齊人,怎能說推就推呢?問清楚原因,是樓頂上的熱水器沒拆卸。泥瓦工說這好辦,咱給拆了,抹好灰后,再安上不就得了。
老張擔心地說:“那是局長家的,不能隨便拆。”
老張示意泥瓦工一幫人稍坐坐,自己忙不迭地跑下樓,再次敲開付局長家的門。付局太太打了一夜牌,臨明才鉆進被窩里,敲門聲攪了她的好夢,不情愿地爬起身,睡眼惺忪地開了門。老張急切地詢問拆卸熱水器的事,付局太太給了一句:“問我家老付去吧。”說完打著哈欠轉身回屋里。
老張如實地向泥瓦工做解釋:“局長不在家,太太不管事,能不能改天干。”
泥瓦工眼瞅著屋頂的地圖,不依不饒發了話:“局長咋啦,局長也得讓百姓過日子吧!老伯,你別管了,有事找我!”
泥瓦工有一副俠義直腸,不管三七二十一,帶著一幫弟兄上了6樓頂,嘁哩喀喳拆下熱水器,挑開油氈干開了。
老張老伴兒張羅著買菜去了,老張站在樓下,手搭涼棚往樓頂上瞅,笑呵呵地提醒著過往的人,不住地說:“當心!當心!”
也不知誰多事,跑去報告付局的太太。付局太太披頭散發滿臉怒容沖下樓,一把拽住老張說:“平常看你是個老實人,老實人就這樣辦事?啊!走!和我家老付說去!”
眾目睽睽之下,老張漲著紅臉,慌忙掙脫她的纖纖玉手,惶恐地跟著她上了樓。
付局太太撥通付局長的電話,連珠炮似的向線的那頭傳達著不滿。
老張聽得汗珠子也滲出來了。
這些日子,單位的正局長離休了,班子要調整,付副局長一心想把副職轉成正局,正等著單位搞民主測評,在這節骨眼上,他可不想出半點紕漏。
電話那頭傳來輕描淡寫的聲音:“拆就拆吧,省得我們找人,過后讓他們安上就是了。”一旁的老張聽得清清楚楚,懸到嗓子眼的一顆心一下子跌到肚里。
接著付局長讓老張聽電話,“老張,給你添麻煩了。還是我關心你不夠啊,請多多原諒。有什么困難盡管說,咱們是鄰居嘛。”
“給您添麻煩了。給您添麻煩了。”老張誠惶誠恐,點頭哈腰,感激涕零。還有就是,仿佛那個太陽喲,照得自己渾身熱乎乎的。
(摘自《新世紀文學選刊·上半月》
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