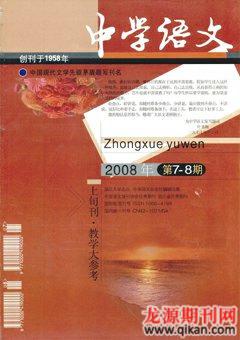孔子:“禮治”遭遇“無道”
朱前珍
《季氏將伐顓臾》中孔子借“季氏將伐顓臾”一事一針見血地道破季氏的野心:“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一語中的地指出“僭越”是天下大亂的根源。通過分析探討,學生對孔子“禮治”的治國主張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認識:在孔子看來,倫理道德是家庭和社會得以維系安定和發展的根本,是任何美好追求的基石。君、臣、父、子的封建綱常要嚴格維護。齊景公向孔子問政時,他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也就是說要搞好統治,首先就得擺正統治秩序,每個人都應該按照自己所在等級的道德行為規范去做事,才能長治久安、百姓安樂。
孔子旗幟鮮明地反對討伐顓臾,同時他也為季氏提供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有一學生問,“修文德以來之”,是國君的職責。孔子的建議,只是改變了形式,換暴力為文德而已,但本質目的不變,都為了滿足季氏擴張勢力的野心,這不還是僭越職權嗎?這不還是有違君臣倫理嗎?孔子為何自相矛盾呢?
此生語出驚人,這的確是一個問題,值得深入探究。課后,筆者查閱大量資料,發現不僅此文中的孔子言論有矛盾,而且綜其一生,都充斥著這種有矛盾的苦楚。筆者在此擬將孔子一生分為四個階段加以闡述:
一、堅守“禮治”
孔子一生推崇周禮,以之為尺度來審視社會,他痛惜禮制的崩壞,對一切不合乎禮制的行為都予以嚴厲的批判,甚至以“禮”來衡量現實和入仕:“不仕無道之世”。他說:“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靈公》)他還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
孔子還教導弟子說:“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勉勵他們潔身自好而不與亂臣賊子為伍。孔子稱贊弟子季次與衛國大夫寧武子,說他們“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于都,唯季次未嘗仕”(《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論語·公冶長》)。孔子贊揚季次和寧武子在邦無道的時候采取不與當權者合作態度。孔子還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對于那些在邦無道之時,放棄理想而“枉道事人”以謀取財富者,孔子十分鄙夷。
二、無奈妥協
但是在現實面前,孔子所標榜的“不仕無道之邦”卻往往顯得蒼白無力。孔子痛心地發現,自己所處的時代早已禮崩樂壞、王道喪失。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以“禮治”面對社會現實呢?坐而論道,或是以“禮”針砭時弊,顯然遠遠不夠。孔子意識到,必須入仕,通過參政來實現“仁政理想”。然而,如果入仕,就必須投身于無道的現實之中,與那些被孔子鄙夷為“斗筲之人”的當政者周旋。在求仕的實踐中,孔子所向往的周禮與仁政,他所信守的人生原則與政治現實之間,顯然矛盾重重,展現在孔子面前的道路與選擇,可謂兩難。
處于窘境中的孔子既不能放棄“禮治”,就只好對“禮”作寬泛的解釋:“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意思就是:君子對于天下的事情,沒有固定統一的做法,只要遵照合理的原則就可以了。可見“禮”并非唯一的準則,因而,經歷了矛盾與困惑的孔子終究有所選擇。當孔子步入無道的現實來求仕的時候,可以說,這是他的無奈之舉,身處亂世,只好退而求其次了。
可貴的是,孔子于矛盾中始終沒有迷失方向,沒有放棄對“禮治”、“仁政”理想的追求,雖明知“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但不是“知其不可而為之”,這就體現了他毅然追求仁政理想的決心。
三、奮力抗爭
只有理解了孔子對于“仁政”鍥而不舍的追求精神,才會理解孔子不僅參加到無道政治當中,并且與僭禮的執政者保持密切關聯的種種做法。
魯國三桓,僭用天子之禮,堪稱無道,但孔子卻始終與三桓若即若離。《論語》中多有三桓向孔子詢問為政之道的記載,如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孔子回答:“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為政》)又如季康子患盜,向孔子求教,孔子也好言勸導:“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論語·顏淵》)更有甚者,在求仕當中,孔子對于家臣之流的召請,也并非完全沒有回應。“公山不狃召孔子”,孔子雖然最終拒絕了他,但是當時孔子仍然不覺心有所動。被孔子嘲諷過的衛靈公愿意請孔子出仕的時候,孔子也就接受其俸祿。孔子認為,求“仁”便會最終得“仁”,希望自己能夠從無道政治中脫穎而出,最終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不僅如此,孔子還多次向三桓推薦弟子,希望通過弟子們入仕,從而實踐他的治國主張。孔子說:“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論語·公冶長》)“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論語·雍也》)三桓以卿大夫身份把持國政,乃是無道政治的典型,然而為追求仁政,迫使孔子不得不靠近他們。孔子的無奈妥協恰恰是執著于“仁政”理想的實現而進行的奮力抗爭。
四、失意回歸
孔子為追求仁政,卻又必須來往于亂臣賊子之中,以背離其人生準則的方式來追求理想,實在是出于無奈。孔子曾仕于魯國,為大司寇,適逢齊國以女樂賄賂魯國執政,季桓子同國君一道前去觀看樂舞,“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勸孔子離開無道的魯國,但孔子對于季桓子尚存一線希望,他說:“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但是季桓子根本無心重用孔子,而是“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此時才默然離魯,開始了長達14年之久的漂泊生活。(《史記·孔子世家》同樣,孔子求仕于衛國的時候,衛靈公荒淫而怠于政,“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將孔子作為其自我夸耀的擺設,視同玩物。孔子見到衛靈公無禮已甚,只好率弟子離開危機四伏的衛國。(《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一生為實現自己的理想不惜顛沛流離,然而最終只能拖著疲憊的身軀,失意地回歸教書著述,授徒講學。因此,孔子對“恪守周禮,不仕無道之世”的隱者格外敬重。他盛贊古代的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在孔子漫長的求仕生涯中,隱者的影子總是若隱若現,從長沮、桀溺直至荷藜丈人,孔子雖然不屑于他們消極避世的做法,但仍對他們恭敬有加,其中不正隱含了孔子對于不仕無道精神的贊賞嗎?
據此,我們不難理解,《季氏將伐顓臾》中所呈現的孔子思想的矛盾,恰恰是孔子一生矛盾的折射。孔子為追求仁政而不得不向無道的社會現實妥協,但在其執著的追求當中,又包含著對“禮”的深深眷顧。同時也深深地折射出了他面對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的無奈。政治現實積重難返,孔子回天乏力,這注定了他追求一生而終無所獲的結局,最后只有留給后人一聲嘆息:“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
[作者通聯:浙江衢州市第二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