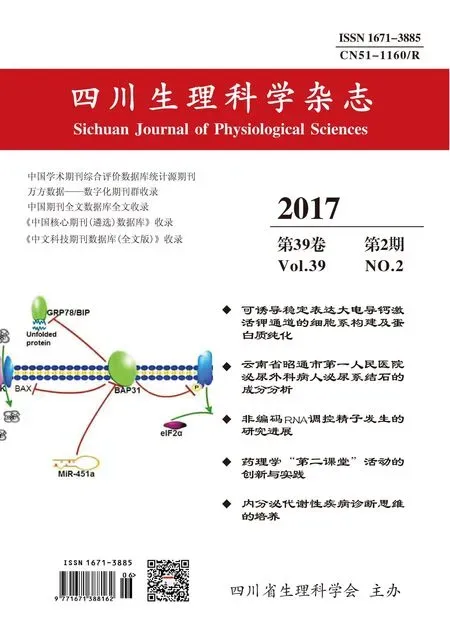內(nèi)分泌代謝性疾病診斷思維的培養(yǎng)
龍健
(重慶醫(yī)科大學(xué)附屬第一醫(yī)院內(nèi)分泌科,重慶 400016)
內(nèi)分泌代謝性疾病診斷思維的培養(yǎng)
龍健
(重慶醫(yī)科大學(xué)附屬第一醫(yī)院內(nèi)分泌科,重慶 400016)
診斷思維能力的培養(yǎng)是臨床醫(yī)學(xué)教育的核心和重點(diǎn),不同專業(yè)在診斷思維能力培養(yǎng)上側(cè)重點(diǎn)不同。內(nèi)分泌代謝性疾病的診斷包括功能診斷、定位診斷、病因診斷,按照內(nèi)分泌代謝疾病特點(diǎn)建立科學(xué)、有效的內(nèi)分泌代謝病思維能力培訓(xùn)模式對(duì)培養(yǎng)專業(yè)醫(yī)學(xué)人才十分重要。
診斷;內(nèi)分泌代謝疾病;思維能力;培養(yǎng)
診斷即對(duì)疾病及其病因進(jìn)行判斷,一個(gè)正確的診斷是醫(yī)學(xué)理論知識(shí)、臨床經(jīng)驗(yàn)和科學(xué)的診斷思維方法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許多誤診就是缺乏科學(xué)的診斷思維方法造成的[1]。內(nèi)分泌代謝性疾病包括內(nèi)分泌疾病及代謝性疾病,具有不同于其他臨床專業(yè)的特點(diǎn),尤其內(nèi)分泌疾病存在中樞-靶器官-周圍組織的調(diào)節(jié)系統(tǒng),影響因素眾多,病因復(fù)雜。內(nèi)分泌代謝性疾病診斷思維能力的培養(yǎng)有別于普通臨床思維能力培養(yǎng),總結(jié)和探討內(nèi)分泌代謝病診斷思維能力培養(yǎng)方法對(duì)提高教學(xué)水平,培養(yǎng)專科醫(yī)師十分重要。
1 內(nèi)分泌代謝性疾病的特點(diǎn)
內(nèi)分泌代謝性疾病包括內(nèi)分泌疾病及代謝性疾病兩大類,其病因復(fù)雜、臨床表現(xiàn)多樣。
1.1 病因復(fù)雜
內(nèi)分泌系統(tǒng)存在中樞、靶器官和外周的相互調(diào)節(jié)作用,激素在腺體內(nèi)的合成及釋放、在外周組織的作用及代謝等任意一個(gè)環(huán)節(jié)異常,均可使血循環(huán)激素水平異常,而各個(gè)環(huán)節(jié)影響因素眾多。炎癥、腫瘤、缺血、免疫、手術(shù)、外傷等均可導(dǎo)致系統(tǒng)損傷,使其病因復(fù)雜[2]。
1.2 臨床表現(xiàn)多樣
2.1 臨床診斷思維過(guò)程
激素主要通過(guò)血循環(huán)進(jìn)入外周組織器官發(fā)揮生理作用,當(dāng)激素缺乏時(shí),臨床表現(xiàn)為外周組織器官功能障礙,但病變部位可能在中樞。
1.3 病變部位與表現(xiàn)部位不同
2 臨床診斷思維過(guò)程、基本原則及培養(yǎng)
在診斷過(guò)程中需遵循一定的原則,以保障診斷的正確性,減少誤診、漏診率,基本原則包括實(shí)事求是的原則、" 一元論" 的原則、優(yōu)先考慮常見病多發(fā)病的原則、首先考慮器質(zhì)性疾病的原則、首先考慮可治性疾病的原則等[5]。
一個(gè)內(nèi)分泌腺分泌多種激素;一種激素作用于多個(gè)外周器官系統(tǒng);一種激素常有多種作用,故內(nèi)分泌疾病臨床表現(xiàn)有多種組合類型,具有多樣性[3]。
2.3 臨床診斷思維能力培養(yǎng)方式
【大意】完全相信《尚書》,那么還不如沒有《尚書》。我對(duì)于《尚書》中的《武成篇》,就只取其中的兩三處罷了。
2.2 臨床診斷思維的基本原則
與其他一些化學(xué)消毒劑[如戊二醛(GLUT)、季銨化合物(QAC)以及GLUT/QAC混合物]不同,衛(wèi)可S和衛(wèi)可LSP在4℃時(shí)仍能有效對(duì)抗致病微生物(冬季農(nóng)場(chǎng)的氣溫一般為4℃),無(wú)需增加使用濃度或接觸次數(shù)。
臨床診斷思維是臨床醫(yī)師的基本功,體現(xiàn)其獨(dú)立解決問(wèn)題的能力。
首先對(duì)所獲得的臨床資料進(jìn)行分析,尋找引起該種臨床表現(xiàn)的相關(guān)疾病,再通過(guò)細(xì)致分析或進(jìn)一步檢查,排除其它并建立診斷,最后通過(guò)治療反應(yīng)修正或驗(yàn)證診斷,其中邏輯思維、發(fā)散思維、假設(shè)思維、推理思維、比較性思維,批判式思維模式在臨床診斷過(guò)程中交替使用,不斷推動(dòng)思維過(guò)程前進(jìn)[4]。
在開采過(guò)程中,為了避免冒落事故,在傾斜及急傾斜的留礦法生產(chǎn)采場(chǎng),應(yīng)盡量在聯(lián)絡(luò)道內(nèi)應(yīng)用水平深孔或中深孔落礦;人員不得已而必須在懸空頂板下作業(yè)時(shí),應(yīng)該類似上述房柱法、全面法在采場(chǎng)中間間隔2~3 m布置一排鋼支架或20~40 t支撐力的單體液壓支柱支撐頂板。為了防止支柱下陷或漏頂,可以給支柱用長(zhǎng)約3 m的30號(hào)槽鋼“穿鞋”或用長(zhǎng)約1.5~2 m的槽鋼“帶帽”。厚大礦體開采的階段礦房法、崩落法采場(chǎng),可以在鑿巖巷道內(nèi)上向扇形中深孔或深孔落礦,從而避免人員在懸空頂板下作業(yè)。
正確的臨床思維是在疾病診治的過(guò)程中逐步形成的,只有通過(guò)積極參與、主動(dòng)思考才能獲得,單純的理論教學(xué)難以培養(yǎng)臨床思維能力。臨床思維能力培養(yǎng)通常通過(guò)典型病例討論進(jìn)行,通過(guò)病例討論指導(dǎo)學(xué)生如何獲取和分析臨床資料,如何結(jié)合理論知識(shí)提出初步診斷并總結(jié)診斷依據(jù),如何制定進(jìn)一步的檢查和治療計(jì)劃,使學(xué)生逐步把枯燥的理論知識(shí)與實(shí)踐聯(lián)系起來(lái),刺激學(xué)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潛能,培養(yǎng)和訓(xùn)練學(xué)生形成系統(tǒng)的臨床思維。在此過(guò)程中,需指導(dǎo)學(xué)生提前進(jìn)行診斷學(xué)、內(nèi)科學(xué)基本理論知識(shí)及臨床技能的復(fù)習(xí)與鞏固,掌握熟練的問(wèn)診和體格檢查技能。
為此,本文提出了采用零損耗深度限流技術(shù)提高變壓器抗短路能力的方法,首先,分析了零損耗深度限流裝置的基本工作原理,探討了變壓器故障類型;其次,分析了變壓器抗短路沖擊能力下降的原因,得出了采用零損耗深度限流技術(shù)可以變向提高變壓器抗短路能力的結(jié)論;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礎(chǔ)上,提出基于零損耗深度限流技術(shù)提高變壓器抗短路能力的基本應(yīng)用原則,并通過(guò)算例驗(yàn)證該方法的可行性。
在對(duì)思辨性翻譯能力重要性程度的認(rèn)識(shí)上,根據(jù)下表我們可以看出,近百分之九十的同學(xué)都認(rèn)識(shí)到了它的重要程度,這就表明,對(duì)于所有的MTI專業(yè)學(xué)生來(lái)說(shuō),不管其年齡多大,都對(duì)思辨性翻譯這一名詞有一定的認(rèn)識(shí),并都對(duì)其有一定的重視程度。其中又?jǐn)?shù)年齡在23到25之間的同學(xué)對(duì)思辨性翻譯能力更為重視。這說(shuō)明,現(xiàn)在在校學(xué)生還是有一定的思辨性翻譯能力認(rèn)識(shí)基礎(chǔ)并不是一無(wú)所知的。
3 內(nèi)分泌代謝病診斷思維能力培養(yǎng)
內(nèi)分泌代謝性疾病臨床診斷思維能力培養(yǎng)既要遵循普內(nèi)科思維能力培養(yǎng)的基本模式,也具有其獨(dú)特的專業(yè)思維特點(diǎn)[6]。內(nèi)分泌代謝性疾病的診斷包括功能診斷、定位診斷、病因診斷三個(gè)部分,逐層深入遞進(jìn),缺一不可,在臨床思維培養(yǎng)中要貫穿這種三段式診斷思維模式。首先從患者的臨床表現(xiàn)分析可能是何種激素水平異常導(dǎo)致,進(jìn)一步結(jié)合激素水平檢測(cè)結(jié)果確定是功能亢進(jìn)或功能減退。其次通過(guò)分析中樞、靶腺激素水平,確定導(dǎo)致激素異常的病變部位。通常情況下,中樞分泌刺激激素增加靶腺激素分泌,靶腺激素反饋抑制中樞激素分泌,如靶腺激素伴隨中樞激素同時(shí)升高,說(shuō)中樞不受靶腺激素抑制,病變?cè)谥袠校蝗绨邢偌に匕殡S中樞激素同時(shí)降低,說(shuō)明中樞激素?zé)o法代償性增加,病變?cè)谥袠小W詈髧@病變部位尋找病因:炎癥、腫瘤、免疫、手術(shù)、外傷等?在診斷的過(guò)程中首先確定受累的激素,再分析病變部位及病因。熟悉內(nèi)分泌激素種類及作用,掌握中樞-靶腺反饋調(diào)節(jié)機(jī)制,掌握各種激素功能亢進(jìn)和功能減退的臨床表現(xiàn)是進(jìn)行內(nèi)分泌代謝性疾病診斷的前提。教師需提前指導(dǎo)學(xué)生復(fù)習(xí)和鞏固內(nèi)分泌總論中的相關(guān)章節(jié),熟練掌握內(nèi)分泌系統(tǒng)基礎(chǔ)知識(shí),并通過(guò)多個(gè)典型病例引導(dǎo)學(xué)生反復(fù)進(jìn)行三段式診斷思維過(guò)程訓(xùn)練,使其養(yǎng)成三段式診斷思維的習(xí)慣。
科學(xué)的臨床思維方法是臨床醫(yī)師得出正確診斷、采取正確治療方式的關(guān)鍵。加強(qiáng)思維能力培養(yǎng),尤其按專業(yè)特點(diǎn)進(jìn)行診斷思維能力培養(yǎng),才能培養(yǎng)富有思考能力和創(chuàng)新精神的合格醫(yī)生人才。如何建立科學(xué)、有效的內(nèi)分泌代謝病思維能力培訓(xùn)模式需要在今后的內(nèi)分泌學(xué)教學(xué)中不斷探索和完善。
1 曾勇,魯映青. 論臨床思維概念[J]. 醫(yī)學(xué)教育探索, 2005, 4(1): 46-48.
2 陳家倫. 世紀(jì)之交的內(nèi)分泌學(xué)淺述[J]. 中華內(nèi)分泌代謝雜志, 2000, 16(6): 337-341.
3 李明龍,趙家軍. 現(xiàn)代內(nèi)分泌學(xué)發(fā)展的回顧與展望[J].醫(yī)學(xué)與哲學(xué), 2003, 24(4): 41-43.
4 陳金秀. 談臨床實(shí)習(xí)生對(duì)內(nèi)科疾病的臨床思維[J]. 中國(guó)現(xiàn)代醫(yī)學(xué)雜志, 2001, 11(10): 106-107.
5 詹華奎,李艷,畢榕,等. 加強(qiáng)內(nèi)科病案討論提高臨床思維能力[J]. 成都中醫(yī)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 教育科學(xué)版, 2012, (2): 4-6.
6 陳適,潘慧,朱慧娟,等. 內(nèi)分泌代謝疾病臨床診斷新思路[J]. 健康管理, 2015, (1): 79-83.
Train of clinical diagnosis thoughts on endocrinal and metabolic diseases
Long Jian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16)
龍健,女,副主任醫(yī)師,主要從事糖尿病、甲亢及并發(fā)癥的臨床、教學(xué)、科研工作,Email:pudding1977@163.com。
2017-3-28)